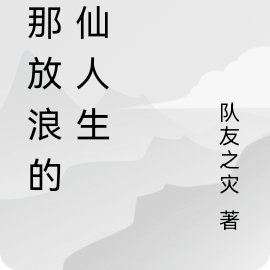随着一声又一声长鸣,火车蜿蜒如蛇,终于停靠在了下一个站台。
“还好,赶上了!”裴祖德喘着气,笑容满面地看着房红文。
“裴祖德!你小子一个招呼不打,这么久都不见人影,到底死哪儿去了?”房红文一个人缩在车厢角落,已经巴巴地张望了许久,“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差点就被查了!”
無錯書吧“怎么?才一会儿就已经想我了?”裴祖德笑地意味深长。
“去你的!你小子一点不正经!”房红文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如此惊心动魄,这家伙怎么能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怎么回事呢?自已和裴祖德不过才认识几小时,却老被他惹生气。
“老房同志生气咯!”裴祖德故意阴阳怪气道,“好啦!我刚才闹肚子,有点急所以没跟你打招呼。刚好火车到站了,我带你去吃个好东西!”
裴祖德不说,房红文还一点没觉得。制服刚才离自已越来越近,眼看已经到了对方看向自已的地步。就在即将开口查票之际,对方竟然被喊走了!
房红文的心刚刚一直吊在嗓子眼上,也就完全顾不得肚子饿这件事了。
这才发现,空气中若有似无地,飘着一股烧鸡的味道。
“你也闻到了?”裴祖德兴奋地搓着手问道。
“烧鸡……烧鸡……来了不吃鸡……错过后悔来不及!”
月台边,小贩们都在卖力地吆喝着。小小的摊位迅速被人群围地水泄不通。
裴祖德虽然长得干瘦,劲儿倒是不小。很快就挤到人群最里面,用洪亮的声音朝小贩喊道:“来两只烧鸡!”
小贩听到喊声,粗着脖子红着脸喊着:“马上就来!”手里却忙不迭地给人找着零钱。
裴祖德眼疾手快地将一张一百元高高地举起,在小贩面前晃了晃。见到面额如此大的钱,小贩是笑得合不拢嘴,乖乖地将两只烧鸡奉上。
别人看他是个孩子也不与他争闹,裴祖德便得了便宜。
烧鸡外面包裹着一层油纸。油纸的一部分已经被浸润,看起来油汪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二人不由得被烧鸡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彼此会心一笑。
饥肠辘辘的肚子在这勾人的香气之下再也等不了,二人就地将烧鸡剥皮拆骨、大快朵颐起来。
烧鸡很快就被消灭完了。裴祖德意犹未尽地舔着油亮的嘴唇、满足地拍着微微凸起的肚子,大剌剌地伸长胳膊、感慨着这样的人生可太美了!
“哟!认识老裴同志到现在,原来你还是这么诗情画意的人啊?”房红文故意揶揄道。
裴祖德却不以为意、只当被人夸奖了:“那是,你不知道我老裴的地方可多了去!”
“话说……”房红文盯着裴祖德、眼也不眨一下:“我的确不知道你小子哪来这么多钱?一出手就是一百块!”
房红文浑身上下加起来,统共也才二百来块钱。就连这些钱,也都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吃俭用很久才攒下来的!
大人都不一定舍得买的烧鸡,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眼也不眨一下地说买就买、而且一买就两只?
对于一个坐火车都要逃票的穷小子,竟然阔绰到随手就能拿出一张百元大钞,这本就是极为反常的一件事。
裴祖德没有解释,却是直盯着房红文看,直看了好一会儿。
“你看个啥?”房红文被盯得心虚,好像自已才是有问题的那个。
“没啥,我叔有钱而已,这又没啥好解释的。”笑容消失在脸上,裴祖德突然就不说话了,大大的眼睛竟深邃起来。
“那逃票是为啥?”
“不为啥。”
“那跟我搭话又是为啥?”
“你哪来这么多为啥?!”
“你指定是有点啥!”
“你烦不烦?”
“说呀!为啥?”
“再问就绝交!”
……
暮色沉沉,夜逐渐深了。
二人在成功躲避又一轮查票之后,终于喘着气在另一节车厢里歇了下来。
肚子饱饱,今晚指定能睡个好觉。
蜷缩在角落里,随着火车有节奏的晃动,二人开始进入梦乡。不料,却突然被一个男人的叫嚷声吵醒。
“啊!啊!我钱包呢?我钱包呢?我钱包不见了!”男人慌乱地在座位四周各种搜寻。
“同志,你再找找,会不会是你放在行李箱里了?”周围有人好心建议道。
“钱包我是贴身放的,没有放在行李箱里!我已经到处都找过了!都没有!”男人慌乱不已,手还在口袋中继续翻找着,“火车到站之前还在呢!”
“同志,不行的话,还是喊巡警吧!”一位大爷说。
不大一会儿,巡警便来到失窃的车厢:“是谁的钱包丢了?”
“我!是我!我丢了一只黑色钱包!”男人激动地回应,然后便开始语无伦次地描述着事情经过。说的时候,就连手都在发着抖。
丢失的钱款数目不小。据男人自已说,钱包里那厚厚的一叠几乎都是百元大钞,得有好几千块钱。
巡警例行公事地询问完,又向男人交代完在后面一站下车去报案之类的话,便离开了。
“啊?就这么走了?等火车进站小偷早溜了!这钱还能找得回来啊?”男人有些崩溃,“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就这么没了……”
这种事在火车上时不时地在发生,根本没有人能给出解答,只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百元大钞……到站前钱包还在身上……房红文的心里总隐隐觉得这件事有哪里不对。
然而浓浓地困意向他袭来,便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夜平静无波。
时间在躲制服和安静地当个好乘客的交错中流逝。
只是,房红文总在竭力说服自已,昨晚发生的盗窃案与身边的裴祖德无关。
肯定是我想多了,他都说了他叔叔是有钱人。应该……只是巧合吧!
房红文将自已心里奇怪的念头驱赶出去,决定不再多想——毕竟,等下了火车,这场奇怪的缘分便也将随之终结。
对方是什么人,又与自已有什么干系?
说到底,自已又有什么资格去管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