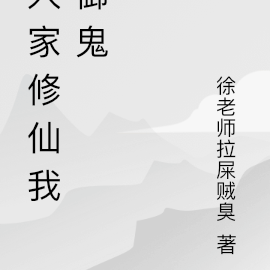格尔木疗养院
梁湾的心不安的跳动着,推开那扇被墙堵住已久的房间门。
只是微微抬眼,便看见了自已最熟悉的两个字,心却落了地。
白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
凌乱交叠的字迹,与血色的页面何其相似,都充满着,
无法诉说的绝望。
梁湾不知站了多久,原本带着欢喜的眸子被浪潮彻底吞噬,只余下诡异的平静。
原来这里就是哥哥住过的地方啊,有点小,比哥哥给自已选的房间还小。
这么想着,梁湾一步步走进那个只能放下一米五宽单人床的房间。
床旁边的地下,是一架不算那么完整的白色人骨,空洞的骨架下是有一米六左右的黑发。
左手骨头离身体远了点,像是被斩断了。
头和头发也是,有些白色的灰,被铁床的床脚与身体分离着。
哥哥,别吓轻轻了,轻轻一点都不怕骨架的。
床单上是发黑的血,真是怪异啊,连身体的血肉都被啃食了,但床单却好好地保存着。
梁湾走过去,打开了那张被细心叠好的床单,熟悉的字体映入眼帘:
‘亲爱的轻轻:
轻轻,见字如晤。
今天是哥哥离开你的第十年六个月零五天,轻轻,生辰快乐。
哥哥今天依旧很想轻轻,你有想哥哥吗?
轻轻,哥哥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哥哥害怕最后不记得轻轻,所以就在墙上写下了轻轻,希望你不要怪哥哥。
轻轻,哥哥最近有点失眠,失眠的时候就靠着想轻轻度过。
所以字写得可能多了一点,希望轻轻进来的时候不会被吓到。’
哥哥,轻轻才不会被吓到。
梁湾继续往下移动,视线向下,
‘轻轻,哥哥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到这里,这是哥哥在那群人撤离的第六十三天写下的信。
我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会被祂带到这里,但我需要祂所说的计划走。
因为哥哥很想再次见到轻轻。
我总是想着,轻轻一个人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
轻轻从小就被哥哥养的娇气,哥哥很怕轻轻受委屈。
轻轻,哥哥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不要担心。
……
轻轻,哥哥有些记不住你了,但是哥哥有办法能永远记住轻轻。
好像有些啰嗦,但哥哥知道轻轻不会怪我的,所以就啰嗦了一些。
轻轻,原谅哥哥好不好。
在离开轻轻的这段时间里,哥哥从未忘记过轻轻。
以后,哥哥也不会忘记轻轻的。
轻轻,你不要难过,
轻轻,不要难过。’
梁湾看完床单上的话,站在原地只觉得头晕目眩,耳边像是嗡鸣又像是有谁的凄厉哭嚎。
那哭声绝望又悲痛,像是失去了此生最重要的人,让梁湾心烦意乱。
梁湾勉强忽略脑海里的哭声才上前一步,却一下磕在铁床的棱角上。
白皙娇嫩的肌肤被磕破,梁湾神情漠然地起身。
绕开路,走到白骨前蹲下,拾起眼前的白骨,移到空旷的地方。
纤细的手指上没有丝毫血色,明明她的动作轻到不能再轻,指尖都因为不敢用力而发颤。
但还是感觉因为用力过度,才失去了血色。
梁湾慢慢拼凑,终于将一副骨架完整地拼好。
骨架弄好了,梁湾就去捡地上的头发。
黑色的长发似乎刚刚从头上掉落,还保留着顺滑与绸缎一般的光泽,和骨头一样散发着奇异的香气。
梁湾却极有耐心,把不听话的发丝拾拢,再将不小心从指缝滑落的发丝捡起。
小心翼翼地理顺,取下自已的头绳把发丝绑好,放在头骨旁边。
她做这一切都极为耐心,整个房间也很安静,安静到仿佛只有她。
梁湾耳边是自已的呼吸声和心跳声,还夹杂着一些陌生的悲泣。
她不知道谁在哭,可是真的好讨厌。
没看到自已在安心做事情吗?怎么可以这样打扰别人呢?
这么想着,梁湾就伸手去摸那头骨。
一点一点地,从眼窝到头骨轮廓,她似乎在比对着什么。
随后就是往下,肋骨,脊骨,尾椎骨,盆骨……
最后是那被截断了些许的左臂,然后,梁湾的呼吸乱了一瞬。
手拿起那节骨头略微翻转弧度,原本应该惨白光滑的表面,有着锋利停顿的凹陷,一笔一划地连着。
梁湾的指腹被划破,鲜血滴落在上面,顺着凹陷滑动。
殷红的液体在光滑处无法停留,它们争先恐后地为了那一点地盘争抢。
最后大多都在滴落,在地上献出自已最后一点绚烂。
‘滴答’
‘滴答’
沉重又轻缓的滴落声,一点点地将梁湾的感知放大,眼里也终于浮现了那熟悉的两个字——
轻轻。
‘以后,哥哥也不会忘记轻轻的。’
梁湾的眸子空洞而呆滞,脸上是一片空白。
只看着那白骨,眸里印着鲜艳的字。
耳边又响起嘶声的尖叫嘶鸣,撕心裂肺,似乎疯了一般地又吼又喊。
手腕突然有着温凉的触感,梁湾机械地抬头。
梁湾想自已一定是眼睛出问题了,因为她看不清眼前的人是谁,却看清了骨头上的字。
“梁湾。”
温和的嗓音传到梁湾耳里,梁湾恍然大悟,眼前的人是张起灵。
不过看不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耳边让梁湾不喜欢的哭嚎声。
她略带好奇地开口,话语纯稚执拗,像是一个天真的孩童:
“张起灵,你有听到有人在哭吗?”
所有人都看着梁湾,她的话语好奇又温和,像是在真诚的发问。
她似乎并不在意张起灵的回答,只是说着自已的感受,
“她哭得好难过,但是我不喜欢她的哭声。”
她这么说着,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在所有人面前,说出自已最真实的感受。
黑瞎子他们的眼眶都红了,王月半更是没忍住,掩面哭出了声。
梁湾似乎听到了王月半的哭声,话语间带着担忧,
“胖哥,你身体不舒服吗?怎么哭了?”
“梁湾,是你在哭。”
张起灵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梁湾抬手抹上自已的脸,
我哭了?
温热的泪水沾染指尖,耳边的哭声渐渐变得清晰,是自已的哭声吗?
可是我,为什么哭。
眨了眨眼,梁湾看清手中的白骨,还有那两个血字。
無錯書吧恍惚一瞬,想起了自已哭泣的原因。
哦,是因为哥哥死了。
迟来的痛苦铺天盖地,很快就席卷了全身,每一根神经都像是绷紧了叫嚣着。
靠着墙角,全身剧烈的颤抖也剧烈的疼痛,身上的力气逐渐被抽空。
喉咙干涩又疼痛,发不出声音,像是被人扼住了一般,疼得她无法言语。
哥哥,
哥哥死了……
死了……
眼泪大颗大颗落下,她像是终于反应过来,唇瓣颤动,最后嘶哑不堪地失声痛哭。
房间内的人在痛哭,房间外的人亦是陷入无法摆脱的深渊。
此刻他们才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
无边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