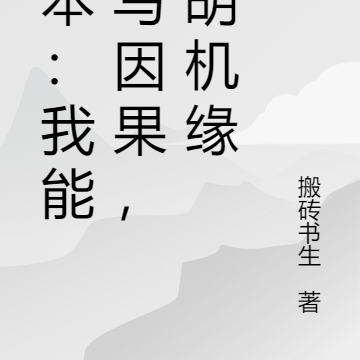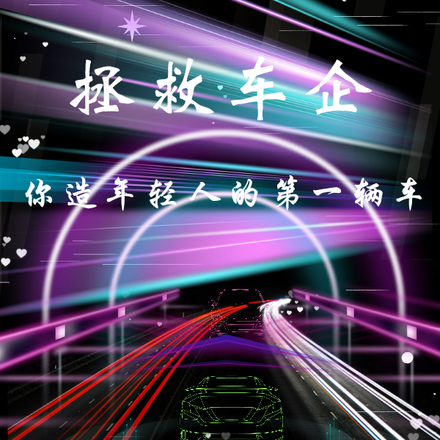第43章 商贾洗劫朝廷的刀
商贾,洗劫朝廷?
皇帝微微抬眼,放眼望向阶下,群臣神色都变了,多是一张张震惊的面容里掺杂着不可置信的韵味。
九皇子说商贾洗劫朝廷,这话是极重极重了。
什么人做得出洗劫的事情?
寇匪。
对于寇匪,朝廷无论走哪条路,最终的选择都是——扫荡。
简言之,九皇子是认为朝廷处理东海鱼患的方式是要扫荡齐聚东海的商贾吗?他不知道商贾背后站着的都是谁吗?
真是年少无畏,且无知!
“你是说,朝廷平抑鱼价,正中商贾下怀?”皇帝看向小儿子,眯着眼忽然觉得有些陌生。
“是。”明海一脸释然,索性直言:“目前来看,商贾手里有两把刀。”
“刀?”
“劫财的刀。”
皇帝沉默一会,又看了看群臣的反应,几乎是同时,前几排的文臣武将都皱起了眉头,文臣是在思索“刀”,武将是在疑惑怎么会突然说起“刀”来。
“你继续,那两把刀。”
“是。”明海一拜,“第一把刀,刀在官价。”
“海鱼量大,按理来讲鱼价应当下跌。东海连续三年鱼潮,渔业势头虽然盛极,但由盛而衰却也极快,当第一间鱼铺开始降价增销,第二间就会马上跟进,然后是十间,百间,再到一州之地,最后是全国。”
“而一旦势衰,鱼商势必火速清仓,加速逃离渔业之衰期,若是……若是……”明海想作比拟,眼里一亮,“若是依仿军势,我们管这个现象叫作,溃散!”
大殿左侧忽然传出一阵齐整的惊呼,都是披着武袍的将军。
他双手不自觉地抬起,张而收,左指右压,思绪飞快地道:
“朝廷,就是统帅,是绝不容许溃散出现,假使出现,也要及时扼杀住溃散的势头,避免影响到其他军队。”
“东海商贾知晓朝廷的难处,却不加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假使,国家常年渔业流通的银钱是一百万两,而在东海鱼潮期间,鱼量上增十倍,父皇觉得鱼价应当多少合适?”
明海说到兴起,有些期待地盯着眼前的人。
大殿瞬间静了,皇帝皱着眉头看他。
明海尴尬一笑,撤回了一个期待,低下头微微沉吟,“呃,这个……鱼价应当下衰……下衰十倍,如此才能符合全国渔业的流通规律,也就是在一百万两上下波动。”
“但这是最理性的情况,而人心是难测的,其可怕之处在于——盲目。”
“鱼价一旦下衰十倍,势必造成渔民恐慌,届时不仅价格会进一步下探,就连各地渔业都要受到冲击,轻则节衣缩食,重则渔圈荒废,此渔圈不止一家,更可能是一州,乃至全国。”
“故而,官府必须救市!”
他握拳,轻轻挥摆,神色出奇的坚定,“救市是用国库,若鱼量十倍,而在官府采买之下,鱼价仅下衰五成,那么全国渔业流通的银钱就有五百万两。”
“其中,只有一百万两是本就在鱼市流通的银钱,还多出四百万!”
“这也就意味着国库要拿出四百万两来救市,而这四百万两中,少部分进了渔民的裤腰里,大部分会被商贾赚去,因为商贾把控了渔业的销路。”
“这就是儿臣所说的第一把刀。”
大殿之上忽然躁动,像是憋足了一口气的人突然松口。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其中户部尚书彭纛最是明显,从原先的龙钟老态一下子精神起来,苍白的脸上像是多了惶恐。
皇帝的手微微抖着,神色有些阴沉。
朝中当前只有几个人知道,九皇子所假设的鱼量……
不止十倍!
如果论述正确,救市的银两也就不止四百万。
太子神色极其难看,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弟弟,心里惊涛骇浪:这还是那个坊间传闻里不学无术、开府半载就花天酒地的九皇子?
皇帝霍然回身,对上太子错愕的目光,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阴得可怕。
“父……”太子连忙垂首,下意识就要唤出声来。
片刻,皇帝看向明海,沉声说:“你,继续说下去。”
明海浑身一凛,父皇那声音很沉重,还有些沙哑,好像藏着许多怨气。
怨气,撒出来就是怒,怒就要有人接着,而满朝文武,谁能来承担皇帝之怒呢?
他没时间多想,思绪再起,接着说:“儿臣以为,第二把刀来自商市。”
“董大人说的对,农事关乎国家之根本,一农兴则万事兴,如果粮食不足,国家就会贫困,国库里有再多的银钱也无济于事。”
“鱼,是粮也。”
“东海鱼潮,国家的粮食得以充裕。”
“但我们都知道一个规律,粮价高万物价格就贱,粮价低万物价格就贵。”
“因为粮是根本,有了足粮,百姓才会去考虑购买布织财物;而如果粮食短缺,百姓就会不惜一切去购买粮食,布帛也就没那么珍贵了。”
“现在粮鱼充足,未来东海三州势必物价高涨,也可视作繁荣之象。”
“万物贵,则商贾此前囤积之货物就会超利,低买高卖收割百姓,而东海渔兴,三州百姓之钱袋子又是依靠国库平准所得。”
“故而,百姓所得的国库赈银又要被商贾拢去。”
“这就是洗劫朝廷的第二把刀。”说到这里,明海微微抬眼,只觉得皇帝的目光冰冷,在他的脸上狠狠剐过。
“而且,三州之繁荣是由东海潮起,必然会因东海而潮落。”
明海回首,朝司农寺大卿的方向看了一眼,“儿臣以为,治国当守以稳为先,而后图进,以农为基,工商并行。”
他一席话,群臣皆为震撼。
有臣子探着脑袋,想要确认说出这些话的人是不是昌王,是不是那个宫里文贤都说不学无术的皇子。
其他皇子看他的眼神也都变了,说不清是惊讶还是……畏惧?
很明显,这个弟弟在宫里藏学了!但他为什么要藏学,为什么开府后整日沉迷酒色,又是为什么在此次朝会上大展其才。
商贾洗劫朝廷的理由,他解释了,群臣无一人反驳。
就像是一次考试,太子和二皇子是开卷,其他皇子闭卷,而闭卷的皇子里,窜出来一个年纪最小的,却拿了比开卷的两位哥哥更高的分数。
父皇和群臣批阅,都看见了九皇子卷上的两把刀。
所有人都很惊讶,沉默着在卷子上打了高分。
“如何解?”皇帝问。
“不知道。”明海如实回答。
“不知道?”皇帝一愣。
明海拢手躬身,只能看见父亲腰下袍翼,翼上黄金纹龙栩栩如生。
“儿臣不曾了解东海三州的具体情况,此前所言仅是儿臣个人之见解,若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还望父皇恕罪。”
“不了解……”皇帝念叨了一句,嘴角露出了一抹转瞬即逝的笑,他转身走到正中,皇子们连忙低下头。
“彭纛、董正!”
“臣在。”阶下臣子再出列。
“昌王说的,是否认可?”皇帝朗声问,目光灼灼。
“这……”彭纛犹豫。
“昌王殿下灼见,臣附议!”董正已然作礼而拜。
彭纛愣了一下,容不得自己多想,下意识地也一并礼拜下去。拜下去的瞬间,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知名的惶恐,此前的从容荡然无存,
“彭尚书,你觉得呢?”皇帝大步走下来,腰剑攒动,透着藏锋般的威严。
“臣,附议!”彭纛压着声喊。
“既然如此……”
皇子们齐齐回身,拢手躬身对向阶下站在过道中间的身影,群臣纷纷侧身正对陛下,金赤袍影映入所有人的眼帘。
“彭纛、董正监事不利,致使各州渔业动荡。”皇帝肃道,“你二人皆是朝中大臣,朝后朕与都察院商议,再定你二人误事之罪,可有异议?”
“…谢陛下圣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