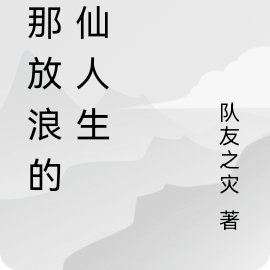第10章 羞辱
傅老太太看着家庭医生面色凝重的收起听诊器,忍不住问:“他怎么烧得这样厉害?”
家庭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许轻辞一眼,缓缓道:“少爷在高架桥底下,差点车毁人亡,本来就失血过多受了惊,又衣着单薄的在祠堂跪了那么久,染了风寒。内里热气一激却纾散不出来,自然病势汹汹。”
许轻辞眼眶突然酸涩得厉害,胸口涨涨的,疼的无以复加。
她知道没有人会再为她遮风挡雨,可是,看着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为了护着别的女人,连命都不顾地跑来忙着堵自己的嘴,她还是觉得一阵悲哀和难受。
原来傅容时并不是没空,只是不能为了她有空而已。
刚发泄过后的平和心态又被这道带刀的旋风给刮得稀巴烂。
她怕眼泪掉出来,忙转过头看向别处,勉力忍住。
“少爷晚上休息不好吗?这两天看起来都没怎么睡的样子。”家庭医生却声音冷冷的叫住她,盯着她的眼神极具压迫和质疑,“少奶奶照顾少爷饮食起居的时候难道就没发现少爷身体的异常吗?”
她和傅容时根本就没有住在一起,自然无言以对。
许轻辞唯有沉默。
傅老太太盯着她身上过于宽大的西装看了几息,似乎想到了什么,嫌恶地皱眉,问:“你不说话,是认为没必要跟我这个半截入土的老不死解释什么是吗?”
许轻辞长睫抖动了下,连脚指都忍不住蜷缩起来,“妈,不是这样的,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没有发现容时他……”
傅老太太声音陡然尖锐起来,眼神犀利的像是要把人射穿:“住嘴!发生了什么,你打量我不知道?”
深吸了一口气,她接着疾言厉色地喝道:“再不收起你那龌龊的心思,别怪我不客气,我们傅家的男人你勾搭了一个还不够吗?我绝对容不下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在傅家!你给我跪下,跪在容时的床边,他什么时候醒,你什么时候起来!”
傅老太太毫不留情的给许轻辞下了定义,不留一点面子。
完全不顾房间里还有家庭医生和候着的保姆。
三年来,面对傅家的长辈,许轻辞的情绪一直绷着,可是到现在,她却有点绷不住了。
这种压抑又窒息的生活,难道她真的要忍一辈子吗?
许轻辞心一横,扬起眉眼,干脆利落的拒绝道,“老太太,恕我不能跪!”
在傅宅,傅老太太向来说一不二,还从来没有人敢拒绝她,更何况是她一向看不起的儿媳,当即就火冒三丈,高声喝道:“林管家,动手,让她跪!”
侯在一旁的林管家听到命令,沉着脸走到许轻辞的身边,一手压着她的肩膀往下按,一脚踢在她的膝盖处,噗通一声,见人膝盖直直砸在地上,他才收了手,掐着嗓子虚伪的道歉:“少奶奶,得罪了。”
许轻辞的灵魂像是重新被吸入到这一场可怕的梦魇里,并且毫无抽离的可能。
她怔愣的看着病床上双眼紧闭俊美犹如天神的傅容时,爱莫大于心死,声音平静到听不出任何情绪,“这样羞辱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人在做,天在看,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怕报应吗?”
闻言,老太太先是震惊,后是愤怒!
当了几十年傅家主母的她,气质和修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形态举止向来优雅高贵,从无可令人指摘的地方。
而此刻,她却像是疯了一样,扑到许轻辞的身边,揪着她的毛衣领子,一个耳光甩上去,“你竟然敢诅咒傅家,诅咒容时,诅咒我?!我们傅家容不下你这种没教养的东西!”
许轻辞抬手捧住自己麻掉的半边脸,看着傅老太太眼里汹涌的恨意,她感到一阵可笑。
这三年,到底是谁该恨谁?
她仰头,把眼泪逼回去,现实那里轮得到她多愁善感?
她不为自己筹谋,还会有谁来为她打算?
她一字一字的,“再容不下,您也容了三年,为什么容的,您心里明镜似的。只要您高抬贵手把长青街的写字楼还给我,我和傅家,往后绝无半点关系!”
傅老太太一肚子火发泄不出去,全憋在肚子里似的,脸色灰败得像是个纸人,恶毒的咒骂道,“你这种女人……简直该去死!果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母亲手脚不干净,养出来的女儿也是这种下等货色!”
许轻辞大脑一片空白,天旋地转的眩晕感让她眼前漆黑一片,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把冒出来的屈辱和愤恨一丝一丝按回心脏:“您嘴下这般留德,倒是比我和我妈高尚了许多。”
傅老太太怒了,喝道:“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许你做不许人说?当初要不是你不要脸,你以为你能有机会嫁进傅家?现在又做出这么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给谁看?你这种满脑子心机算计的女人……”
“闹完了没有?还嫌别人看笑话看得不够多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的傅正钧脸色铁青地盯着傅老太太,手背在身后,命令道:“你出来,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
傅老太太满脸狰狞的不甘心,狠狠剜了许轻辞一眼,怒气冲冲地走了。
许轻辞并不在意,她和傅老太太早就势同水火,这种白眼,她以前住在傅宅的时候,日日时时都能看到。
傅正钧盯着她看了足足一分钟,才声音清沉的道:“你妈这杆枪真那么有用的话,当年你也进不了傅家的门。真有种,就说服容时,让他和你把婚离了。别的心思打起来,只会让你处境更难,更没有尊严。”
無錯書吧原来,她一旦回击,就叫打别的心思。
她失望不已,又自嘲不已。
尊严这种东西,她真的有吗?
就算有,又有什么用?
当初,她自以为能与天争锋,对权势和资本不屑一顾,仰着高傲的头颅把尊严捧得高高的,现实狠狠驯服她之后,才发现自己连个屁都算不上。
她倔强的绷着全身的线条,低眉顺眼,一语不发。
傅正钧却从这沉默中看到了她不死不休、铁骨铮铮的倔强。
有那么一瞬间,他竟看到了竹的风骨。
像是出自名家之手的水墨画,浓淡相宜。
这孽缘!
念头一闪而过,他拧着眉心,挥退木头桩子一样立着的仆人,转身走了出去。
许轻辞塌坐回地上,束手无策的屈辱感似乎把她全身的力气都消耗光了。
所有人都厌恶她……却都又不提离婚。
还是说,长青街,藏着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傅老太太不是那种让针戳在眼里还能不吱一声的人,而傅容时……
她审视而探索的目光落在傅容时身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心乱如麻的盘算着,壮着胆子在傅容时被换下来的衣服里搜寻起来。
他有一枚随身携带的印章,重要到她曾经只略略看过一眼,就被他大发雷霆的从家里赶了出去……
如果能找到……许轻辞心里升起了微而薄的希望,聚精会神的在皮夹里翻找起来。
因为太过专心,所以她没有注意到,床上刚刚醒来的傅容时,正以一种悲悯的目光盯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