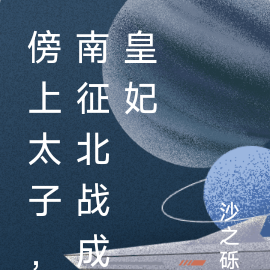第75章 叛军
听村民们七嘴八舌添油加醋地说完,他越看那女子越觉心痛,声音沙哑问了一句:“你有什么打算吗?”
篝火旁,孤零零的薛盼章蜷缩成一团,沉默不语,脸上尽是茫然,想起那个暗无天日的家,她宁愿去死!
过了许久,她才正眼瞧他,身旁身着便服的男子关切望着她,让她忽然想起祖父在世时见故人,便是这般眼神。
“大伯,我们,认识吗?”怕人看不懂她的手势,她便在地上一笔一画写了几个字。
他答非所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她自嘲一笑,在地上继续写:“爱死不死,爱活不活,打算我是没有,不过,大伯,你们居然救了我,能不能帮人帮到底?让我去你们家打杂吧,我什么活都能干。”
他不再说话,也一笔一画在地上写起了字:“我住的地方被圈起来了,你要是跟了我,也会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
“我家里人不在乎我,我已无路可退,若您不帮我,便也别拦着我去河里寻死。”
“你不怕我是坏人?”
她伸脚将眼前满是字的泥土用力搓了搓,而后伸回脚,伸手重新写:“我不知道什么是坏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人,我只知道我是孤立无援的人。您我虽是陌生人,可您救了我,祖父教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您救了我,我本就欠你恩情,我去您家打杂,是寻求庇护,亦是报恩。再者,您就算再坏,也坏不过他们去。”
“那……如果我要你?”
她静静看了他半晌,而后继续写:“如果大伯您想要一个以身相许的话本子,小女子今晚便能如了您的愿,已报您救命之恩,但过了今晚……若小女子还能活着,便是您把小女子绑了。”
宋怀玉瞧着她那张脸,嘴角轻轻勾起,语气温柔:“那,便跟着朕,入皇宫吧。”
她惊愕抬头,从刚刚到现在,她虽心中猜想眼前这气质非凡的大伯不会是寻常人,却未想会是当今九五。
……
宫里多了个奉茶侍女,后宫佳丽三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天资国容,竟会败给一个相貌平平的乡下人。
皇上经常与她眉来眼去,说是奉茶侍女,可宫里哪个娘娘敢小瞧了她去。
先皇后故去后,皇上时而暴躁易怒,可自薛侍女入宫后,皇上便消停不少,两人时常形影不离,封她为妃后更是宠爱有加,甚至一日数驭……
谁人都知皇上为何如此,故而宫中无人不叹皇上深情,可宋元安却只觉恶心。
想着相隔遥远的两位姐姐,想着故去的母后,还有身后三个无力自保的小家伙,他便觉天都要塌了。
夜深人静之时,他偶尔会回想,以前的父王是何模样?可这些年来,那个笑起来憨态可掬,一本正经起来又不怒自威的人,越来越看不清容貌。
越来越清晰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是十天半月只见上几面,一见面便问他功课,催他学习的“皇帝陛下”。
每每想到这些,宋元安总忍不住夜晚偷偷哭泣:“母后,今儿是您的忌日,那个老东西……连您的忌日都忘了。”
唯有在自己的太子府里,他才可卸下一日疲惫,同那孤灯烛影中的自己一桶满醉:“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和您一样的人,还带她……去吃咱们种的苹果,他怎么能这样?”
他笑着,含着泪,仰起头,不知是笑天上的母后,亦或宫里那温柔乡里的皇上:“您说让我别怪他,可他何曾把您放在心上,他……”
这些年来,他看着父皇将那女人带回宫来,明明只是个奉茶侍女,如今却已成了宫里恩宠正盛的晚妃娘娘,甚至还让她诞下了一名皇子,一个当他儿子都绰绰有余的弟弟……
他父皇有什么妃嫔他管不着,可那人却长的相貌平平,是个哑巴,还会医术。
父皇怎可如此亵渎母后?
他怎可如此!
想到无情无义高高在上的人,群狼环伺的后宫,宋元安想同眼前的灵位说声累,可想着身后的妹妹弟弟,他便就着泪水将千言万语吞入腹中。
……
“启禀皇上,秦州暴动。”
“启禀皇上,宁州暴动。”
“启禀皇上……”
景顺十年初秋,大启各地有人蠢蠢欲动,朝廷百官宛如热锅,许多官员都主张出兵平乱,另一批官员不同意此事,两方争的不可开交。
那所谓的叛军,正是景顺前一年的冬日,而今高高在上的皇上曾承诺过的那些人。
烈刀的发展方向仍是草原,故而对于获得的大启领土采取了宰杀统治,他们一边打压着那里的百姓,一边又享受着他们提供的东西,他们最初高喊着烈刀更好的大旗。
烈刀人不需要百姓交赋税,日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们被血洗了一遍后“很高兴”,天真的期待起来。
烈刀人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如同温水煮青蛙,那里的百姓过起了行尸走肉的日子,日日成群结队去干活,干完活回家歇歇,周而复始。
烈刀人说话算话,他们不需要百姓们交税,他们将百姓们所有的收获都被聚拢到一起,留下够他们吃到来年庄稼有收成食的分量,其余的全部上收,年复一年……
种出庄稼的百姓们可以吃粮食,可以吃饱,吃饱了继续干活,可他们,没有支配权!
他们日日白干的活不多不少,可剩下来的自由时间并不够他们养家糊口,眼睁睁看着村子的私塾破旧。
他们的儿女无需读书。年纪小就放牛放羊,年纪稍微长点便跟着大人一同下地干活。
传承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延续血脉,他们卖妻卖女,倾家荡产,只为给自家的男丁娶上一个暖床媳妇,生下孩子继承他们的衣钵,延续香火。
只有孩子多,干起农活来才能轻松,只有孩子多,才能减轻家里负担,然后举全家之力供养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带着全家走向新生。
一切都按照烈刀的计划走,统治下的大启百姓们也曾奋力反抗过,而他们奋起反抗争取更平等利益的昙花一梦,换来的,是官府的雷霆之怒。
在烈刀马蹄踏上这片领土并开始统治时,已明明白白告诉过这里的百姓“最新的烈刀刑法”:“一户有反者,屠五户,五户有反,屠五族,十户有反者,屠十里!”
人口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样惨无人道的法律,在这片土地上已然执行过许多次,因为他们从不把他们当成烈刀的百姓。
人总趋利避害,若温顺,尚且能活,若反抗,便得拖家带口,莲乡带里。
前车之鉴足够让他们停下反抗脚步,乖乖顺顺当那被困在无形羊圈里的小小肥羊。
寒门出贵子的奇迹永远不会出现,因为这里的做官第一要求便是会骑射,会烈刀语,穿上官袍的第一件事情是高喊:“烈刀威武,打败大启!”
故此,但凡有点风骨的学子都不愿去当官,可理想总向现实低头,那些归于现实的人们成功迈过那一关又会发现,所谓的官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吏,被呼来喝去的鹰犬。
官吏,官吏,官与吏,天壤之别。
有没有人站在这片土地上向南而望,无人知晓。
可大启的土地上,有人等了十年,他们代表着许多人,他们或胸怀家国同胞,他们或有钱有势,或是身无分文,只求一口饱饭的无路之人。
他们来自四方,他们组成了一支支不听命于朝廷的“叛军”,他们向官府抗议,他们昂首挺胸向北而行,拿着手中武器视死如归,高声喊着:
“北伐,复我河山!”
“北伐,复我河山!”
“北伐,复我河山!”
官府的人拿着武器指着他们,可他们只是拿着手中武器仰天长举,一步步向前。
百姓们没有夹道欢迎,但心中却是骄傲,这些年他们交赋税交的比较勤。
官府不敢派兵镇压,又不敢放他们离去,可有些地方官员明目张胆放他们出境,摘官帽,脱官服,上表请罪,吾皇万岁。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是居心叵测,浑水摸鱼,可这样的一支支“叛军”,朝廷若是真派兵镇压,便会寒了人心。
这些年大启攒的钱四舍五入花出去不少,国库余钱虽够支持一场北伐,却也只是勉强够,所以朝廷不能发兵。
将风调雨顺寄托于神灵,向来都是无奈之举。
“若由着他们聚集起来,他们最终会不会北伐尚且难测,且,就算他们真是北伐,光靠他们断然是撑不起的。”
大殿之上,已是风神俊朗的皇太子傲然而立,拱手向着龙椅上满头银发的九五至尊请命:“父皇,儿臣愿往。”
他父皇对他越来越冷淡,他是一国储君,中宫嫡子,只要不犯错,便可坐等那高高皇位,可一个没有实权或威望的人,坐不稳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