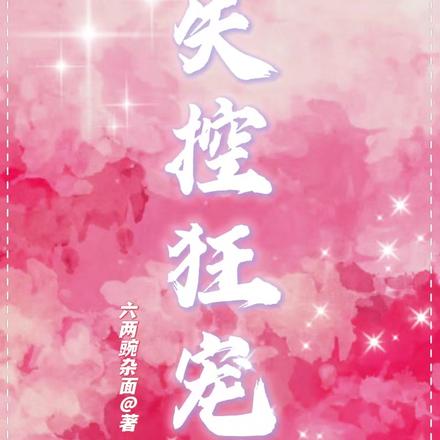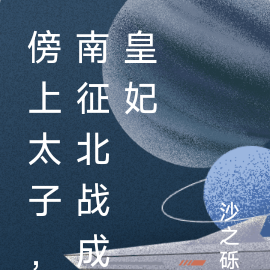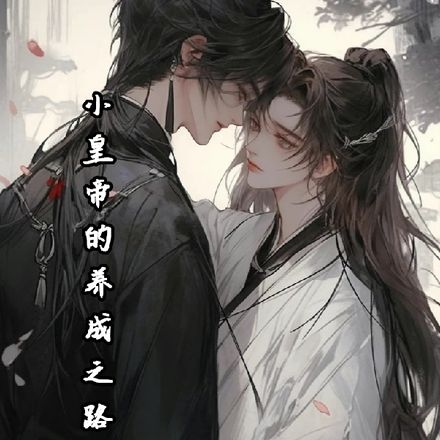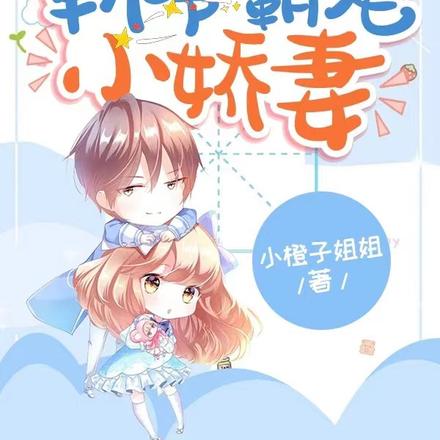第74章 祭天
“启奏皇上,秦州大水…”
“启奏皇上。宁州大旱…”
“启禀皇上,和州地动…”
景顺七年的夏日炎热,正和殿内,大启天子看着折子,只觉胸闷气短,手中笔欲落不落,粗叹一声后搁下笔,起身往殿外走,小宝沉默无言跟在他身后,脚步若轻似无。
比起前几年的风调雨顺,今年大启的运道实在不好,不是这旱了,就是那淹了
天灾跟商量好似的,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致使民间不少人家破人亡,百姓苦不堪言,朝廷官吏也鸡飞狗跳。
下面一层层报上来要银粮,刚刚缓了几年的国库一下子空了大半,眼看着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少,陛下自是心烦意乱,加之今年初春,轩辕左丞相和司徒右丞相因年迈致仕,心里便更烦闷了。
虽说左右丞相的位置有人接任,可用习惯了的一双手忽而不在了,陛下也是会伤心的。
司徒右丞相虽说性子圆滑了些,但为人处事实不错,陛下很喜欢他,他致仕前,陛下还赏了些东西给他颐养天年。
轩辕左丞相更不必说,说他直,他又并非是那不通情理之人,许多事同他讲也能说得通,可说他通情达理,在许多事情上他又很固执。
固执到舌战群臣,同陛下意见不合时,甚至不顾以下犯上之罪名可能会牵连家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敢大意妄为指着龙椅上的陛下开口便骂:“陛下,你肩上之责重如泰山,怎可任性妄为?你任人唯亲,而今又以私废公,竟想徇私枉法,一国之君如此…实在昏聩无道……”
陛下虽登基不过几载,但手上也有些人,可到底轩辕左丞相是三朝老臣,且他说的并无过错,陛下即使被他骂的狗血淋头也没罚他,毕竟左丞相骂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昔年景宗,过宗,左丞相也骂过。
陛下虽未罚他,却也不让步, 逼的轩辕左丞相撩袍跪地不起,高喊:“陛下三思!”
轩辕左丞相是朝堂上的老骨头,虽有人看他不顺眼,亦有人跟着他一起跪,哪怕跪到百官散朝也不肯起身。
陛下极为不耐,扭头便走了,他们便乌泱泱跟到陛下处理政务的正和殿,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继续撩袍跪地:
“请陛下三思!”
陛下只当没看见他们,自顾自处理奏折,有些奏折扫一眼便甩到一边,有些奏折看了后他会想许久,谨思缓缓在上落下几字。而后盖上宝印,放到一旁,接着又翻下一本。
大殿内静悄悄的,轩辕左丞相他们也不闹,就眼巴巴跪着,乖巧温顺似端庄闺秀。
小宝记不清他们跪了多久,只记得食欲不佳的陛下都吃了三碗饭,视死如归的轩辕左丞相成了第一个倒在地上的人,陛下叫人给他请太医,接着又派人送他回府。
主心骨一倒,也不知是不是身体不大好,其他大臣们后来接二连三的晕倒,陛下派人将他们送回府去好生照料。
陛下暗暗松了一口气,可左丞相是朝堂上有名的老骨头,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肯罢休的?
晕倒的左丞相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儿孙叫到身边来交代后事,之后才入的宫。
听说入宫之前,轩辕左丞相的晚辈们跪在地上,拽着他的衣角泪流满面劝他别去,年过花甲的三朝元老一脚踹一个,怒气冲冲地往外走,走之前对着儿孙们说:
“君目浊,臣当引其路,以正其行,为臣者若惧君怒而不劝,何以为臣?任君浊目专行,要臣作何,君独断专行则天下必乱,天下乱则万民难安,万民难安则生反心,叛乱四起则社稷危。启今孱弱,外患趁虚而入则亡矣………我轩辕风,宁当死谏之臣,不为苟延残喘之亡国奴犬!”
后来左丞相又风轻云淡地入了皇宫,那些与他一同跪地请旨的大臣们,醒了之后便紧随其后入了皇宫,因着那时刚好上朝,左丞相他们便没闹。
上朝时大家都各司其职,上完朝之后那帮老家伙又紧随其后跟着陛下去了正和殿,接着又像那日一般,跪地便喊:“陛下三思!”
陛下还是不理他们,老家伙们气得吹胡子瞪眼,但为了不妨碍陛下办公务,还是只能乖乖跪在那里温顺乖巧如端庄闺秀般安安静静。
之后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少卿接连在朝堂上弹劾北唐家,虽然北唐家因贪污本就在风口浪尖,但更多的罪证意味着皇上要将北唐家流放的决定越来越像轻拿轻放。
可即使这样陛下也仍不愿按照大臣们的意思来处置北唐家,气得温顺乖巧在正和殿跪着的左丞相在哭着骂,逼的陛下换了好多地方,可那帮人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后来陛下又把地方换了回去。
此事被先皇后得知,先皇后不忍陛下为她因私废公,劝了几句,陛下没办法,只得派人不让先皇后出春凤宫。
可先皇后只是一餐没吃饭,就逼得日理万机的陛下眼巴巴地去春凤宫喂她。
先皇后虽然吃了饭,但许是未给陛下好脸色,以至于陛下回正和殿时没精打采。
见陛下回来了,老家伙们又把之前陛下离开时的说词说了一遍,可这些日陛下已然养成了出门被念一遍进门被念一遍的好脾气,无动于衷。
次日朝堂上,陛下硬着头皮差人宣布了对北唐家的判决,大臣们虽然依法照作,但难免有一些不服气。
那日,正和殿里,失望至极的轩辕左丞相彻底没了耐心,在陛下的一声“朕已有决策”后彻底爆发:“陛下,您乃一国之君,行事万不可如此!”
陛下没有回答左丞相,左丞相竟是拔出了私带进殿的匕首指着陛下,痛心疾首道:“陛下知民间疾苦,却因私废公,臣等苦劝已久未果……可见陛下并不在意江山社稷……君昏愦,臣之罪,臣这就以死去见景宗皇帝,向景宗皇帝告罪去!”
可陛下却不紧不慢地从宽袍大袖里也掏出了一把匕首,抵着自己的脖子说:“朕与丞相同往!”
“陛下!”
“北唐太师,护国郡主对社稷有功,你们怎都不提?朕会将有罪之人流放,如果你们觉得朕判决不合你们的意,那便换个皇帝吧。”
一帮跪着的人竟把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逼到此等地步,小宝心生哀叹, 陛下说到底只是一棵树,是一棵没有长大的树,却妄想去笼罩整片天空。
地上的草说到底只是草,自己立不住,随便来阵风都能倒,遮了天空,又有何用?
原本坦然赴死的轩辕左丞相泄了气,扔了手中匕首,头扣于地,大吼了一声:
“陛下!”
陛下没有回答,重重将那把匕首放在案上,接着坐回龙椅上继续批奏折,逼得一众跪地朝臣瞪圆了眼。
后来先皇后坐着凤辇来了,陛下拿着披风冲出大殿,走到凤辇旁边着急地往她身上披,一边又动怒斥责随行的宫女内侍,日日跪着的大臣们一瘸一拐地跟出来跪了一地,一个个满眼哀求看着先皇后。
先皇后跪在陛下面前,陛下跟着先皇后一起跪在了地上,小声地说了一句话,气的先皇后不断朝陛下做手势。
陛下扶起她进了大殿,没过多久,先皇后就自己先出来了,大臣们进去之后,陛下终于松口,同意处死北唐家一些人以正国法。
自那日起,陛下虽然总想着去见先皇后,可每次去了,都跟犯错的孩子一样矮了一头,先皇后也因忧思过重,景顺六年初秋便走了。
先皇后走后,陛下连着几日茶饭不思,礼部拟了许多谥号,最后大臣们又一同上书要给先皇后定谥号为“昭慈慧悯皇后”,这也是满朝文武与陛下意见如此相同的一次。
后来陛下把先皇后生前住过的寝殿封了起来,除了一些洒扫宫女,再无人可踏足。
虽说陛下对此事颇为介怀,但轩辕左丞相致仕的时候,陛下曾看着老人的背影叹一声:“父皇,真会挑人啊。”
……
今年各地天灾不断,大臣们忧心忡忡,皇上要去广灵山开坛祭天,留太子监政,祭完天有官员提议陛下去周边转转,体察民情,宋怀玉应允。
“有人?〞青山绿水间,一名身着便服的侍卫指着河边喊:“哎,他们在干什么?”
宋怀玉坐在树旁,神色淡淡:“你们几个快去将人救下!”
只见远处有一人被一群人追赶着,不得已往水里行去,岸上的人指指点点着,那人在水中央不断挣扎着。
几名侍卫冲到河里把人给救了起来,那女子浑身无力咳嗽了好一阵,起身又继续往河里冲,几名村妇冲上去抱着她嚎啕大哭:“不要做傻事……”
“孩子别做傻事……”
旁边已然吵了起来,一名侍卫中气十足指着那帮村民愤愤不平:“干嘛的干嘛呢?光天化日的就逼死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不是你们把这姑娘往河里赶的吗?现在假慈悲?”
“这是我们村子的事,干你什么事?”
“就是就是!”
“她是女子,这么大岁数了不去嫁人,居然想着寻死,难道还有理了不成?”
“她就是个不孝女!”
“什么不肯嫁人?装什么装?了不起啊?其他姑娘都是到岁数让嫁就嫁,就这小妮子死都不肯嫁,我看啊,是早就在外面和人勾搭上了。”
“若非失了清白没了完璧之身,怎不肯嫁人?贱女人!”
“……”
村民们的污言秽语,把侍卫们听得头皮发麻,怪不得这姑娘要去死,实属可怜。
那女子迷迷糊糊听了,更是愤然欲死,泪流满面地往河里冲。
远处的宋怀玉好奇地走过来想看个究竟,见地上相貌平平的女子,愣了神,而后赶忙冲过去,抱着她泣不成声……
“看看看看,让我说中了吧,这就是她的野男人……”
“话说,这群人看着很有钱啊,唉,你家姑娘真厉害。”
人群中的老两口沉默无言,男子走上去就给宋怀玉怀中的人儿狠狠一巴掌,直把人打得眼冒金星。
耳边嗡鸣不断,可女子却仍能听清耳边亲人的锥心话语:“贱人……你这个贱人……不要脸的贱人!”
那男子刚上前便被侍卫阻拦,但那一巴掌还是结结实实落在了那女子粗糙脸上。
“滚开。”
反应过来的宋怀玉看着怀里楚楚可怜的人儿,怒火中烧地将那上前来的男子踹翻在地,又转过身抚摸那人儿的小脸,梨花带雨地看着她,身子一颤一颤,轻轻话语似春风醉人:“你没事吧……”
村民们欲要动手,可抬眼一看,竟发现周围不知何时围来了上百名身形魁梧的男子。
柔弱身躯发抖,怀中女子仰面朝天,哭却无声。
把宋怀宇心疼到无以复加,紧紧地把人按在怀里:“别怕……”
这并非是理直气壮的世道,而是谁拳头硬谁有理。
……
那女子姓薛,名盼章,是家中长女,上有父母和祖母,后头还有两个弟弟。
二弟十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因无钱医治,早早便没了。
而今她三弟要娶亲,女方狮子大开口要二十两银子,家里人想让她弟弟换个媳妇儿,她三弟吃了秤砣铁了心,说此生非他不娶,若是不帮着他娶妻,他便……让薛家绝后。
她三弟性子野,向来敢说敢做,薛盼章的祖母和父母被吓得不轻,只得东奔西走借钱,可离二十两还是差了十两。
薛盼章之前进城卖过一些草药,恰好被一名商人看上,那商人见她家困难便出手相帮,这一帮就是五十两银子。
礼尚往来,那商人提了自己的要求,要薛盼章做自己的小妾,薛盼章不愿,她虽是天生的哑巴,但她跟着祖父学过不少东西,只是胎没投好。
能识文断字替人诊脉的本领,让她不甘嫁给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去做低贱小妾。
可她家里人收了钱,逼着她嫁,她三弟不忍心,之前便已同父母讲过,将钱退了去,自己不娶也罢,可寻个便宜妻子,可她父母拿了五十两银子不肯松手,便只能舍了她。
她三弟将她偷偷放了,她对村里了如指掌,可她终是孤身一人,连夜跑了几里后到了此处,无路可退之下,毅然决然冲到了河里,本想着此生一死百了,却没想会被人相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