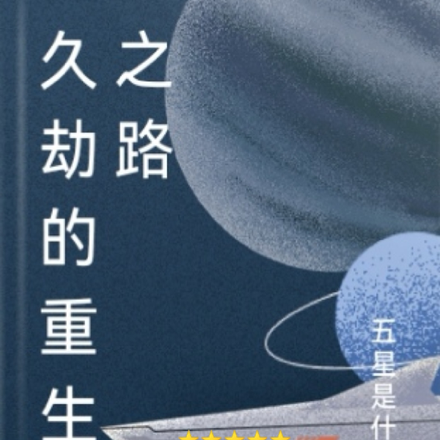遭劫難,西川迷風雪
遇白狐,書生驚破魂
山中無年月,世上多浮沉,十年光陰如水流。
這一年的冬格外的冷,雪也格外的大,紛紛揚揚的下了好幾個日夜,大千世界盡顯銀妝,西川群山成雪之圣地,杳無人際。
有詞唱贊:
風度暮云,
月落漢霄,
西嶺千里飛蝶,
嬌柔不堪人憐,
詠無聲,
自翩躚。
一宿間,
江山褪罷霞裳,
幽泉珠簾斷,
蒼崖玉劍懸,
碧水青山,
共素顏。
端的是風雪連天、冰凍三尺,人畜俱匿,偏偏有一天,綿綿群山間出現個人影,此人蓬頭垢面、衣襟爛縷,背負一個大包袱,正手腳并用,慌慌張張的爬行在陡坡,大雪封路,崎道艱難,他一進三退,連連摔跤,樣子極為狼狽不堪,濃霧未散盡,晨曦未照進,深山之中一股陰戾森寒之氣繚繞浸骨,野鳥巨梟歇落在密林茂葉之中,靜斂著翅,轉動著幽冷的眼睛,朔風刮過,雪濺枝頭、寒生心底。
這人卻氣喘吁吁、大汗淋漓,不知是疲憊的熱汗還是驚懼的冷汗,垂著頭不敢斜視,可巧一只巨鳥“突的”尖聲驚叫,撲騰著雙翅從他頭頂飛過,帶起一陣寒風與簌簌雪落,這人嚇得心中大呼“哎呀有鬼”,連聲都不敢出,腳下一滑俯摔在地,手抱著頭半天不敢動,靜聽了許久確認沒有動靜,這才慢慢的抬起頭,驚恐的打量四周。
臟兮兮的臉龐仍顯清秀,他的目光在林間灌木中警戒的察看,突然停落在遠遠的一處叢林,眼中升起恐懼,全身顫抖,寒意從心口往外擴散,再也忍不住,大叫一聲“妖怪啊——”白眼一翻,暈死過去。
氤氳濃霧中,隱約可見一位白衣女子在翩翩起舞,白衣勝雪,輕盈無骨,踏雪無聲,她始終以背相向,一頭烏黑的長發毫無修飾,隨著舞姿變化在身后婉然靈動的搖擺,聽得有人驚呼,俏生生的回轉,露出一張不染人間煙塵的清麗面容來,她一眼便看見暈倒在地的少年人,飄然而至。
少年人醒來時發現自己好生的睡著木板床,身上蓋著柔軟的錦\\被,詫異萬分,明明記得在山上爬行時遇著了女妖,怎么又睡在了床榻上,這質地上乘的棉被是哪家的物什,哎呀呀,莫不是小生連日里又驚又累,竟暈在山道旁做起美夢來?閉眼又怡然享受半刻,心中狐疑,伸手入口,咬痛食指才知道自己并未入夢,一驚而坐起,翻身下床,四下打望,屋內別無長物,唯有桌上放著一只小小的香爐,無全香火,可見是年久失修的破廟,稍稍放下心,這定是哪位不畏嚴冬進厚雪的樵夫好生救起了小生,想這鋪天大雪之歲、萬禽棲窩百獸蜷眠,若非恩人相救,小生豈非要凍死在荒山野嶺?哎喲,那可正是功名未就反成野鬼,好生凄慘?小生且出去瞧瞧,若是恩人仍在,小生定要三磕頭三作躬以謝救命之恩。
正要舉步,木門外無聲無息的轉入一位白衣女子,這女子肌膚晶瑩似玉、皎白無瑕、美目盈盈似秋水涓涓,娥眉斜飛如遠山淺\\淺\\,身著雪白衣裙,飄逸不似人間姝麗,好象廣寒仙子降臨人間,可是這等荒山深林中怎會有仙子,莫非狐精妖女?哎呀,看她烏發如瀑齊至腰、看她白膚白衣無塵染、看她孤身一女現嶸林、看她閑笑無羞眼兒俏,憶起適才見到的女妖背影,頓時臉色大變,連呼“妖怪!妖怪!”,四處尋找藏身之地,偏這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別無他物。
白衣女子笑吟吟的看著他驚慌失措,半倚在門口,不進不退,少年人想鉆進床底下,不料床沿太矮,幾番努力竟鉆不進去,無奈只得縮成一團,駭然盯著白衣女子,顫聲問:“你……是妖怪么?”
白衣女子笑意漸濃,輕啟朱唇,悠悠回道:“我是千年狐貍精。”聲音清冽飄忽,恍若來自天際,直嚇得少年人連聲怪叫,跌足亂跳,幾乎又要暈倒,這才掩嘴大笑道,“呆子,不過是騙你的,我是人。”
少年人哪里肯信,緊蜷在床角,驚疑的抬起眼,顫抖著打量白衣女子,將頭搖得撥浪鼓似的不肯相信。
白衣女子抿嘴一笑,緩步走近,柔聲道:“你莫怕,我也是迷了路在這里住的,并不是什么妖怪。”
少年人仍是不語,惶惶然瞪著她,因無路可退,只得竭力將身子縮蜷,牙齒咬得咯咯作響。
白衣女子突然伸手在他手背上一觸,笑問:“可有感到熱氣?妖怪哪有體溫呢?”
少年人低叫一聲,象是被毒蝎蜇了一樣倏的縮手入懷,越發顫抖得厲害,轉念又想,曾記得先生有言:鬼乃至陰、妖乃至邪,行無蹤、體無溫,區分于人。眼前這女子雖然膚色白瑩如梨花綻雪,行為亦怪異無端,不過手背溫似常人,哦,想來不是妖怪了,既然是人,就該知男女授受不親,這女子生得這樣艷麗,也不知是哪家的閨女,也不坐守閨闈、也不矜持避諱,膽敢邁蘭房、出庭院、獨上深山,這樣荒疏禮儀、不避人嫌,實在有欠淑嫻,定不是那名門望族的大名閨秀,興許是哪家樵夫農戶的小家碧玉,生于窮鄉僻壤、長于村頭山陌,自小不曾學得閨儀禮貌,才敢這樣不驚不羞,言行放肆!啊唷,我顏如玉世代書香門第,家風文儒嚴謹,男女之嫌尤其講究,我雖趕考途中受風雪、遭強盜,也不能私會女子,授人言辭,還是速速辭去為好,這才小心翼翼、驚魂未定的爬起身,作躬道:“小生顏如玉,杭州人氏,上京趕考,迷道山野,還請姐姐指路則個。”
白衣女子轉身走開,裊裊娜娜的半依門框,巧笑倩兮,不緊不淡的看著他,早將他一番心事看了個通透,心里暗笑,這書生果然癡得很,流落到這荒山野嶺,衣襟爛縷、食不充口、隨時可能被山中猛獸吞吃,還講究這些酸儒,防女子甚于猛獸?她吃吃一笑,問:“原來還是個讀書人,這方圓百里皆無市鎮,人煙稀少,自杭州去京城,怎么走到這里來了?”
顏如玉黯然嘆道:“原來是沿江逆上,不想一上船便遇到強盜,吃了迷藥,一覺竟睡到入了川,不但銀財被搶去,就連隨行的書童也不見了蹤跡,只怕是兇多吉少了。”說著滿目哀愁,竟是泫然欲泣。
白衣女子不禁為他柔弱模樣又驚又笑,寬慰道:“你也莫傷心了,既然入了川也可以北上,又何必非要進山呢?”
顏如玉又蹙眉道:“不料剛入川又遭山賊\\,被擄入山寨,興許是見小生身無分文,又丟出寨子,這大雪茫茫一片,盡已掩埋了道路,萬里一色,這才迷了道。”
白衣女子笑起來,道:“你倒是撿了條命呢,雪深路滑,這時候你也出不去,不如就在這里住上一段時間,等開了春,雪消了再下山罷。”
顏如玉低頭不語,啊唷,莫非說小生近日竟下不得山去?那可好何是好?
白衣女子繼續道:“這破廟雖然簡陋,倒也可避風雪,你背的這包袱里可都是書?”
無錯書吧提到書,顏如玉臉上露出笑容,答道:“不錯,都是書卷,亦是老天有眼,竟然都沒讓那些強盜搶去。”
白衣女子心想,呆書生倒是有趣,強盜向來是搶金銀財寶,怎么會稀罕你的書?嘴上道:“如此更好,你住在這里,十分清靜,也可用心功讀,衣食之物,我給你便是。”
顏如玉訕訕的看著白衣女子,雙頰微紅,囁喃道:“姐姐可是也住這里?”
白衣女子一愣,繼而大笑:“我不住這里,書生休要胡思亂想。”笑聲如銀鈴一般清脆悅耳,雪白如玉的臉頰也略泛上微微粉色,映著窗外雪花紛紛,恰如那早發的桃花,好看得緊。
顏如玉雖然也覺笑聲好聽,心里卻微有不悅,哪有女子笑得這樣放肆?不過總算松口氣,朝她尷尬的笑了笑,如此甚好,否則這孤男寡女,小生是決然不能同意,想我自幼讀孔孟圣賢之書,習君子德行,萬不能與一女子私會私約,若著人瞧見,小生清白蕩然無存,就是顏氏門楣,也要失了光澤。
白衣女子瞧出他眼底微鄙之意,也冷冷一笑,打量他道:“瞧你穿的衣裳都是上好的緞子,可見是個殷實人家子弟,如今到了深山,怕是要受苦了,這等偏荒之地,可沒有丫環仆役供你差遣,更談不上錦\\衣玉食了。”
顏如玉忙揖手道:“小生不怕受苦,但求明春春闈提名,謀\\求得功名,光宗耀祖,使小生可榮耀鄉里,則心滿意足矣。”
白衣女子微微一怔,古來讀書人都是如此么,十年苦讀不知人事,一生志在金榜題名?滿腔心思盡在書中,焉得不迂腐酸呆,不過這讀書人也實實可敬,春去秋來全不看,花紅柳綠全不想,端的是心靈清純、稟心善良。
白衣女子轉身出了門去,不多時,帶回許多日用之物,皆是上乘質料,做工精細,顏如玉吃驚的看著白衣女子,玉容也變了色,她一個閨女,怎么能將家里的男人衣裳拿來于我?這要是被人發現,豈非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唉呀,她一個二八女子,縱然生在小戶人家,失禮少教,難道竟毫不知羞?竟然這樣膽大,嘖嘖,這樣不知閨儀,實在羞煞,我顏如玉若是收下這些衣物,豈非有與她勾當之嫌?且看我嚴詞推卻,定教她羞愧轉回,方才知曉顏如玉乃清風世家子弟,絕非村野紅妝可以調戲得。
顏如玉微微蹙眉,清眸帶怒,意欲不收,嚴辭相斥,轉念暗忖,身上衣裳早已破爛不堪,周身之物,唯有書卷,豈不要又凍又餓,死于此地?垂首暗暗較量,終于軟下心,慚慚不語,權為接受之意。
顏如玉接過衣物,只覺俊面緋紅,渾身如赤,訕訕的退開些,又問白衣女子如何稱呼,白衣女子冷清清的瞧著他,將他心思盡收眼底,又是氣惱他迂儒,又感慨他心清如鏡,輕輕一嘆,道:“就叫姐姐罷,只有一樣,萬一遇有生人,切莫說出見過我。”
顏如玉對她仍有三分敬畏,不敢再問,依言叫她“姐姐”,諾諾稱是。
白衣女子也不理他,利落的為他收拾好屋子,眼見天色漸晚,朝他福了福,告辭離去,顏如玉又怕又驚,且嫌且嘆,又不敢多言,見她要走,竟松了口氣,躬身相送。
舉目四望,顏如玉惴惴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