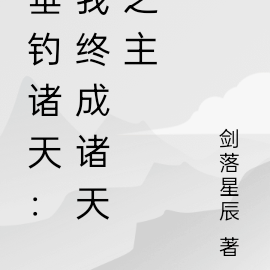酸秀才,破廟棲身,滿腹酸腐受奚落
俏佳人,古墓隱居,一曲舊詞露行蹤
白衣女子蓮步出廟,飄然隱于叢林深木,閃身進了一座古墓,墓內坐著一位鶴發雞皮的老嫗,她見白衣女子回來,一邊迎上,慈愛的捧過她的手暖在掌心,一邊輕聲責道:“小姐,你一時憐憫,只怕為自己引來禍事。”
白衣女子嘻嘻笑道:“婆婆多慮了,阿憂不過是見他一個讀書人,迷路荒野,十分可憐,送他些御寒之物,怎么就會引來禍事?”
田婆婆嘆道:“小姐,你如今大了,這墓穴太小,你近年時常出洞去玩,已嚇著進山砍樵的百姓,如今山下已傳言山上有千年白狐出現,怕要引來貪財之人呢。”握住她纖纖玉手,輕緩的摩挲,十分的疼愛。
莫憂不以為然,噘嘴道:“婆婆,阿憂的輕功是您親自教的,您還信不過么,若是長時間捉不到白狐,傳言自消。”她依坐在田婆婆身側,親昵的將頭歪在田婆婆的肩頭,聲如鶯囀,眸光盈盈,一派嬌嗔女兒模樣。
田婆婆將她愛惜的摟在懷里,道:“你這次又送出衣物,你也知道這墓是前朝定川王愛妾之墓,這些用物都是賠葬之物,珍奇名貴,不是尋常百姓可用,如今出現在破廟,若叫有心之人看見,怎會不追根究底、順藤摸瓜?”
莫憂聽了也知冒失,遲疑道:“婆婆所言極是,確是阿憂之錯,阿憂大意,只想著書生暈倒山道,實在可憐,可是,既已送出,怎好再去索回,再說這天寒地凍,那書生沒有衣物也必凍死,婆婆,如何是好?”
田婆婆嘆道:“既是救人性命,婆婆也不能過于反對,好在大雪封山,樵夫路人一時半會難以進山,如無異常,應該兩個月內積雪難融,只在兩個月內,讓他下山罷。”
無錯書吧莫憂笑著謝過婆婆,又提出時常去看望顏如玉,送水送食,田婆婆見她難得這么開心,點頭應允,惟是叮囑她切莫泄露行跡,莫憂一一依從。
于是,莫憂便每隔一二日就去破廟找顏如玉,開始不過是送些點心食物,顏如玉也是低眉順眼的唯唯諾諾,不敢正眼看她,心里越發的驚疑她的身份,哪家的女子,成日里不坐深閨、不學女紅、隨意出入門庭,家門尊長亦不管教么?這樣來來回回,實在有失體統,難保被人覺察,那時該如何是好?待要正言相告,又嘆,她若不來,廟內無水無食,怎樣生活?一番矛盾,又忍下不語,只是每每都規規矩矩的作躬致謝,不敢半點親近。
過了幾日,顏如玉見她雖然行為毫無閨儀,但是亦不曾言詞上有甚輕浮、褻du,漸漸輕消了對她的輕蔑,當她來時,也說些言話,驚訝的發現莫憂完全不似自己想象中未經教化的山野女子,能詩善詞,言語侃侃、文章娟娟,不由得刮目相看。
漸漸的莫憂來得勤了,除了送東西,也時常為他收拾衣物、整理屋子,每每此時,顏如玉仍是心中不悅,覺得她過于出格,難脫粗鄙,終究是小門低戶的見識,遠不如大家閨秀的雅致與高貴,一邊低貶一邊又感動于其溫柔大方,毫不造作。
莫憂知他懷疑自己的身份,也不說破,平時只作不知,但凡他追問時,就以不便相告回之,顏如玉也不再多提了。
莫憂常年幽居古墓,身邊惟一位田婆婆相伴,亦師亦仆,雖卻慈祥溫和,莫憂終究不敢在她面前玩鬧,往時哪有個人說句話兒,因此覺得顏如玉端的有趣,神態憨癡、心境純明,故而也不計較他諾諾行禮、處處唯謙,反而生出戲弄他的心思,時而彈葉飛雪,擊響門窗,顏如玉不知就里,只見得葉旋如魔、雪飛如妖,驚得惶恐不安,莫憂則掩嘴直笑,待他反應過來,也猜不透原由,越發的訕訕,頰紅如霞。
一日,莫憂閑來無事時,就陪在一旁,看他朗誦經書時的認真模樣,忍不住暗暗發笑,顏如玉已完全不當她是妖怪,不讀書時也與她說話閑聊,但總是恪守禮教,滿口之乎者也、搖頭晃腦,莫憂便道:“顏公子是讀書人,說話不比我們山野女子,有趣得緊,你功課乏了,我給你講個故事如何?”
顏如玉很高興,自從知道她文章錦\\繡之后,就不再輕視她的言談,一則他時而可以聽到莫憂脫口而出的璣珠詞章,二則他長年苦讀蘭窗,過的是身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富貴生活,對莫憂偶爾講述的民間趣事很是驚奇新鮮,側耳傾聽,莫憂便講:
有個姓朱的財主,又講忌諱,又愛說話文縐縐。他對新來的小豬棺說:“記住我家的規矩:我姓朱,不準你叫我時帶‘朱’(豬)字,叫‘老爺’或‘自家老爺’就行了;平時說話要文雅一點,不準說粗言俚語。例如,吃飯要說‘用餐’;睡覺要說‘就寢’;生病要說‘患疾’;病好了要說‘康復’;人死了要說‘逝世’,但犯人被砍頭就不能這樣叫,而要說成‘處決’……”
第二天,一頭豬得了豬瘟。小豬棺急忙來對財主說:“稟老爺,有一個‘自家老爺’‘患疾’了,叫它‘用餐’不‘用餐’,叫它‘就寢’不‘就寢’,恐怕已經很難‘康復’了,不如把它‘處決’了吧!”
財主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小豬倌接著說:“老爺要是不想‘處決’這個‘自家老爺’,讓它自己‘逝世’也好!”
顏如玉聽出莫憂話中奚落之意,俊面通紅,莫憂格格直笑,欣賞他憨態可掬。此后顏如玉果然注意言詞通俗,兩人相處日漸融洽,但顏如玉始終脫不了他的迂腐書生氣,莫憂剛經常通過講笑話的方式取笑他,然后看他垂首翡面而哈哈大笑。
時過一日,莫憂坐在他身邊,托腮靜聽他念書,倦怠起困,長發隨意的搭在肩頭,星眸微合欠精神、嬌腮生暈添嫵媚,顏如玉一看之下竟收不回目光,癡了半晌,又羞又怕的埋首書中,總覺心神不寧,只得放下書,輕聲道:“姐姐要是困了,小生也講個笑話給姐姐聽。”
莫憂聞言立刻來了精神,支起下巴,顏如玉微微搖頸,講道:
“戰國時,趙國都城邯鄲人的走路姿勢很美,燕國壽陵一個少年聽說了,便不遠千里,來到邯鄲學習步法。結果,不但沒學成,反而連自己原來的步法也忘光了,最后只好爬著回去,如此求學,非但沒有學得所長,反而失了自我,姐姐,你道這少年可笑不可笑。”
莫憂一怔,邯鄲學步也能算個笑話?看他一番興致,又不便取笑他,含笑贊了聲“好”,道:如玉講得果然有趣,我也講一個:
庸師慣讀別字。一夜,與徒講論前后《赤壁》兩賦,竟念“賦”字為“賊\\”字。適有偷兒潛伺窗外,師乃朗誦大言曰:“這前面《赤(作拆字)壁賊\\》呀。”賊\\人驚,因思前而既覺,不若往房后穿逾而入。時已夜深,師講完,往后房就寢。既上chuang,復與徒論及后面《赤壁賦》,亦如前讀。偷兒在外嘆息曰:“我前后行藏,悉被此人識破。人家請了這樣先生,看家狗都不消養得了!”
顏如玉聽了也忍不住放下素養儀態,哈哈大笑,笑畢忽問:“姐姐剛才笑話中講到的《赤壁》兩賦是何人所做?”
莫憂側目打趣,道:“虧你是個讀書人,竟連東坡居士也不知道嗎?”
顏如玉面色微紅,竟站起身上,長揖到地,慚道:“小生確是不知,還請姐姐多指教。”
莫憂忽的一怔,半晌做不得答,見顏如玉仍然盯著自己求答,只得答道:“眉州的一名士人,據說在當地小有名氣。”
顏如玉認真的思索片刻,道:“小生聽說眉州有一位頗有聲名的同輩,姓蘇名洵字明允,姐姐說的可是此人?”
莫憂忙擺手笑道:“我也不過是聽說而已,一個笑話罷了,何必認真。”顏如玉還想追問《赤壁》兩賦的內容,見莫憂似乎不愿再繼續說下去,只得咽回。
如此一晃便是月余,深山之中人跡少有,難得清雅,顏如玉每日對窗苦讀,暇時與莫憂吟詩賦詞、閑絮詠對,漸見熟識,不似初時拘束。
一天,莫憂剛剛離開破廟,獨身一人回墓,沿途霧凇如仙、冰掛枝頭,雪壓松柏,西陽從灰色的云層中隱隱約約的露出幾線淡黃色的光彩,投落在冰雪之上,瑩光流動,偶有一只不畏寒的小鳥啾啾叫著在林間跳躍,莫憂想起似十年前又似遙遠的故事,那似乎已經成了一個醒來的夢,被現實隔在了厚厚的云后,遠離地面,不可觸及,可夢里的人夢里的話依然可以隨時浮現在眼前,如煙如幻,她幽幽一嘆,想起一首久遠的曲子,一段久遠的故事,不由得輕吟低唱:
“記得一霎時嬌歌興掃,
半夜里濃雨情拋;
從桃葉渡頭尋,
向燕子磯邊找,
亂云山風高雁杳。
那知道梅開有信,
人去越遙;
憑欄凝眺,
把盈盈秋水,
酸風凍了。
恰便似桃片逐雪濤,
柳絮兒隨風飄;
袖掩春風面,
黃昏出漢朝。
蕭條,
滿被塵無人掃;
寂寥,
花開了獨自瞧。”
吐語如珠,不禁幻想那扇上妖嬈綻放的桃花,相思的人兒,曾傾盡心腸,也等不回遠去的背影,就如同十年前的自己……她默默一嘆,驀然回首,身后仍然是無盡頭的雪與無盡頭的層巒疊嶂,十年前,她就知道,她的過往,那些歡笑與痛苦,永遠的成了虛幻的夢境,舉目望去,只有前方幽深濃密的槿木叢林掩蔽下的古墓才是如今最真實的家。
她飄步如飛,衣襟翩翩,穿行在雪林之中,很快就消失了,孰不知叢林之中隱藏著一位衣衫破爛的樵農,他魂飛魄散的睜著雙眼直瞪著莫憂如仙子一樣且歌且行,冷汗濕透衣裳,全身顫抖,面色灰色,足怔了一刻鐘工夫,才回過神來,嘴里失惶失措的念著“狐貍精……千年白狐……真有妖怪……”丟下肩頭的柴,連滾帶爬的飛奔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