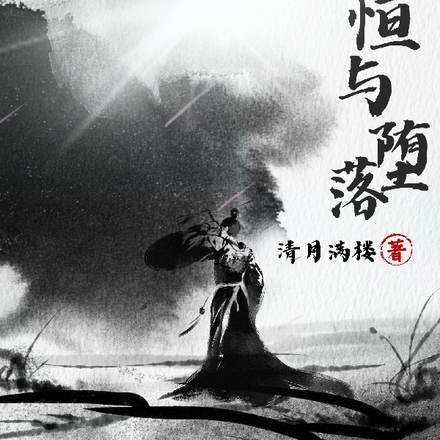石室。
一燈如豆。
映出四墻晶瑩溫潤的白玉石壁,微微泛出柔和清冷的光澤,投落在石臺上。
石臺上躺著一個約摸五六歲模樣的垂髻女童,她頭纏布巾,血色隱滲,雙目緊閉、小臉蒼白,突然在昏迷中“嚶嚀”一聲,眉尖緊蹙、牙關緊咬,小手攢成拳頭,顫抖、搖動,似乎很是痛苦,掙扎著低低的呻吟了幾聲,忽的哭出一聲,慢慢睜開眼睛,一雙皎皎明月似也的眸兒驚異的四下打量,透出漸漸濃烈的驚懼。
一個衣著樸素扎緊、身染斑斑血跡的老婦聞聲緊跑過來,撲在石臺上,見女童醒來,悲喜交加,淚水倏倏,順著蒼老的臉流了下來,低低的哭道:“感謝上蒼,小姐醒了。”說著,匍匐在地上連磕了幾個響頭才爬起來。
女童卻兀自睜著一雙大眼,驚駭的盯著老婦,醞釀了許久,才鼓起勇氣顫聲問道:“你……是……誰?”
老婦一愣,驚慌的將她上下周身打量,忙回道:“老奴是田婆婆啊,小姐是否還覺著暈眩?”
田婆婆?女童猶在惡夢中仍未清醒,她蹙眉想了想,顯然未記得這田婆婆是何人,不過她并未急著追問,用手往后一撐想坐起來,頭部傳來一陣劇痛,她“哎呀”一聲又躺下去,田婆婆忙將她扶好,道:“小姐莫動,小姐后顱受了傷。”
女童似乎并沒有注意到田婆婆說的話,伸出手,去摸老婦,田婆婆未遲疑,忙湊上前給她摸,女童摸了摸她的盤髻,又摸摸衣領,摸摸胸前,又摸摸袖口,一臉驚奇的樣子,好似那初生的幼嬰,萬物都覺新奇,正要說話,突然目光落在自己的手和袖上,那是一只嫩白如玉、粉潤晶瑩的小手,寶藍色的袖口用金線繡著栩栩如生的雉菊,如象它們確實怒放在深秋的陽光下,女童好似被施了定魂針,目瞪口呆,張著嘴僵在那兒。
田婆婆詫異的看著女童,疑心她頭痛難忍,慈愛的握住她冰涼的小手,柔聲勸道:“小姐大難不死,必有后福,夫人,夫人……”話未畢,又流下淚,她小心翼翼抱起女童,垂淚道:“去看看夫人吧,夫人……只怕是,快不行了。”
女童神情癡呆的任由她抱著來到另一個石臺旁邊,這石臺上躺著一個女子,她身上鮮血染紅如雪白衣,如一朵朵怒放的紅牡丹,越發反襯得面色蒼白如紙,只見她雙目緊閉難睜,薄唇緊抿發青,污血斑斑醒目,可是這仍然掩不住她的絕世容貌,眉似柳葉雙分,英姿逼人,肌膚細膩如脂,溫潤如玉。
田婆婆跪在石臺前,輕輕呼喚:“夫人,您睜開眼睛看看吧,小姐醒了,小姐想您呢,您就睜睜眼吧。”女子睡得很沉,魂游三界之外,不在塵世之中,老婦無奈,泣對女童道:“小姐,您也叫娘,興許夫人聽了就醒了。”女童驚愕的看著老婦,不過她還是柔順的叫了聲“娘!”
或許真是母女連心,石臺上那女子聽了女兒的呼喚,眼皮顫了顫,真的慢慢的睜了眼,那目光雖然倦倦無神,卻清澈似秋水湛湛、十分美麗動人,她美目流轉,緩緩移目過來,田婆婆喜得一把將女童摟在懷里,把頭埋在女童的肩上隱隱的大哭起來。
女子目視田婆婆,微微一嘆,輕聲道:“田婆婆,莫柔連累您了。”
田婆婆忙道:“夫人折煞老奴了,只要夫人和小姐平安,老奴愿意死一百次。”
女子微微一笑,美目中流出戚凄悲痛之色,道:“田婆婆,莫柔有件事,要托付田婆婆,求田婆婆答應。”
田婆婆俯在石臺前,連聲應道:“夫人有話只管咐付,萬莫說求。”
女子向女童眨眨眼,艱難的動動手臂,想拉女童的手,可惜仍是動彈不得,無奈的作罷,女童卻主動伸出小手握住女子的手,女子眼中露出歡喜的神色,癡看她半晌,才向田婆婆道:“田婆婆,莫柔將阿憂交給您,請您將她扶養成人,莫柔來生結草銜環,報答您的恩情。”
田婆婆哀哀哭道:“夫人何必說這話,夫人雖然身受重傷,卻也并非無可醫治,只要好好養著便是,這地方荒僻無人,他們是找不到的,待老奴為你調息度氣,一定會很快康復的,小姐年幼,你怎么忍心舍她而去,讓她剛遭追殺之劫又失至親之人。”
無錯書吧女子痛苦的閉眼,雙行清淚滑落腮旁,冰冷的手心里緊攢著女童的小手,恨不得將它揉化進自己的身體,緩又睜眼,戚然苦笑道:“我哪里舍得,不過是知道傷及心肺,難以活命,有些話還是交待了吧。”她似是氣力不支,頓了頓,接著說道,“丁府里帶出來的帛卷,還有我早寫好的遺書,都在我胸口放著,您收好了。”田婆婆捂著臉磕頭。
女子目光漸漸迷離,恍若魂魄即去,她吃力的看了眼女童,又轉向田婆婆,悠悠一嘆,道:“田婆婆,勿忘你我當年之約。”
田婆婆悲聲哽咽:“夫人只管放心,老奴絕不敢忘,就是小姐,夫人也可放心。”
女子癡癡看著女童,美麗的眼中流出淚水,她戚然道:“我的孩子,莫憂,莫憂……”狠狠的握住那只小手,雙目一合,氣息悠悠漸覺無、香魂離體游太虛。
田婆婆仆在地上哀哀痛哭,因為強壓著聲音,使得身體陣陣抽搐,女童茫然的看著這一切,忽覺心痛似絞,五臟六腑都要裂開似的,女童劇痛難忍,呻吟一聲,一跤跌坐,軟在地上,緊接著嗓子一熱,腥血之味涌上,“哇”一聲,吐出一口血來,盡噴在亡母的手上。
田婆婆驚得魂飛魄散,面色慘無血色,她手忙腳亂的將女童摟在懷里,哀聲泣道:“小姐!小姐!切莫過于悲傷,傷了身子。”再看女童時,淚落如雨,全身顫抖,原本稚嫩清純的雙目中,此刻射出兩道如狼虎般狠毒的光來,仇恨、痛苦、憤怒、冤屈……驚出田婆婆一身冷汗。
田婆婆心跳如鼓,仔細眨了眨眼,再細看時,女童雙目含悲,清稚如常,全無剛才駭人神彩,田婆婆只當自己年老眼花,雖然隱約惴惴不安,不過揪心于小姐吐血,深怕有負夫人臨終之托,也不將適才一幕耿耿了。
女童則恍若無知,只是茫然的看著剛剛死去的母親,突然也掙開田婆婆,將亡母腰間墜著一只白玉環摘下,緊攢在手心,然后跪下來,磕頭拜道:“娘,您安息吧。”
田婆婆欣慰的看著女童,拜了幾拜,這才站起身來,小心的拭去女童嘴角的血跡,從女子胸前果然摸出薄薄的一疊的帛絹,小心的放進自己胸前,也不說話,徑直往里走去。女童這才打量起四周,這似乎是個山洞,但是十分氣派,墻與地面都是大理石打造,幾座石臺光滑寬敞,田婆婆往洞深處走去,明明一眼看過去是墻,田婆婆卻轉進去不見了,女童好奇的跟過去看,原來那不過是個拐角,里面別有洞天,正琢磨著這是什么地方,似乎有些眼熟,聽到里面一陣低沉的、震人心悸的磨擦聲,女童探頭去看,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原來田婆婆抗著一具尸體走了出來。
田婆婆道:“小姐別害怕,這幾天只怕外面有人,過幾天老奴再將她丟了去。”說著將尸體往一個角落里一塞,不一會兒又回來,來到石臺前向女子道:“夫人,老奴無能,不能給您換件干凈衣裳,就這樣為您入棺吧。”說著抱起女子又往里面走。
女童哆嗦著爬起來,跟在后面,見洞室中央放著一口漢白玉石棺,棺蓋側翻,想來是剛才被田婆婆推在一旁的,看不出這矮小瘦弱的老婦會有這么大的力氣,竟能推動這么大的一片石板,正驚嘆著,田婆婆已念念有詞的將女子放入石棺。
田婆婆向女童招手道:“小姐,來向夫人磕個頭吧。”女童默默走過去,拜倒磕頭,田婆婆向著棺內道:“夫人放心,老奴一定不負夫人重托,將盡心盡力扶養小姐。”也磕了幾個頭,走到棺蓋邊,雙手抓住石板邊緣,往上一抬,就將石板提起,輕輕蓋在石棺上,吻合無縫。
女童驚訝的看著她利落的完成這套動作,怯怯的問:“田婆婆,這是個……墓穴吧?”田婆婆愧疚的回道:“是的,小姐,為了躲避丁府的追殺,老奴只能讓小姐住在這個地方了。”女童的臉頓時變得煞白,住在墓穴中,太可怕了。
田婆婆見她害怕,小心的抱著她,寬慰道:“小姐莫怕,有老奴在,小姐只管放心。”女童仍是驚恐不已,顫聲問:“田婆婆,我……叫什么名字?”田婆婆駭然看著她,半晌摸摸她的額頭,又翻了翻她的眼皮,試問:“小姐可是受傷太重,頭痛得很?”女童一怔,點點頭。田婆婆愛憐的撫著她,道:“小姐,你叫莫憂。”
莫憂心中一動,問:“婆婆救起我時,可有見著旁邊有人?”婆婆說:“夫人,還是老奴便是。”莫憂追問:“再沒有別人了嗎?”婆婆驚異的看著她,據實答道:“還有個小叫花,被誤推下山而死。”
莫憂心絞得疼,硬聲問:“那小叫花,確是死了?”婆婆點頭道:“我探過鼻息,確是死了,唉,無辜的生靈,老奴原是想埋了他的,顧念你和你娘,擔心后有追兵,也就沒顧上管了。”莫憂的頭象是團棉絮綿綿的,半天才回個神來,突然輕笑起來,眼水恣意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