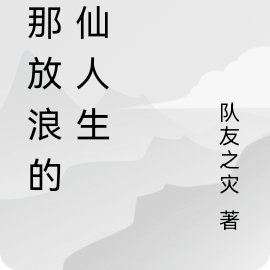第173章 城里来的?还开着大汽车?
傻柱紧跟着钻了出来,还没站稳,腿肚子就先转了个筋。
他那一双眼睛急吼吼地往院门口瞅,心里咯噔一下。
院门紧闭,上面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黑铁锁。
原本那股子要见媳妇的兴奋劲儿,瞬间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透心凉。
傻柱一张脸煞白,手足无措地搓着裤缝,声音都在打颤。
“哥……这……这是没人?不能是反悔了躲出去了吧?是不是嫌咱们来得太早?”
这患得患失的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在四合院横着走的混不吝劲头。
何大清提着网兜下了车,瞧着那锁头也是一皱眉,不过到底是老江湖,瞥了一眼周围那光秃秃的烟囱。
“瞎琢磨什么!庄户人家哪有大白天在家闲坐着的?这个点儿,肯定都在地里刨食呢。”
何雨生没搭理傻柱那点没出息的慌乱,眼神往周围那一圈看热闹的人群里一扫,目光落在一个虎头虎脑、吸溜着清鼻涕的半大小子身上。
这小子眼珠子骨碌碌转,胆子最大,离车头最近。
何雨生手腕一翻,掌心里多了一把大白兔奶糖,那蓝白相间的糖纸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嘿,小子,过来。”
那半大小子被这声招呼弄得一愣,脚下像是生了根,想跑又舍不得那看起来就甜掉牙的好东西。
“拿着,叔请你吃糖。”
何雨生嘴角噙着笑,把糖往那孩子手里一塞,顺手揉了揉那乱糟糟的头发。
“这可是大白兔!城里都买不着的好东西!”
周围的孩子们一下围了上来,馋得直咽唾沫,那眼神恨不得把糖纸都给吞了。
那半大小子名叫石头,也是个机灵鬼,一把攥紧了糖,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小伙伴,生怕被抢了去。
“叔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家王大伯和翠花姐呢?咋锁着门?”
石头剥开一颗糖塞进嘴里,浓郁的奶香瞬间在他口腔里炸开,甜得他眼睛都眯成了缝,说话含含糊糊却格外响亮。
“翠花姐跟大伯在东头玉米地起茬子呢!一大早就去了!”
原来是在地里。
傻柱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这才算落回了肚子里,长出了一口大气,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吓出来的冷汗。
何雨生点点头,又抓了一把糖塞给石头。
“得,再给你个任务。跑一趟东头玉米地,告诉王大伯和翠花姐,就说四九城老何家来人了,开着大汽车在门口候着呢。”
“好嘞!叔您擎好吧!”
石头哪里见过这等阔绰的手笔,把糖往兜里一揣,跟脚底抹了油似的,撒丫子就往村东头狂奔而去。
其他的孩子们见状,也嘻嘻哈哈地跟在屁股后头跑,那阵势比过年抢炮仗还热闹。
剩下的就是等。
何雨生靠在吉普车头上,点了一根烟,优哉游哉地吐着烟圈,神情淡定得像是在自家后院晒太阳。
可傻柱却是如坐针毡。
他一会儿扯扯衣角,一会儿摸摸那打了发蜡的头发,还在车窗玻璃上照了照,生怕刚才那一吓把自己给吓得走了样。
他在原地来回踱步,脚下的黄土都被磨平了一层。
“哥,你看我这领扣歪没歪?我这鞋是不是踩灰了?”
雨水坐在车里,看着二哥那抓耳挠腮的样,忍不住扑哧笑出声。
“二哥,您就别转悠了,转得我头都晕。您这模样倍儿精神,翠花姐要是看见了,准保一眼相中。”
何大清也看不下去了,把手里的网兜往地上一放,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傻柱一眼。
“有点出息行不行?你是来相亲当爷们的,不是来上刑场的!把腰杆给我挺直了!老何家的脸都让你这就差尿裤子的德行给丢尽了!”
傻柱被亲爹这一顿损,老脸一红,强撑着把背挺了挺,可那眼神还是止不住地往村东头飘。
何雨生弹了弹烟灰,看着弟弟这副模样,心里倒是透亮。
这年头,相亲就是一锤子买卖。
成了,那就是老婆孩子热坑头;不成,这辈子能不能再遇上合适的都两说。
無錯書吧傻柱这是把下半辈子的幸福都押在这一哆嗦上了,能不慌吗?
“沉住气。这吉普车往这一停,这排场摆开了,你就已经是这十里八乡最靓的仔。剩下的,就把你那手艺和真心掏出来给人看。”
何雨生的话音刚落,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稚嫩却穿透力极强的喊声。
那是石头。
这小子跑得气喘吁吁,还没到地头,声音就已经顺着风传到了玉米地里。
“翠花姐——!翠花姐——!”
正在地里挥着锄头刨玉米根的王翠花直起腰,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疑惑地看着远处狂奔而来的小黑点。
石头一边跑一边挥手,嗓门大得恨不得要把这冬日里的寒气都给震碎。
“别干啦!家里来且啦!开着小汽车的大官儿!在门口等着跟你相看哪!”
那一嗓子喊出来,风都像是停了半拍。
其实那绿皮吉普刚进村的时候,王翠花在地头直起腰瞥见过一眼。
也就是一眼。
她当是公社来了哪位大领导视察,或者是部队拉练路过,心头虽说晃过一丝没来由的羡慕,可转瞬就把那点不切实际的念头给掐灭了,低头接着挥舞锄头。
咱就是土里刨食的命,那四个轱辘的铁疙瘩,跟咱隔着九重天呢。
可谁承想,这惊雷偏偏就劈在了自己脑门上。
石头这孩子嗓门随他爹,亮堂得跟村口的破锣似的,这一嗓子“相看”,把方圆二里地的耳朵都给震醒了。
周围那几十号社员,手里的活计全停了,一个个脖子抻得老长,眼珠子瞪得都要掉进土坷垃里。
紧接着,这片玉米地就炸了窝。
“啥?城里来的?还开着大汽车?”
“我的乖乖,老王家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啊!那吉普车我也瞧见了,威风得紧!”
“不是说翠花那是大龄难嫁吗?咱村二癞子前儿个还笑话人家嫁不出去,这一转眼,凤凰落咱穷山沟了?”
议论声往外冒酸气,也冒着藏不住的艳羡。
王翠花握着锄头的手猛地一紧,指节都泛了白。
她心口那只撞得慌的小鹿,这会儿简直要撞破肋骨跳出来。
原本压在心底那点不敢奢望的火苗子,被这一把油浇得轰然而起,烧得她脸颊滚烫。
真的是来找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