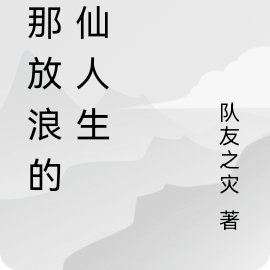第172章 这门亲事,太高了
何雨生上下打量了一番,满意点头。
“行啊柱子,这一收拾,人模狗样的,倒真像个干部。”
“哥,您这叫什么话,合着我平时就不像人?”
傻柱有些局促地扯了扯衣角,脸上虽然还要强撑着不在乎,可那嘴角都要咧到耳根子去了,眼底的期待跟火苗子似的乱窜。
何大清站在水槽边,手里的抹布忘了放下,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青年。
無錯書吧这还是那个只会跟在他屁股后头要糖吃的傻小子吗?
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却又比自己更体面,更硬气。
一股子酸涩猛地冲上鼻腔,那是愧疚,是自豪,更是这些年缺席的遗憾,五味杂陈,搅得他心里头发苦。
孩子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可这成长的代价,却是没了爹娘的庇护,在风雨里硬生生熬出来的。
何大清背过身,假装去涮抹布,偷偷用袖口抹了把眼角。
“是不错,这身板随我,是个爷们样。”
何雨生抬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一肃。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今儿这仗只许胜不许败,咱们老何家能不能在四九城把头抬起来,就看这一哆嗦。”
他站起身,一股子行伍之人的肃杀气场瞬间铺开。
“分东西!”
一声令下,堂屋里立刻忙活起来。
雨水乖巧地拎起两盒包装精美的桃酥,笑得见牙不见眼。
傻柱深吸一口气,一把抄起那几瓶沉甸甸的老汾酒,还有那两条大前门香烟。
何大清最是卖力,抢着要把那最重的米面袋子往肩上扛,却被何雨生拦了下来,指了指地上那一大网兜的杂七杂八——糖果、茶叶、还有那几块精心挑选的花布。
“你拿这个,别弄脏了衣裳,那是给人家姑娘看的。”
“哎!哎!得嘞!”
何大清点头哈腰,提着网兜,腰杆却挺得比刚才直了不少。
一家四口,提着大包小包,浩浩荡荡地跨出了中院的月亮门。
此时正值大院里上班上学的高峰期。
前院的三大爷阎埠贵正推着自行车要出门,一眼瞅见这阵仗,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嚯!这一家子!
“哟!雨生,柱子!这一大早的是去……”
阎埠贵扶了扶眼镜,脸上的精明瞬间化作满得溢出来的热情。
“三大爷,今儿带柱子去涿州相看个姑娘。”
何雨生笑着应了一句,脚下不停。
“哎哟喂!这是大喜事啊!我就说今儿怎么喜鹊喳喳叫呢!柱子这身板,这气派,肯定马到成功!”
“借您吉言了三大爷!”
傻柱虽然平时看不惯阎埠贵那抠门样,可今儿这话听着顺耳,心里头那股子紧张劲儿散了不少,憨笑着回了一句。
一路上,碰见早起倒尿盆的二大妈,提着鸟笼子的二大爷,一个个见着这场面,谁也不敢再拿那冷眼瞧人,纷纷堆起笑脸说着吉祥话。
不管真心假意,至少在这四合院的一亩三分地上,何家如今的气势,那是独一份的。
直到坐进吉普车里,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傻柱那颗狂跳的心才稍微平复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和温暖。
这就叫一家人吗?
……
与此同时,数百里外的河北涿州,王家村。
日头刚爬上树梢,王翠花就在那面裂了一道纹的水银镜子前照了第八回。
她不是那种小家碧玉的模样,常年的劳作赋予了她健康的小麦色皮肤,眉眼间透着股子英气,身板结实,虽然不如城里姑娘娇嫩,却像是一株在野地里肆意生长的向日葵,透着勃勃生机。
自从那个开着卡车、穿着军大衣的大哥来过之后,她的心就没静下来过。
二十岁,在这个年代的农村,已经是被人戳脊梁骨的老姑娘了。
没人提亲不是因为她丑,是因为她太强,太烈,一般的汉子镇不住,也不敢娶。
可她王翠花心里也有个梦,想找个能顶天立地,知冷知热的男人。
“花儿,差不多行了。”
老王头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烟雾缭绕中,那张满是沟壑的老脸上满是愁云。
他看着女儿那精心编好的麻花辫,还有特意换上的那件虽然旧却洗得发白的碎花袄,心里既欣慰又酸楚。
“爹也不想泼你冷水。人家那是城里的人,又是开车的大干部,家里条件肯定差不了。咱这就是个土窝窝,你期望别太高,万一……万一要是看不上咱,你也别往心里去。”
老王头磕了磕烟袋锅子,叹了口气。
这门亲事,太高了,高得让他心里发慌。
王翠花转过身,抿了抿有些干裂的嘴唇,眼神却异常明亮。
“爹,我想试试。”
“那大哥看着是个正派人,他说他弟弟是个厨子,手艺好,人也实在。我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安稳过日子。”
她顿了顿,目光有些飘忽,看向窗外那光秃秃的树杈。
其实她心里也没底。
除了知道对方住在皇城根下,有个厉害的大哥,是当厨子的,其他的,高矮胖瘦,脾气秉性,她一概不知。
这就跟要把自己下半辈子押宝一样,全凭运气。
吉普车的引擎轰鸣声像是一声惊雷,硬生生把这沉寂的涿州王家村给炸开了锅。
四个轱辘卷起的黄土漫天飞扬,惊得村口的几只老母鸡扑腾着翅膀上了房顶,大黄狗夹着尾巴狂吠,却只敢缩在墙根底下,哆哆嗦嗦地瞅着这只从未见过的绿色钢铁巨兽。
何雨生稳稳地把这一脚刹车踩死,吉普车带着一股子彪悍劲儿,刚好停在一家挂着斑驳木门的院落前。
这就是王翠花家。
车还没停稳,屁股后头已经跟了一大串半大的孩子,一个个脸上挂着鼻涕泡,眼里闪着好奇又畏惧的光,想上前摸摸那锃亮的铁皮,又怕被这铁家伙咬上一口。
大人们也都端着饭碗跑出来看稀奇,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声跟苍蝇似的嗡嗡响。
“得嘞,到了。”
何雨生拔下车钥匙,推门下车,那一身将校呢大衣在冷风中猎猎作响,往那一站,跟画报里走出来的人物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