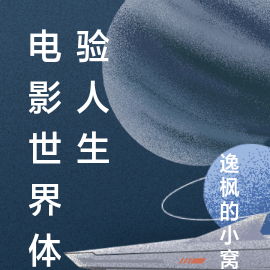汪荣一伙急匆匆跑出砖厂,见公共汽车就招手,他们担心方飞派人追赶阻击,自已人生地不熟,被打个半死,实在划不着。所以只要有长途车,不管它去哪里,先上车逃出南京城再说。路过的都是短途的,长途的很少见。汪荣脑筋急转弯,想这条路总是跑短途,不如换另一条试试。
真的如愿以偿,刚来到一条沥青马路,一辆啵啵车就吼着开过来了。汪荣手一挥,车“嘎”的一声停在了路边,八人用最快的速度登上车,然后找个位置坐下。
“刚上车的旅客同志,请买票!”售票员有礼貌地喊。
汪荣走过去,问这车在哪里停,多少车费?
售票员微笑着道;“终点站是扬州,车票十六元一个。”
“出南京城吗?”
“当然了!南京距离扬州几百公里,你说出不出?”售票员很诧异,这几个年轻人乘车怎么这般漫无目的,上车才问去处?本想问一问,但又想,只要给钱,巴不得越远越好,管他们去哪里。收过汪荣八人的钱,撕了八张票递给了汪荣。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乘客们在摇摇晃晃中打起了瞌睡,但唯独冯云没有。八人中,只有冯云结了婚,而且生了一个女孩,快两岁了。离开家乡半年了,母女二人是否安好?是否有钱用?冯云望着窗外不断闪过的景色,心中越发焦虑。他想起上次给家里写信还是两个月前,也不知道老婆收到没有。
他默默盘算着,如果到了扬州,一定要找份工作稳定下来,尽快往家里寄些钱。车子颠簸一下,旁边的汪荣也醒过来。看冯云愁容满面,碰了碰他问道:“老冯,想啥呢?这么出神?”冯云叹了口气,把自已对妻女的担忧说了出来。汪荣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老冯啊,等咱们安定下来,肯定能找到新的事儿做,并且能够挣大钱。”冯云点了点头。此时车子突然颠簸了一下,冯云的心也跟着颤了颤,他仿佛看到女儿可爱的小脸和妻子期盼的目光,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前面有多难,一定要多赚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车子经过小站,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汪荣的同坐刚刚下去,另一个人便接替了他。这人四十左右,善于言谈,扭过头去,笑着问汪荣:
“小伙子,你在哪里下车啊?”
“扬州。”
“去扬州干啥呢?”
“打工。”
中年人很吃惊,心想,现在的打工人都往南部沿海走,怎么往扬州去呢?不免感叹一声,劝汪荣:
“不知你们那里是否有关系,这扬州历史上是很出名,但现在的经济发展却是落后,去打工若没有关系,恐怕难找到工作的。”
汪荣不愿将南京砖厂的事说出来,更不会说是在逃难。听了中年人的话,心里不禁凉透了,难道命运就这么舛?哎!管他,到达后再说,我就不信船到桥头没有路。
只听中年人又道:“在扬州,即使有关系有事做,你又不是什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很少的。你若相信我,我给你们指条路。”
汪荣一听,像生死绝望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喜得笑眯眯地向中年人道:
“不瞒叔叔说,我们出门就是无头苍蝇,四处乱窜,老叔若肯帮我,就请快阐明吧!”连忙递一支香烟过去。中年人不抽烟,拒绝了,但他还是说了出来:
“你们在扬州下车后,换车去一个叫七圩的码头、大运河边坐着等,看见一艘艘水泥船来往行驶,船上的老板会上岸物色年轻力壮的打工人给他们做事,如果看上了,他就会领你上船。船上干活,工资是工厂打工人的几倍。”
“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做什么工作呢?”汪荣听了,喜出望外,要打破吃砂锅问到底了。
“我们萍水相逢,没必要哄你。上船去翻沙。”
“什么叫翻沙?”
“我的乖乖,怎么连翻沙都不知道?就是用抽沙机从江底把沙子抽上来,然后滤掉水,沙子就落在了船舱里,满了,有其他船老板来购买,你就把沙铲给他。就是这样。一般情况下,老板都是当天发工资的。”
“谢谢!谢谢!大叔告知。”
啵啵车到了下一个站,中年人起身下车。隔着窗子,汪荣向他挥手告别,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七人睡眼惺忪醒来,汪荣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忙把中年人的话轻声说给了他们。
有了着落,用不着四处漂泊,谁不高兴呢?
终于,扬州站到了,八人下了车,又急忙去售票窗口买了去七圩的票,然后登上了车。
七圩是建在大运河上的一个渡人码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水泥壳船开着马达往来穿梭,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行驶的船,船边都会印着来自不同的县名,有扬州的,武进的,淮阴的,镇江的,林林总总,杂七杂八,令人眼花缭乱。
其中,运沙船占多半。拖沙的老板心狠厚,不把沙子装的船帮和水平面一样高,决不罢休。所以,有些水泥船不堪负重,像老水牛一样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江面上吃力的走着。这又是另一番撩眼的景象。
经过两小时的跋涉,公共汽车终于到达七圩。七圩码头上摆了许多面食摊,老板煮好面,加几匹菜叶,一点油酱醋,就叫菜面价格也比什么都没有放的素面要贵一毛钱。汪荣八人自逃出南京,几番奔波,肚子早已饿的咕咕叫。找个桌位坐下,每人要了两碗,喜得那老板娘做起面来动作更加熟练。一会儿,面端在了八人面前。
“有辣椒吗?”冯云问。
“有有有,怕把你们辣着,所以没有放。”老板娘端上一瓶辣椒,放在餐桌上。这八人“呼啦”一声,争先恐后用筷子往里蘸,然后放入面条里一搅,便狼吞虎咽起来。
老板娘望着这伙吃辣椒的人,心想不是湖北的便是那湖南的,这两个省的人都喜欢吃辣的。老板娘好奇地问:
“你们是湖南还是湖北的?”
“都不是,我们是贵州人。”罗七答。
“没有听说过贵州,只知道有个贵阳,哎呦,贵阳省离这远着呢!你们大老远的,来这干什么?”
“打工啊!听说这里船老板招翻沙的人,所以我们就来试试。”汪荣回道。
老板娘眼睛一亮,知道生意来了,对着汪荣说:“是有这回事,但不是每个人来找活干都顺心。有时候要等个把月,有时候只是一两天。你们是不是打算一定要找到工作?”
“那当然了。”冯忠插嘴道。
“只要你们光顾我的生意,我可以帮你们的一点忙。你们一时找不到工作,晚上住旅社?不是我鄙夷你们,打工人未找到工作之前是舍不得花钱的。往西边去一里处的帮砍上有一个窝棚,比较宽敞,睡十来个人没有问题。那是我地政府专门往流浪人员建的。里面有干燥的稻草,可以将就着度夜。”
汪荣八人感激不尽,表示在没有人聘请之前,一定要来老板娘这里吃面,但前提是要有辣椒面。老板娘笑呵呵地点头,连说:“有,一定有!”
离开面食摊,来到了大运河岸。正月的河风带着泥腥味扑鼻而来,刺骨寒凉,直逼脸颊。站了半天,行驶的水泥船并没有靠边,也没有任何人上岸招工。眼看天就要黑了,汪荣叫冯忠去面食摊找老板娘打八份面条的包,然后带领六人去寻找老板娘所说的棚子。
果然,靠河帮上有一间油毛毡覆盖的棚子,周围摆放了许多杂乱的稻草。棚子里也堆放着被人睡平了的稻草,已然变成了睡垫子。待冯忠拿来面条,大家吃过后,点然香烟喷云吐雾一番,四人左,四人右,交叉相拥取暖。不知不觉中,很快进入了梦乡。
突然,外边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把瞌睡较轻的石汝法惊醒了,接着又听见有人说话。
“大哥,我们的棚子好像有人给睡了,今晚在哪里休息?”
“对啊!去哪里睡?”
“把里面的私儿赶出来,我们去睡。”
七嘴八舌的喧闹,把汪荣八人吵醒了,都没有发话,只听着外面的动静。
“里面的人好像比我们多,我们恐怕打不过。”外面有人说。
“这里不是有草吗?点燃,把里面的杂种熏出来。”果然是说到做到,稻草被点燃了,火光中,一个熟悉的脸孔显现出来。石汝法一看,怒不可遏,一个鲤鱼打挺站起,大喝一声,一马当先,奔出去,飞起一脚就把点火的踢了一个狗啃屎。
原来,点火人就是砖厂屙屎屙尿在汪荣工棚里的何明,他几个被开除后,四处流浪,不知不觉中在七圩相遇。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汪荣看见石汝法冲了出去,怕他吃亏,喊一声:“打,打,打!”
七人连同石汝法,朝着对方就拳打脚踢,打的何明一伙哭爹喊娘,往坎子下逃走了。汪荣让大家把火扑灭,然后又去补觉。但此时大家怎能睡得着呢?
天明后,八人吃了东西,然后走到河岸边继续等着有缘老板的到来。约午时,一艘空水泥船靠岸,走下来一个三十多岁,农家媳妇打扮的妇女。她一看见站在岸边的七八个年轻小伙,就知道是找工打的人。她问:
“你们是打工的吗?会翻沙不会?”
汪荣怕他人说漏了嘴,连忙应道:“会,会,会!”
“好吧,我看你们都很结实,选两个跟我上船。要快!”
汪荣望了七人,然后把冯云冯忠推给船老板,道:“老板,您看这两位如何?”
“可以,上船!”
半年多的日夜相处,大家彼此都分不开了,但为了不失时机,只得忍痛暂时离别,此时的心情,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痛”。冯氏弟兄站在船艄,挥手致意。汪荣大声呼叫:“老贤,保重身体!”
之后,又等了两日,胡秦胡贵一组,罗七马札一组,汪荣石汝法一组纷纷上了翻沙船,驶出大运河,直往长江深处,又开始了打工翻沙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