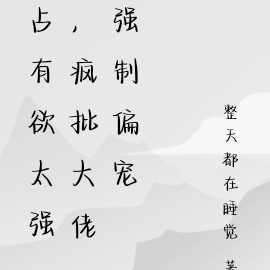第25章 一场梦
连着几日的阴雨绵绵,在半夜时分迎来了狂烈的暴风雨,外面风吹雨打电闪雷鸣,小小的帐篷哪禁得住这般威力的风势,歪来歪去随时要散架似的。
帐篷内也没好到哪里去,地面布满雨水,没一处能下脚的地。
林厌奚也遭遇了暴风雨,她的脸色在雨滴击打篷顶的声音中变得越来越差,犹如置身严寒冰窖中,身体冷得直发抖。
程予檐脱了鞋子外衣上床,掀开被子小角钻进去。林厌奚感受到热源,本能地靠了上来,紧紧贴着他。
怀中的人身形娇小,细腰盈盈一握,脸蛋皱成一团,难受得小声哼哼。程予檐看在眼中,却无能为力。
他将林厌奚脸颊的湿发挽到耳后,不过一天时间,下巴尖了许多。这样子折腾几天,得瘦成什么样,他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喂回来。
林厌奚根本没睡着,但也不算醒着,意识不清,头痛欲裂,像被人用锤子敲了几大锤似的,肉烂了骨头还没断。
她收回之前的狂妄之话,为自己轻看瘟疫这玩意感到万分抱歉。再来一次,她定对其毕恭毕敬,唯唯诺诺也行。
林厌奚一晚上在冰山与火海的状态中变换,白日清醒了片刻,喝完药又陷入昏迷。脖子开始长红疹子,紧接着脸上和身上也长了,疼痒难耐,她总下意识地去抓挠。
程予檐按住她的手,防止她把自己抓得血肉模糊,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林厌奚的症状看着比其他人要严重得多,应该是她体质弱,加上与过多病人接触的原因。虽然程予檐这些日子好吃好喝地供着林厌奚,但身体先前的亏损落下了根,没个半载很难养回来。
林厌识派人叫程予檐过去,程予檐让听雪帮忙守一会,便刻不容缓地去了林厌识的帐篷。
几位大夫不眠不休,总算找出了治疗瘟疫的药方。
程予檐道:“那还等什么,赶紧给他们煎药治病啊。”
無錯書吧大夫露出为难的表情:“问题就出在这,我们没法煎药。”
“什么意思?”程予檐不明白。
林厌识道出问题所在:“药方是有了,少了一味药材,我派人去买,偌大一个绥云城,竟然没有一株苻樱草。”
早在半月前便有人将城内的苻樱草一购而空。这样看来,这场瘟疫是人为的,又岂会让他们轻易找到解决的方法。
程予檐意识到问题不简单,蹙了蹙眉,随即想到,“越城呢?”
越城是距离绥云城最近的一座城,不过几个时辰的脚程,骑马不过一个时辰。
林厌识摇头:“问过了,也没有。”
对方早预料到今日局势,想必其他离得近的几城也不会有符樱草了。回屿阳城的路程又过于遥远,他确定屿阳城有苻樱草,但他不敢耽搁。
“药房没有,不代表山上没有。”程予檐道。
大夫道:“苻樱草喜阴耐寒,多长于深林沼泽,环境恶劣,极难采摘,因而时常一株难求。”
“我知道一处,可能会长有苻樱草,眼下这般情况,需要你帮我主持大局。最多明日,我一定能把苻樱草带回来。”林厌识道,他叫程予檐来便是为了告知此事。
此行凶多吉少,他要面对不止是恶劣的环境,还有半道的埋伏,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绥云城交给程予檐他才放心。
程予檐不认可他的提议:“不行,你是绥云城主,你不能去,我去。这帐篷外的许多人,都是因为相信你才支撑到现在。”
“正是因为他们相信我,我才应该去。”林厌识语气急道,他受够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是绥云城的事,我是绥云城的城主。”
程予檐想起病榻上的林厌奚,不容置喙道:“她不能再失去你了。”
如果林厌奚清醒了,知道她的哥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到时要如何面对她。
林厌识愣了下,如今的林厌奚,谁都不能再失去了。他却仍旧没有打消去寻找苻樱草的念头。
程予檐不管他什么想法,抄起桌上的纸笔,让大夫在上面画出苻樱草的样子。将纸张折叠好放进胸口,对林厌识道:“不瞒兄长,我带了一队人马在城外,都是训练有序的暗卫,如今正好派上用场。我会尽快将苻樱草带回来,林奚就拜托你了。”
不等林厌识作答,他一意孤行地走出帐外,对栅栏外的临风招了招手,“临风,找两匹马来。”
没有与林厌奚道别,一路快马加鞭出了城门,为了林厌奚,他会安然回来的。
“小姐,有姑爷和城主在,你一定会没事的。”听雪守在床边,握住林厌奚的手,默默祈祷着。
小姐一生积德行善,所遇非良人吃尽了所有的苦头,因为失忆才过了段开心的日子。老天有眼,保佑小姐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林厌奚以为自己死了,这种感觉跟死了也差不多,她全身都难受,跟被重物碾压过一般,四肢无力。
她做了好长的一场梦,梦见奈何桥头,两侧长满了鲜红如血的彼岸花,桥的那头站着两个人,浓雾昏暗,她看不清他们的长相,只当是索命的黑白无常,转身拼命地跑。
前方有一道白墙,她顾不上其他,一头撞了上去,眼前所见变了模样。她看见程予檐弯着腰刨土种花的身影,她坐在树下,听雪用一片荷叶给她遮阳,临风挑着两桶水稳稳当当地走了进来。
程予檐指着一小块空地,询问她想种什么花。
梦里的她好像很矜持,不怎么爱说话。
程予檐也不失落,他只是问问,本就不期待她能回复什么。
芍药,月季,鸢尾……好像还种了几排小葱,程予檐说等葱长出来了包小葱猪肉饺子给她吃。
树上蝉鸣不息,池里莲花开得正好,夜里白天蛙鸣四起。程予檐花了大价钱从北方运来许多冰块,贮藏在冰窖里,随时拿出来给林厌奚消热。
程予檐在院里忙得满头大汗,休息时跑到她面前,手背在身后,弯下腰,露出一口大白牙:“帮我擦擦汗。”
炙热的气息打在她的脸上,她懒洋洋地抬起眼帘,偏过头,态度再明显不过。
“娘子,我的好娘子。”
她眼神一变,知道某人又要开始了。
某人扯着她的袖子,撒娇道:“你帮我擦擦汗嘛,好不好,我的好娘子。”
旁观的听雪嘴角含着浅浅笑意,俨然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
“你,别这样。”她无论多少次也无法习惯程予檐这个样子,尤其是有外人在的情况下,她不情不愿地用手绢擦掉他额上的汗。面前的人笑得牙不见眼,她不禁也跟着笑了。
“谢谢娘子。”程予檐迅速在她脸上落下一个吻,得逞地一挑嘴角,又去忙碌了。
到了冬天,他们好像要出远门,程予檐将她裹得严严实实的,里三层外三层,活像个大粽子。她下楼梯时看不见脚下,一路滑了下去,众目睽睽之下旋转了几圈,根本爬不起来,出门的计划就此泡汤了,程予檐花了几天时间才哄好她。
后来两人去野外捉野兔野鸡,布置了好些个陷阱,在雪地里生火烤红薯,她吃得脸脏兮兮的,程予檐就地用雪给她擦干净。
……
一场场画面给林厌奚带来不小的冲击,看着有点幸福过头了。难道在这三年里,她跟程予檐都这般恩恩爱爱,有种既和谐又怪异的感觉。
画面一转,白绫过梁,她立于木凳之上,面色苍白双目无神,是要悬梁自尽的节奏。
林厌奚在一旁干着急,想去阻止,却忘了这是梦境,自己触碰不到任何人。只能祈祷有人在这个时候进来。
直到她双脚离地那一刻,也没有一个人进来。她的喉咙撕裂般地疼痛,胸腔也痛,呼吸不上来,双眼充血。身体的本能让她想伸手去抓白绫,于是她用左手死死攥着右手。
这是抱了必死的决心。
林厌奚看得龇牙咧嘴,仿佛她才是那个上吊的人。话也不能这样说,上吊的这个人确实是她。
反正林厌奚好好活到了三年后,而且这是在梦里,她是不会死的。这样想,林厌奚就不着急了,听见脚步声,好奇地扒在门框边看是谁来了。
听雪手中的盆“哐当”落在地上,盆里的水溅得到处都是,湿了她的半条裙摆。她反应极快,两步走上前,抱住一心寻死的人的小腿,扯着嗓子大喊道:“来人啊,救命啊!”
一段更加匆忙的脚步声,程予檐大步流星冲了进来,一刀砍断三尺白绫,将人解救下来。
怀中的人昏迷不醒,程予檐命听雪去请大夫,他掐她的人中,又小心地去探她的鼻息。松了一大口气,好像他才是那个劫后余生的人。
林厌奚看见程予檐抱着她,双手箍得紧紧的,像要拼命抓住什么,额头脖颈青筋暴起,又在极力克制着,怕弄疼她。
“林厌奚,你不准死,我不准你死。”
她幽幽醒来,只看了程予檐一眼又闭上了眼睛,询问意味十足。
为什么要救她?
“我不会让你死的,就算你下了九泉入了阎王殿,我也会把你从阎王手中拉回来。”他道。
“……”
良久,他才说了第三句话:“你死了我怎么办?”
话音刚落,一滴泪自他的眼角滑落。
林厌奚的心咯噔一下,这不是她认识的程予檐,她认识的程予檐才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她竟然产生了用手拭去他泪水的冲动,告诉她自己活得很好。
“我害怕,林厌奚,我害怕。”这次发现了,下次呢,他要是不在呢。
程予檐低着头,林厌奚只看见他颤抖的肩膀,听见他隐忍的哭腔。
“你再给我点时间,我杀了他。”
什么意思?他是谁?为什么要杀他?
看她的穿着打扮,并非是出嫁前的姑娘打扮,林厌奚环顾四周,这显然是程府的装潢。听雪说她是为嫁给程予檐寻死觅活,如今既已嫁得如意郎君,为何还要这般。
而且太奇怪,她太瘦了,皮肉包着骨头,瘦得脱相,毫无美感可言,加上那双如一潭死水的眼睛,说是林中山鬼也不足为过。
她过得很不开心,由此想要通过自杀结束此生。
林厌奚洒脱成性,自认为没有什么事能将她逼到这种地步。可能与程予檐口中的他脱不了干系。
这三年里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林厌奚越来越好奇。又或者,这一切只是黄粱一梦,她嫁给程予檐是假的,瘟疫是假的,她如今看到的这些是梦中梦,没有恩爱,没有寻死。
她要快点醒过来,林厌奚跑出程府,身边的场景一换再换,她不敢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