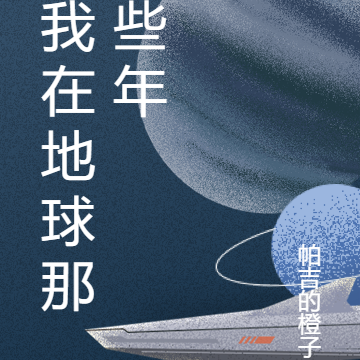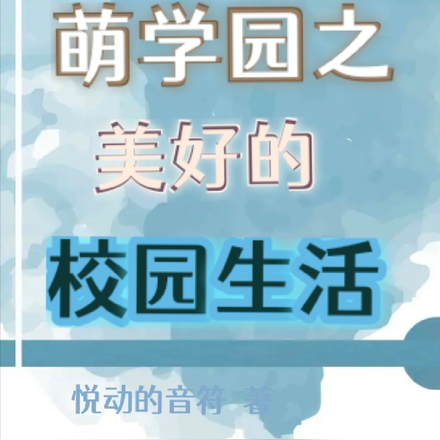第 37 章 听壁角
封秀珍听了这话,更恼了。
“咱们永林?你也知道是咱们永林?从他出生到现在十几年,你这读书人的脑袋缩得比乌龟王八蛋还要深!”
方永强一个斯文人,哪里吵得过一个在流言堆里修炼多年的悍妇。
他浑身颤抖:“你现在要跟我翻旧账?当年你没有同意吗?”
“同意?我哪料得到陆水民个短命鬼死那么早!”
方永强嗫嚅着:“那……那这你也怪不到我头上到呀。”
“是,怪我,怪我信了你跟陆法民那个老兔子的鬼话!”
“你骂我归骂我,你不要牵扯法民……”
封秀珍眼珠子彻底红了,她手指头戳到方永强脑门上:“陆法民什么东西!我骂他半句你就听不得了?啊?你当年怎么赌咒发誓的,你跟他只是老朋友,你没有摸过他的腚……”
封秀珍越说越气,突然一屁股坐倒在地,拍着大腿哭道:“你以为我这些年都不知道吗?我也是自已骗自已,我早知道你们一对兔爷,花言巧语骗了我,拿我借种呢!老天爷啊,你该收了陆法民的贱命,不该要了水民的命啊……我那苦命的水民啊……”
方永强原本还烦躁地在想法子逃开,脸色却突然变了。
外头一直十分嘈杂,可还是有一阵突兀的响动从门口传来,突破封秀珍的蛮哭,像惊雷一样闯进方永强嗡嗡作响的耳朵里。
“谁!”
方永强立刻要过去查看,被封秀珍拖住双腿:“你别想溜,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
方永强急着挣脱,但封秀珍比他粗壮很多,又下了死力气,他根本脱不开身。
窗外闪过一个过分匆忙的影子。
情急之下,方永强胡乱许诺:“你先放开我,你要钱还是要什么,只要我有,都好说,都好说。”
封秀珍喊道:“我刚才在灵堂就跟你说过了,我要你带我到镇上去!”
“好好,好,我带!”
“明天就走!”
方永强还没有丧失基本的判断,否决道:“那不行,明天不是出殡吗?你再等等,再等等。”
封秀珍蛮横道:“等不了!你休想再拿空头支票诓我!”
方永强实在没有办法了,裤子都快被拽下去了。
正扭打着,响起一阵敲门声:“秀珍婶子,你在里头吗?”
方永强被吓了一跳,这要是被人看到他跟一个老寡妇扭在一起,裤子掉到膝盖,他更不要活了。
他一手拎着裤腰,一手在兜里掏来掏去,却只摸到一串钥匙。
那是他医院办公室的钥匙。
方永强看了眼窗外,一狠心,将钥匙串凑到封秀珍眼前:“你先拿着这个,这是我吃饭的家伙什儿,丢了这个,我就活不了了。”
封秀珍一看,白了一眼:“什么破钥匙?几个烂抽屉能锁几个钱?别想糊弄我!”
方永强压低声音,气急败坏:“这是医院财务室的钥匙!”
封秀珍一听,双眼放出精光,立刻撒了手,将钥匙夺了过去,紧紧攥在手心里。
“秀珍婶子?秀珍婶子?”
外头的叫嚷声更大了,底下已经朽了半截的屋门被推得摇摇欲坠。
封秀珍带着得逞的笑望了一眼方永强,爬起来掸了掸裤腿,将钥匙往腰上一塞。
她不紧不慢地走过去,还没伸手,门就被推开了。
外头的人看到封秀珍吓了一跳:“哎呦我说秀珍婶子,你在里头咋不吱声呢?”
封秀珍擦了擦脸上纵横满布的泪痕和汗水,沉默不语。
“哎呦,对不住啊……这……”那人显然是误会了。
封秀珍叹道:“哎……老了,眼窝浅了。你这急三火四的,怎么了?”
那人忙一拍大腿,恢复了刚才急吼吼的状态:“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尔林他大伯………”
無錯書吧那人压低声音在封秀珍耳边说了些什么。
封秀珍吃惊不小,声音猛的拉高:“哪里?!”
“呦,这可邪了门儿了。还有哪里啊?那个野塘!”
那人似乎是打了个冷颤,又嘀嘀咕咕了几句,转身就走了。
封秀珍在门口痴痴地站了一会儿,才重新带上门回到屋里。
方永强躲在土豆堆里,只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听谈话内容涉及到陆法民,早急坏了。
但他又怕被人看到自已在一个寡妇屋里,只好一直缩着身子等着。
见封秀珍终于关了门,他急忙站起来,问道:“怎么了?法民出什么事了?”
封秀珍见他急得这样,眼底透出酣畅淋漓的恨意。
她嘴角噙着痛快的笑,死死盯着方永强。
“快说啊!”
封秀珍捡起地上的那碗饭,又不顾形象地吃了两块猪肝。
咂摸手指头的时候,她却突然笑不出来了,滚下来两行泪。
她拿油乎乎的手抹干净眼泪,转身出了门,留方永强一个人呆愣在原地。
饭有点凉了。
挺好,馊了才好呢。
最好让那肚子里的杂种吃了就变成一滩污血,痛她个三天三夜也流不尽。
封秀珍恶狠狠地想着,心里更加畅快了。
“哎?方老师,这就走了?不留下吃晚饭?里头可在套肠圈呢,老刘的手艺可了不得。”
封秀珍回头去看,方永强跌跌撞撞地往院外奔去,都没有理会旁人的搭讪。
她好不容易自已生生憋造出来的一点子快乐又没有了。
她魂不守舍地拿着饭进灵堂,不得不跟面目可憎的儿媳妇打照面。
这山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跟别人一样,对自已转了态度。
雪上加霜的是,没一会儿,那碗豆腐饭就盖在了陆尔林。
山花急得就要拿手去抓,可碰到陆尔林脸上的棉花帕子后就犯了难。
这帕子必须换掉,脸估计也得重新洗净。
她问一旁呆立的封秀珍:“秀珍姐,这……这得找家里的男人来,咱们女人不干净。”
封秀珍嘴角一丝苦笑:“男人……家里没男人了……”
山花嗔怪着:“净瞎说!永林是还小,这法民可是嫡亲的大伯,是你家的大家长。”
封秀珍如同泥塑偶胎一样,双眼直愣愣得出神。
“法民……法民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