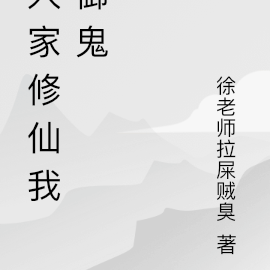第 22章 使坏
“我妈真会杀猪?”
陆永林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想了想,打了个寒噤。
可能是在脑补封秀珍拿着杀猪刀的样子吧。
慢悠悠走回去,周小满才意识到两人刚才跑了很远,都快跑出村口了。
周小满偷着乐,这小子是有多怕自已的亲妈啊。
要是秀儿真会杀猪,估计这小子是不敢再回家了。
周小满也想起了自已的往事。
十几岁的时候,她也急于离家,急于证明自已。
反倒是现在,活在别人的躯壳里,即便有系统任务在身后追着,她也能不紧不慢,由着性子来。
她抬头看天上与他们亦步亦趋的月亮。
以前哪有时间抬起沉重的脑袋欣赏月亮啊?
“永林,你打算考什么中专?”
“我妈让我考会计,毕业了还能分配工作。”
“你自已呢?”
陆永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犹豫道:“……我想考师范,当老师。”
周小满想,果然是经久不衰的香饽饽职业。
她才没有想改变陆永林的命运,只是嘴闲不住瞎问一句。
可陆永林好像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嫂子,你会背《岳阳楼记》,那你肯定也上过初中吧?”
周小满自嘲地笑了笑,嘟囔道:“岂止,我还上过大学呢……有个毛线用,还不是在这里,过几天可能还要去自学养猪……”
“大学?养猪?”
周小满忙捂住嘴,尴尬地掩饰:“我就上了个镇上的初中……有一年下大雪,路不好走,我就辍学啦,然后就……就去养猪啦。”
“下大雪?我们这儿很少下雪的……哪一年啊?”
“呵呵,呵……”周小满努力编着,“十几年前了,你那时候还没不记事呢吧。”
“哦……嫂子你很聪明,没有继续读书可惜了。”
周小满心想:以后在这小子面前说话得有个把门的,他吃瓜的本事可真强啊。我看他也别当什么会计什么老师了,当娱记去好了。
两人又围绕各种古文名篇聊了很多。
周小满看出来了,陆永林对文学是又菜又爱。
可能是阅读的机会少,他的词汇量和对文本的理解都很有限,只知道死记硬背;加上这个年代的老师很多本身文学素养就不高,导致学生们对很多典故都一知半解。
周小满虽然也不是什么学霸,但毕竟是经历过大考的人,一些古今名篇还是信手拈来的。
两人闲聊着到家门口时,陆永林已经十分崇拜周小满了。
“到家了。”周小满说。
刚才还兴致勃勃的陆永林,看到院门就打蔫儿了,站在院门口不肯进去。
周小满笑了笑,粗暴地将他一推,然后快走几步赶在陆永林前头进了灵堂。
她怕封秀珍还举着什么凶器候着他们,小心翼翼探头探脑。
然而,多余。
封秀珍正躺在草垫子上睡得正香,表情放松,鼾声如雷。
陆永林慢吞吞进来,看到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些失望,随即又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落寞。
周小满有些气愤。
儿子大半夜负气跑出去了,亲妈还能睡得这么香。
这封秀珍该不会没长心肝吧?
对待陆尔林也是。
虽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子,但好歹一块儿生活了那么多年,也互相帮扶着艰难度日,总归会有些感情吧。
可正如陆永林的低情商发言,封秀珍在外人面前极尽哀痛,在家人面前则是连装都很敷衍。
無錯書吧周小满突然想起早些时候她在法民大伯面前痛哭的样子。
这样的人,难道面对喜欢的人,也会粉饰自已的情绪吗?
她有些担心,封秀珍对法民大伯,到底是真有好感,还是只是那几年太难了所以利用他?
她一直信誓旦旦不再嫁,是不是因为看不上法民?
哎,牡丹不懂啊。
周小满摇摇头,她就是吃了没谈过恋爱的亏。
好难,什么神经系统,出这种扭曲的任务?
她轻叹了一口气,拍了下陆永林的肩膀:“永林你也睡会儿吧,天亮了还要回镇上找老师呢。”
陆永林问:“那你呢?”
周小满露出一个苦笑:“我守着你哥。”
说罢坐到下首开始叠纸元宝。
陆永林二话不说坐到她旁边,闷头闷脑开始干活。
周小满手上忙活着,心里却憋着坏,想着怎么整封秀珍,又不至于太惹恼她。
现在亲儿子都同意老妈改嫁了,那个大伯明显也是流水有意,她完成任务的唯一阻力就是当事人本人。
她将目光落到了前面的供桌上。
叠纸元宝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陆永林熬了大半宿,没一会儿头就垂下去了。
周小满悄悄起身。
供桌上现在架着七八层的丧礼屉子,是晚饭时间有邻居送来的。
周小满凑上去一层层地查看。
里头都只剩下一些干果、毛巾、黄纸。
果然,稍微值钱一点的被面、香烛、方糕,都已经不见了。
自然是封秀珍悄悄收起来了。
周小满瞥了一眼熟睡的封秀珍。
可真鸡贼啊。
她撅了撅嘴表达不屑,随即蹑手蹑脚转出堂屋,往封秀珍的房间找去。
封秀珍的床头被拆了,原本放在床头的枣红色樟木箱子现在放在床底下。
周小满弯腰把它拖出来,只见上头挂着一把小铜锁。
这种锁特别简陋,周小满从头上取下一个黑色的小发卡,随便一捅就开了。
里头都是封秀珍的宝贝,两套新衣服、一些发黑的银首饰、几张红纸、一些粮票布票,几封旧信……
最上头压着的,俨然是四五套崭新的涤纶被面,几捆没拆封的白色蜡烛。
周小满不想做小偷,没有去翻看其他东西,只是把被面和香烛拿走了
她重新将锁扣严实了,箱子推回原处。
她又在房间一角的凉橱里发现了两碟雪白的豆沙方糕,正好饿着呢,她将每一块都咬了一大口,剩下的仍留在原处。
周小满抱着被面和香烛回到灵堂。
她将被面全部展开搭在屏风上,蜡烛拆开码放在香案上。
这都是它们本该待的位置。
丧礼屉子是亲朋友邻们接济丧主家的一种方式,封秀珍却连这么点都要中饱私囊。
要不说她胖呢,每天挖空心思从家里人身上克扣挪用,全部用在自已身上,她不胖谁胖?
做完这一切,她把一个火盆添满黄纸,放在离封秀珍脚边只有小半米远的位置。
她打开堂屋后面的小门,一阵小风吹进来,带着黎明将至的一丝阴冷。
周小满重新坐到灵堂下首,装作不小心睡着的样子。
就在她迷迷糊糊真要睡着之际,封秀珍对鼾声很突兀地停了。
紧接着,她听到封秀珍似乎跳了起来,声音气急败坏:“天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