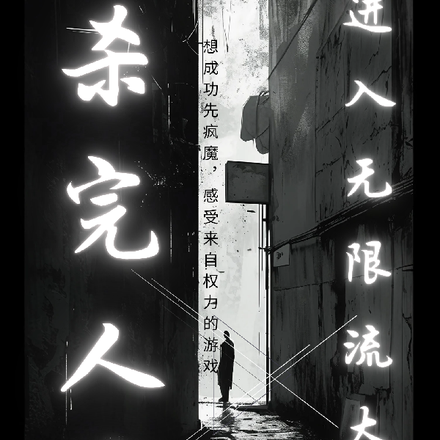皇帝听闻太后突发急病,一路急匆匆地赶到坤宁宫。一进门,便得到太后的当头棒喝,呆愣在原地,错愕地看着太后中气十足的样子。皇帝自知上当受骗,难免觉得恼羞成怒,面露不悦,却也无可奈何,犹豫磨蹭了片刻,最终只能硬着头皮跪下。
“国家大事,国之重臣,岂可儿戏!”太后见皇帝仍是一副不知悔改的样子,心情愈发沉痛烦躁,开口怒斥皇帝,如同训诫一个不知悔改的顽劣小童。玉竹姑姑适时地为皇帝膝下送上一个柔软的蒲团,又为太后递上一杯茶,借机在太后耳边轻柔地劝说几句,略略平息两边的怒火。
皇帝终究还是个孩子,似乎是满腹委屈,像倒豆一半霹雳吧啦地说了出来:“那些阁老事事向太皇太后禀报,动辄以太皇太后的旨意相阻拦,朕这个皇帝形同虚设。这大明终究是朱家的天下,岂能以一外姓妇人为尊。朕是不忍心看着吕后武皇的悲剧在大明重演。”听了此话,太后竟哭笑不得,她站起身,俯下身将皇帝搀扶起来,苦口婆心地劝说:“若是为了此事,那可当真是皇帝多虑了。当年,先帝猝然离世,你虽然贵为太子,但年仅九岁。文武百官皆恐你年幼,不能承担社稷重任,欲立太皇太后的幼子为新帝,仍尊她为太后。太皇太后断然拒绝,执意要你继承帝位。太皇太后担恐夜长梦多,事多生变,便亲手将你抱到龙椅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声泪俱下。立你为新帝。她德高望重,久负贤名,亲自率领文武官员行叩拜大礼,这才有你的今日。”说到这儿,太后难免有些动容,声音夹带上一丝感动和哽咽,继续说:“若说她要做吕后武皇,凭她当日的威望的名声,又何须将这宝座拱手相让。哀家总说你是小孩心性,皇帝总是不服气,如今当真是孩子一般。”太后言辞恳切,虽然平时与太皇太后有些矛盾,但她此刻却是将个人恩怨抛诸脑后,句句肺腑之言,恳切地劝说皇帝。
皇帝听了太后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诲,有所感触,但终究仍是有所顾忌,支支吾吾地说:“可是……朕毕竟是皇帝,文武百官总该给朕些面子。”太后走上前,伸出手轻轻搭在皇帝的肩膀上,慈爱地看着眼前风度翩翩的少年,温柔地劝导说:“好孩子,面子是要靠自已的本事争取的,并非是别人给的。你只管勤勉刻苦,虚心向阁老和师傅请教,何愁日后没有脸面。”少年皇帝扬起英俊的面庞,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一双清澈的眼睛,带着懵懂、委屈和不安望向太后,满怀着对今日的不甘和对来日的渴望。太后轻轻将他搂在怀中,仿佛他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在外受了委屈,回家同自已母亲诉苦。太后一只手轻轻地拍着皇帝的后背,在他的耳边轻声细语地讲道理,渐渐安抚了皇帝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我偷偷瞄着在外面的王振公公,他打起十二分精神,竖起耳朵也在听殿内的声响,此时听不真切,面露焦急之意。正当他急切的时候,门帘打开,太后牵着皇帝的手从殿中走出来,要带着皇帝向太皇太后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王振见状,吓得立刻把脖子缩了回去,怯怯地跟在皇帝的后面,像极了一只淋了雨的狼狈小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穿梭在红墙之下,一路举头丧气地到了仁寿宫外。王振又被仁寿宫宫女阻拦,他有些恼火,求救似地望着皇帝,而小皇帝拾级而上,并未注意到。我斜眼瞄过去,他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下一秒就要跳起来指着那宫女痛骂一阵,却被两个健壮的侍卫拎起来,架着走远,宛如一只任人宰割的小鸡崽,可怜而狼狈。因为丁香的缘故,我对他全无半点好感和同情,内心暗喜,见他被架走,心中得意,有一种为丁香报仇出气的快感。
跨入殿中,一股扑面而来的威严和压迫感令人紧张惊惧。太皇太后高居宝座之上,面色铁青,如同积压了一层阴沉沉的黑云。见到太后和皇帝进来,她的脸色又阴沉了几分,发出一声不易察觉的叹息。她辅佐了三代帝王,如今已是一把年纪,头发花白,容貌不再,却还是有着许多操持不完的烦心事。太皇太后望着焦急的太后和虚心的小皇帝,无奈地站起身,缓缓走到他们二人面前,低声说了一句“随我来”。一行人缓缓走进寝殿之中,才发现那寝殿正中摆放着仁宗和宣宗两位皇帝的灵位。太后和皇帝皆目瞪口呆,毕竟将灵位放在寝殿之中,恐有冲撞。太皇太后接过宫女递上的三炷香,带着太后和皇帝拜祭了二位先帝,轻轻地插在小巧的香炉之中。那铜香炉内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层香灰,显然是已经搁置在此许久了。
太皇太后转过身来,已是从方才祭奠和上香之中收获到了一丝宁静和宽慰。太皇太后转过身,她仔细地端详着眼前稚气未脱的皇帝,少年面庞清秀,风华正茂,满脸的青春朝气代表着国家和大明王朝的未来与希望。太皇太后牵起少年的手,走到灵位跟前,指着一对灵位,用难得的温情语气说:“人人都说寝殿中安置灵位会冲撞,哀家却不怕。皇帝,你好好看看,这是你的皇爷爷和父皇,一个是哀家的丈夫,一个是哀家的儿子,他们日日都陪伴着我。哀家在你身上投入了颇多的心思,只因为你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你们便是哀家在这世间最亲近的人。哀家已是迟暮之年,要这权利名望有什么用。哀家只盼着皇帝快些长大,将大明江山托付给皇帝,日后在九泉之下与你的皇爷爷和父皇相见,哀家也可有个交代,告诉他们大明王朝后继有人。”说到这儿,太皇太后的眼眶已经湿润,声音夹杂上了些许哽咽。她一向是个坚强独立的女人,在风雨飘摇之际仍然能够保持临危不乱的冷静和运筹帷幄的智慧,从世子妃到太子妃、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一路走来,她不知见过多少风浪,经历过多少大事奇事,却始终是一副淡定冷静的模样。但是,她在自已的丈夫和儿子面前卸下了坚硬的铠甲,呈现出女人的温柔和深情。她的眼角滑出两滴晶莹剔透的泪珠,悲伤地说:“哀家无福,做了十个月的皇后,便没了丈夫,做了十年的太后,又没了儿子。天地茫茫,独留哀家一人,如今只盼着孙儿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接过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发扬光大。”
听了这番话,皇帝的眼神略略闪烁,他看着面前老妇人泛红的眼眶,自已的内心激起了一丝波澜,立刻跪下,单膝跪地,懊悔地说:“皇祖母,孙儿今日险些酿下大祸,请皇祖母责罚。”太皇太后立刻将他搀扶起来,拉着他的双手,笑着说:“既然是皇祖母,便是天地之间最亲密无间的家人,做祖母的怎么忍心惩罚自已的亲孙子呢?”
太皇太后牵着皇帝的手,走到正殿的桌椅旁,对坐相视。正殿的空气中,飘散着令人心情愉悦的檀香,最能凝神静气。太皇太后亲手将一盏晾好的茶递到皇帝手中,脸上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温柔地说:“皇帝年轻,满怀抱负,急于施展,这些哀家都明白。但是,所谓治国之道,不能全凭年轻气盛,那些阁老们皆是阅历深厚的人,他们心中闹钟声的东西,绝非是书本那么简单。皇帝少不经事,又易受贱人蒙蔽,但是皇帝的本心最是善良,一心为国,稍加历练,来日必成大器。”此番话如同水一般柔和,缓缓地将道理说出,举重若轻,如同海浪一层拍打着皇帝的心房,扣动了皇帝内心的柔软和敏感。祖孙二人对坐,祖母牵着孙儿的手,眼波中流转着慈爱,轻柔地劝导着误入歧途的孙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此情此景再次展示了太皇太后的智慧和手段,以柔克刚,情深意重,打消了皇帝心中的猜忌和顾虑。
次日朝议之后,太后坐在正殿之中,焦急地等待着内官汇报情况,远远地望见一个小内官脚步匆匆地走入坤宁宫。那小内官刚刚站定,正在请安行礼,却被太后免去,催促他快些奏报。内官躬下身子,禀早朝一切正常,毫无波澜,皇帝和诸臣皆是缄口不言,仿佛昨日并未发生任何事情。奏报完毕,内官再奏,太皇太后请太后往奉天殿偏殿一叙。
太后闻言,大吃一惊,因为她一向身居后宫,从不涉猎前朝政事。太后再三确认后,又单独询问太皇太后所为何事,那内官却只是个传话的,并不知晓内情,只说太皇太后和皇帝已经在偏殿等候,请太后速速前往。一群宫女立刻围上来,为太后梳妆打扮,更换朝服,随后,在一队人马的簇拥下,打着黄罗伞盖,穿过后宫,一路往前朝奉天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