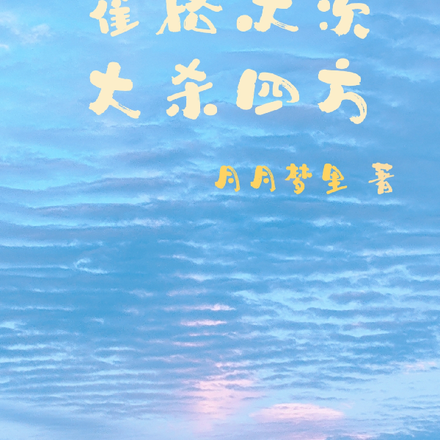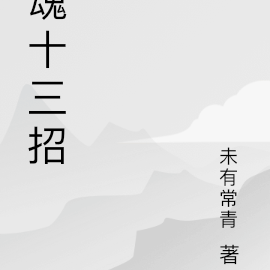我们回去的时候,正巧碰上南戏开场。锣鼓齐奏,弦乐共鸣,场面热闹。
自从太后想起南戏班子,每隔三五日总要召见,与那班主、管事和台柱子交流,听取他们的介绍,研究剧本。近段时间,太后手中总是捏着一本南戏戏文,仔细地赏读,读到高兴处或伤心时,也会同随侍的宫人们说上几句。偶尔兴致大发,太后站起身,捏起手指,迈开脚步,学着演员的样子,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再咿咿呀呀地唱上几句,俨然成了半个行家。玉竹姑姑忍不住说,太后宛如一个贪玩的孩童,沉迷其中,不知疲倦,不知烦恼,人也年轻了许多。我曾经偷偷地瞄着太后,有时见她悠闲安静地读着戏文,有时惟妙惟肖地学唱几句,满面荣光,精神焕发,当真宛如一位回春少女,俊俏美丽,明艳动人。有次,三公主娇嗔地倚靠在太后身上,娇滴滴地抱怨着太后迷恋戏文,疏忽了她。饶是如此,太后对南戏的兴致有增无减,已经将几部大戏名曲的戏文一一读过,颇有心得。
大戏开场,所报的剧目是《西厢记》选段,名为《张君瑞庆团圆》。太后曾经提及这段戏文,因此我略知一二。《西厢记》本是元朝时期王实甫所作的杂剧,班主结合了戏曲的风格和演绎方式,又与婉转动听的昆山腔结合,令这出戏剧重焕生机,大放异彩。《西厢记》讲得是男女爱情之事,全剧跌宕起伏,高潮迭起。为迎合新岁团圆的美好意境,仅演出了最后夫妻二人阖家团圆的温馨场面。故事细腻动人,配合婉转曲折的唱腔,娓娓诉说,动人心肠。
崔莺莺娇嫩俊俏,明眸皓齿,一走一动,身姿姣好,如同弱柳扶风,又似春日的花朵迎风绽放。张君瑞样貌清秀,身材高挑,一言一行,风度翩翩。二人终得团圆相聚的美满结局,喜不自胜,互诉衷肠,尽显小儿女的缱绻深情,如同两只比翼齐飞的相思鸟,又似一双相伴相随的蝴蝶。伴随着深情款款的戏文,演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将大家带入到剧本的世界中。一曲唱罢,余音绕梁,不绝于耳,众人皆是意犹未尽,回味其中。
太皇太后耳目一新,赞不绝口,忙传旨招班主和一众演员入殿召见。太皇太后仔细询问了班主,班主一一作答,详细地介绍了班子的特色与剧目。原来,他们在昆山腔的基础上,吸收了周边地区的特征,丰富了自已的唱腔和风格。在戏文之上,他们细细打磨,在名家名篇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次创作,并虚心地请当地的秀才帮助他们更改词句,使戏文更显文雅细腻,一时之间备受上流社会和书香世家的追捧。太皇太后已是眉开眼笑,赞赏他们这种一字一句、精雕细琢的用心和匠人精神。太皇太后侧头问太后:“哀家往日在宫中从不知有这样一支戏曲班子,太后有心了。只是不知,太后从何处寻得他们?”太后笑着回答说:“是在江浙为官的钱贵。去年年初,他依照惯例进京述职,想向太皇太后表一表忠心,但知道太皇太后最痛恨贪官和贿赂之事,恐弄巧成拙。于是,他便送进宫中一支戏曲班子,算不上什么贵重之物,只当是地方特色,博太后一笑。”太后听后不言,吩咐周围的宫女将赏赐分发下去,又点了一出《荆钗记》。那班主领了赏钱,欢喜的不得了,连连叩头谢恩,匆忙带着一众演员退场,更换戏服妆造。
待一众人等都退场,太皇太后才开口说:“本应也赏赐钱贵一份。但是,如此一来,哀家怕是助长了官场的不良风气。他是个好官,治下有方,百姓安居乐业,颇有建树。但若是此时赏了,旁人只会以为揣摩圣上的心思,远比勤恳工作、为官清廉重要。日后,若是人人效仿,今日进个戏曲班子便官升一级,明日靠着珍奇异宝平步青云,岂非助长官场污浊之气。”她思量了片刻,从头上拔下一根金钗。那钗子通体鎏金,钗头处雕刻成一朵祥云的样子,云朵之上镶嵌着七颗黄豆大小的珍珠,圆润细腻,散发着淡粉色的光泽。她将那根钗子交给身边的侍女,吩咐说:“哀家记得,钱贵家中有个独女,便将这金钗赏赐给她的女儿,日后可添作嫁妆,算是哀家的一份心意。”如此一来,既赏赐了钱贵,却又未给他本人任何实际性的利益和好处,反而将这份恩赐转化为对幼女的祝福和盼望,不偏不倚,十分巧妙得体。我暗自叫好,心中为太皇太后的政治智慧而佩服的五体投地。
太皇太后思量了片刻,回想起了那班主方才提及,南戏的戏曲多表现小儿女之接的细腻感情,又吩咐说:“此类的曲目,宫中每逢年节,花好月圆之时,最合时宜。只是,不可多奏,一年总有个三五次便够了,否则传扬出去,朝臣阁老们会说,朝廷不思进取,只知些儿女私情的享乐之事。太祖皇帝所定下的几出忠君爱国的戏剧,不了荒废。”太皇太后思虑周全,时时刻刻都在为皇室和国家考虑,众人忙起身,双手相握,躬腰行礼,为之称赞。见众人都表明了态度,太后放松了神色,脸上重新浮现出一抹笑容,和颜悦色地说:“哀家并不全然拒绝这种戏曲,艺术并无高低,百花齐放才是最好的。年后,三公主出嫁成婚后,也该张罗着为皇帝钦定皇后人选。到时候,登台亮相,便是图一个琴瑟和鸣、夫妻情深的好兆头。”众人又连连应声回答,皆称赞太后思虑周全,胸怀广阔。
此次宫宴之上,我第一次见识到太皇太后高明的政治智慧和精明的政治手段。她已是历经六朝的老人,经历过太平盛世,也曾感受过靖难之变那场浩劫。如今,她的两鬓已经染上风霜,皮肤不复往日的光泽,但是人生阅历都积累在心中,一点点塑造了她的英明和睿智。更难得的是,她从不夸耀,总是默默地退居幕后,将风光和功名都交给皇帝,为年纪尚轻的新皇帝积累威望和口碑。自入宫以来,我已见过宫中不少人,她是最令我佩服的一位。
我偷偷注意到,太后似乎对太皇太后的话并不十分满意,但碍着体面尊贵,每每都是隐忍不发。从太后角度而言,太皇太后屡屡尊崇静慈法师,又指责她钟爱的南曲为靡靡之音,似是故意针对。而太皇太后而对于太皇太后,她所做的一切皆遵守规矩制度,处处为国家生计着想。虽然绝非刻意刁难,但是日子久了,太后心中总是别扭不爽。这幅景象恰如我的祖母与娘亲,皇宫之中,权大利大,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和博弈的焦点。总归,这是天下第一麻烦的婆媳关系,更是天下第一焦灼的家庭。
不过,到底是除夕新岁,大家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之中,醉心于每日的欢声笑语、丝竹管弦,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被快速地抛诸脑后,人们又投入到了新岁的快乐和欢欣之中。欢庆了几日,宫中恢复了上朝,文武百官再度投身于朝堂之上,共议国是。朝议第一日,太后悠闲地坐在床边,研究黑白二字。她甚少参与朝政之事,一切都交于太皇太后和皇帝,而她每日只听取内官简明扼要地禀报今日的情况。太后看了半晌,抬头望天,早已是过了往日内官通报的时辰,顿时感觉异常。未免意外,太后差了个坤宁宫的内官去前朝打探消息。那小内官领命后脚步匆匆地离开,约一炷香的功夫,又急匆匆地回来。一进门,那小内官一把跪倒在地,慌乱地说:“太后,大事不好了。今日早朝,有朝臣上奏,请求罢免几位辅政阁老,免去太皇太后的听政问政,归政于皇帝。众朝臣议论纷纷,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没个定论。不过,看皇帝的意思,大约是同意的,奴才回来的时候,皇帝正说要拟定圣旨,昭告天下呢。奴才不敢怠慢,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禀告太后。”
太后一听,大惊失色,急得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忙打听仁寿宫的消息。太皇太后虽然知晓了此事,却不能出面阻拦。太后更为恼火,尽管在诸多事情上她与太皇太后这对皇家婆媳有诸多分歧和矛盾,但她深知皇帝还不具备独自处理朝政的能力,国家和朝廷离不开太皇太后。她一只手扶着桌子的一角,指节已经泛白,吩咐道:“速去告知皇帝,就说哀家突发心口绞痛,情况危急。另外,把那个上书建议的臣子留下,拖出午门外,痛打二十下。”这自然是谎话,不过是使了个调虎离山的法子,将皇帝从朝廷中唤来,阻止这场荒唐的闹剧。果不其然,皇帝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坤宁宫中,满目焦急,直愣愣地冲进来。我抬起门帘,独让皇帝一人进去,让形影不离的王振拦在门外。他面露不悦,轻蔑又怨恨地看了我一眼,但碍于太后的旨意,也无话可说,只能独自一人站在殿外。
“跪下!”太后一声怒喝,底气十足,怒火中烧,显然不是大病一场的危急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