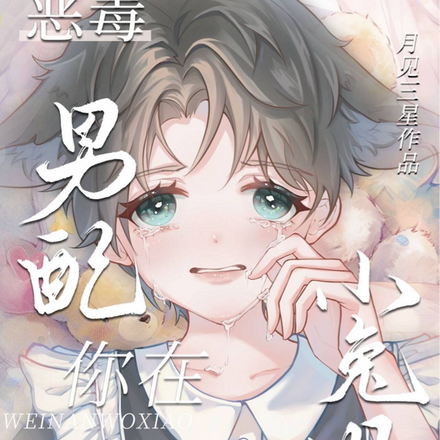每逢新年,坤宁宫的宫人们总是格外忙碌。即便如此,今年与以往不同,差事繁杂,多如牛毛。入冬后,除夕新岁,之后便是二月二的太后寿诞,紧接着是三公主大婚出嫁。事情接踵而至,桩桩件件都是不能马虎的大事,人人需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认真做事。众人常为此心烦意乱或忐忑不安,玉竹姑姑此刻便如同坤宁宫的一根定海神针,不慌不忙地教导众人说:“莫要慌乱,事情总是一件件做的,都能做好,总会挺过去的。”眼下,最要紧的事情便是先小心伺候除夕宫宴。
眼看时辰差不多了,玉竹姑姑轻轻地将太后唤醒,先伺候了一顿茶饭垫垫肚子。玉竹姑姑解释说,晚上的宫宴场面盛大无比,但是为了顾及皇室的尊贵和体面,只能略略地吃几口,大多是吃不饱的。因此,各宫在宴会前后都会自行准备一些吃食,以做充饥之用。太后进了些饭菜,又饮了两碗三鲜鹌鹑羹,把肚子填了七八分饱。紧接着,三四个宫人便围了上去,簇拥着太后梳妆打扮,穿戴繁琐复杂的朝服,约莫又花费了一个时辰的光景。冬季天寒日短,一切收拾妥当已经是黄昏时分。太后纵目远眺,望着隐藏在屋檐后的夕阳,将天边的云彩渲染的通红,与金黄色琉璃瓦连成一片,喃喃地念叨着:“又是一年的光景。每到年节,宫中举办宴会,哀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先帝在世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贵妃,她是皇后,她坐在我的上头,居高临下,气派极了。但是我从不慌乱,因为我知道,先帝的眼里、心里都只有我一个人,就算她坐的离先帝再近,终究也进不到先帝的心里。就像现在这样,就算太皇太后抬举她,她也穿不得这华贵的朝服,只能当这紫禁城中的尴尬人物。”玉竹姑姑为太后披上一件赭红色的毛领厚实披风,应声附和说:“太后说的极对,既然如此,当下无论如何都不必挂在心上。太后,时辰不早了,咱们该启程了。”
黄昏时分,一行人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浩浩荡荡地前往上梅园。宫中的宴会因时节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举办场所,以观赏四时美景,增添乐趣。春日的碧柳苑,夏日的雨荷轩,秋日的菊傲馆和冬日的上梅园,便是四处景色绝佳的地方。上梅园中种着红白两色的梅花,犹以红梅居多,已经傲霜开放。火红的花朵绽放枝头,连成一片,宛如云霞一般。置身其中,淡淡的香气进入鼻腔,渗透入每一个毛孔之中,令人精神放松,心情愉悦。那朵朵白梅点缀其中,便如同冬日的精灵,踮起足尖,以红霞为幕,翩翩起舞,我们穿过红梅,仿佛是仙女穿过层层烟霞,径直顺着小径,前往那神秘而美好的仙境。
轻柔的乐音响起,如同仙乐一般优雅动听,众人高举酒杯,共贺新春之喜。太皇太后高居主位,依旧是将静慈法师的座位高于太后。一切皆在太后的意料之中,这次她面色如常,眉宇舒展,优雅从容,只是一味地命人将桌上的菜色不断分发给静慈法师和众人,以示恩情。我忽然明白了太后先前命静慈法师供奉《道德经》的内情,正如宴会赐菜一般,一命一赐之间,看起来是恩赏和宽厚,背后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告诫和警示,无形之中向对方突出了自已的主人地位。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后有些昏昏沉沉,再加上宴会的乐舞千篇一律,乏味无趣,以更衣为由先行离场。我和玉竹姑姑陪同着太后漫步在红梅之中,吹吹冷风,头脑清醒许多。我们走了几步,天上忽然窸窸窣窣地飘落几片雪花。太后伸出手,雪花轻轻地落在她的指尖,冰凉一点,最终化为一滴水。太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轻轻擦去指尖的水,笑着说:“好极了。瑞雪兆丰年,是好兆头。雪中赏红梅,最有情致。”话音刚落,我们便远远地看到红梅之中有人影闪过,天光昏暗看不真切。玉竹姑姑迅速护住太后,厉声斥责道:“谁?!是谁在那里!鬼鬼祟祟,还不快出来。”
“太后莫慌,是旧相识呢。”一个温柔熟悉的女声传出,随后缓缓地从红梅之中现身,来者正是静慈法师。她依旧是一身道姑打扮,端正地向太后行礼,笑着说:“贫道有些困倦了,想出来走动一下。不曾想太后也在此处散心,想来给太后请安,又怕打扰了太后的好兴致,犹豫不决,却惊吓了太后。请太后恕罪。”太后瞟了她一眼,几步走上前去,微微抬手示意她起来,讥讽地说:“倒也是个知礼数的,哀家还以为你在太皇太后身边待久了,以为自已将来也能做太皇太后了呢,忘了紫禁城的规矩。”静慈法师在宫中多年,自然也知晓紫禁城中的纠葛与算计,她眉宇淡然,恭敬地表示自已不敢忘记身份,行僭越之事。太后听了这话,得意地笑了,昂起头,故意不用正眼瞧她,趾高气扬地说:“那便好。不然,哀家有的是法子,在这宫里,终究还是贵贱有别。静慈法师是出家修行之人,看破红尘,大彻大悟,自然明白,过往的风光皆是往事,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而哀家,便是这场比赛最后的胜者。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输了,便该认命,任凭处置。”话说到此处,言语之间尽是奚落嘲讽的意味,我听着难免觉得刺耳难受。那静慈法师只是淡淡一笑,思量了片刻,低声说:“贫道听说,曾在太后身边侍奉的墨竹每年都会为太后和皇帝送上一份礼物,旁人都说她是忠仆,情深义重,出了宫也对太后和皇上念念不忘。不知今年,她又用什么奇珍异宝进献太后和皇上?”
此言一出,太后神色大变,整个人僵硬在原地,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玉竹姑姑立刻上前搀扶住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胳膊,示意她不可慌乱。太后站定了身子,怒目圆瞪,低声呵斥道:“大胆!你胡说什么,还不快闭嘴。否则,哀家即刻便把你发落去暴室。”静慈法师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太后何必急躁。贫尼看到玉竹,只是想起当年墨竹、沁竹共同侍奉太后的情景,有感而发。太后天威震怒,若是将贫尼打发去了暴室,岂不是招惹口舌是非,徒增烦恼。”太后闻言,怒火中烧,却只能忍耐着不好发作。她恶狠狠地盯着静慈法师,仿佛要从眼中发射出一把钢刃,即刻将她斩杀。静慈法师见状,又行了一个礼,弓着身子,低声恳求说:“贫尼无意冒犯,也从来不是搬弄是非之人。自打被先帝厌弃废黜后,贫尼只希望能够潜心修行,了此残生,别无他求,养太后成全。”说罢,她直起身,后退两步,离开梅林。
太后呆在原地,恨恨地望着静慈法师扬长而去的背影,咬着牙说:“玉竹,她这算是要挟哀家吗?”玉竹姑姑赶忙搀住太后,低声说:“不会的。若真是拿捏把柄,她断断不会隐忍这么多年。依老奴愚见,不过是担心来日太皇太后不在了,想给自已找个安身立命的法子。太后不必惊慌,这么多年了,她从未提及,日后想必也不会说出去的。”尽管如此,太后仍是觉得揪心,咬着牙恨恨地问:“墨竹的事情她是怎么知道的?”玉竹姑姑思量了片刻,回答说:“其实,墨竹当年出宫时,宫中便时常议论。那时候,皇帝才刚刚出生,众人议论太后不看重为人母的喜悦,反而急于铲除招蜂引蝶的宫女,有些古怪。不过,宫中常有捕风捉影的事情,大家终究是议论,又没有真凭实据。太后将墨竹安置在了自已的娘家,有人照看,是不会有差错的。”
提及娘家,太后哀叹一声,不悦地说:“说起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整日只知道饮酒作乐,寻花问柳,刚把人送过去就打上了主意,简直是色胆包天。幸亏有哥哥盯着,不然还不知要闯出多少乱子,惹下多少麻烦。”她思量了片刻,转过头去,同玉竹姑姑说:“说到底,哀家方面给哥哥传个话,墨竹的那份东西就不要送进来了。”玉竹姑姑正要答应,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摇了摇头,说:“老奴认为,这样反倒不好。静慈法师也只不过是听些宫内流言,再加上自已的揣测。若是往年都送,今年停了,反倒坐实了这件事情。依老奴之见,今年不仅要如常送进宫,还要宣扬褒奖她的一片赤诚之心。”太后点了点头,又站在梅花中,吹了半晌的冷风,才淡淡地说了句:“咱们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