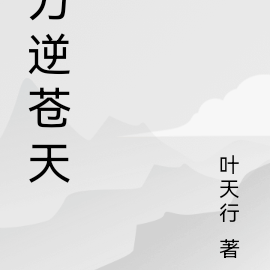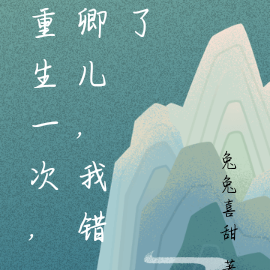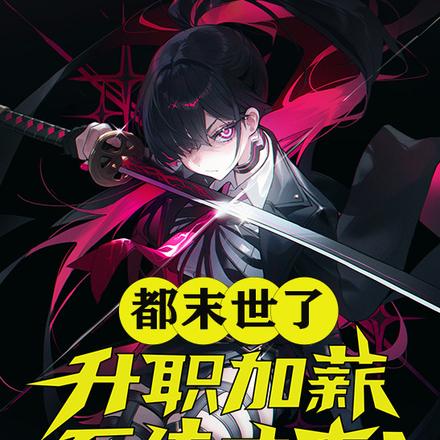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和忙碌之中,除夕悄然而至。今日是年关岁末,人人一大早便纷纷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之中。
晨起,所有宫人们换上了新岁的宫服。内官们是绣着两尾红色鲤鱼的黑色官服,宫女们是嫩绿色的宫服搭配桃粉色或鹅黄色的夹袄,上面绣着花团锦簇的图案,行走在宫中便如同一尾尾欢快的鱼儿和一枝枝吐露绽放的花朵,寓意着春日的勃勃生机。按照规矩,每年的除夕、元日和元宵时节,宫人们可自行佩戴一些首饰钗环或祈福物件作为装点。玉竹姑姑年岁大了,换上一身深绿色的宫服,不失优雅庄重。她从柜子顶部的最深处取出一个不起眼的木匣子,打开后竟是琳琅满目的首饰,应当是入宫多年以来的赏赐和家当。她拿起最顶层的一个羊脂玉镯,套在手上,立刻合了匣子,束之高阁。她身上的其他地方并未特殊装点,那镯子又深深地隐藏在宽大的衣袖之中,若不留心看起来与往日并无差别,一如她往日低调内敛的行事风格。一来我进宫时日不久,并无什么积蓄,二来我知道姑姑不喜招摇,因此,我只从小包袱中翻出我娘和丁香亲手缝制的香囊,一左一右地系在腰间,以代对亲人朋友的思念和牵挂,倒也是相得益彰。
整理完毕后,我们二人同往坤宁宫,伺候太后梳妆打扮。太后今日需穿着繁琐华贵的朝服,完成朝见、宫宴等一系列宫内的礼仪活动。在宫人们的伺候下,太后梳洗打扮完毕,穿戴一新,张开双臂,欣赏着铜镜中倒映出的美人影子。她头戴九凤点翠金冠,上面镶嵌着红蓝宝石和圆润饱满的东珠,九只凤凰用点翠工艺制成,色彩明艳,随着人脚步和动作轻微抖动,栩栩如生,仿佛下一刻就能煽动翅膀翱翔于云霄。身着深青色翟衣朝服,上绘有十二对翟鸟飞跃在红色的小轮花朵之间,深红色领缘袖缘描边,上面绘有金色小云龙纹样,绣工灵动进展。下着深青色长裙,裙边绣着一圈金色云龙,每只口中缀着一颗黄豆大小的明珠,随着衣裙摇曳而微微闪光。足蹬一双青色翘头履,两只高翘的鞋头上各缀着一颗鸽子蛋大小的血红色纯净宝石。远远望去,如同天宫的王母娘娘降临人间,雍容华贵,光彩照人。太后皮肤白皙,头发乌黑亮丽,纤细弯弯的眉毛如同两座匍匐的远山,嘴唇似一颗红樱桃,好一个明眸皓齿、风姿绰约的美人。
梳洗完毕后,太后步入正殿,高坐在坤宁宫金色鸾凤椅上,俯瞰众人。坤宁宫的宫人们向太后叩头问安,如山呼海啸一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殿内殿外黑压压跪了一大片,齐声恭喜太后新春之喜。太后一声“赏”下来,我和玉竹姑姑等几位贴身伺候的宫人便立刻将预备好的赏钱分发下去。各人领了赏钱,自然喜不自胜,各个面露喜色,谢恩之后便纷纷退出殿外,投入到了一天的忙碌工作之中。
紧接着,是皇帝率领公主王爷等皇亲国戚拜见太后。皇帝站在队首,一身明黄色的龙袍挺立于人群之中,如同一棵青松般挺拔,九旒冕垂下的珠帘遮挡了少年清秀俊朗的面容,仍难以掩盖少年扑面而来的帝王之气。我好奇地看着,许是每日练习弓马骑射的缘故,皇帝似乎比上次健壮了许多,皮肤也黑了几分,人也显得孔武有力。红苕兴奋地冲我眨眨眼,示意紧跟皇帝身后,穿着紫色朝服的是郕王殿下。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见郕王殿下虽然比皇帝年幼,但身形更为高大。他头戴六旒冕,但仍能看出皮肤白皙,举手投足之间一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形象。我斜眼看去,红苕的欢喜溢于言表,她双眼放光,周围的几位年幼宫女也是一番欢欣鼓舞的样子,偷偷地瞧着年少英俊的郕王。我常听宫女们讲起,郕王是先帝幼子,出身尊贵,温润如玉,平易近人,每次进宫皆是谦和有礼,礼数周全,从不对宫人们吆五喝六,从未严厉训斥,因而广受宫人们的喜爱。
朝拜后,皇帝与郕王、公主等子女留下,同太后少叙片刻,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出发,前往仁寿宫拜见太皇太后。礼毕,众人留在仁寿宫中,一起饮茶叙话。太皇太后望向郕王,笑着说:“多日不见,郕王又长高了几分。不知吴贤妃可好?”郕王起身行礼,恭敬地回答:“幸得太皇太后和太后庇佑,母妃一切都好,特意嘱咐儿臣今日向太皇太后和太后问安。”话音刚落,他便双膝跪地,行三跪九叩大礼,果然是彬彬有礼、久负盛名的郕王殿下。太皇太后笑着让他起身,又继续说:“如今你在外立府,进宫的机会不多。既然来一趟,有一人你不可不见。”说罢,她便唤出静慈法师,坐在身侧,有意将静慈法师抬高于太后,又扭头对郕王说:“你幼时,静慈法师对你百般照顾,又同你母亲吴贤妃的交好。如今,你虽然出宫立府,也不可忘记静慈法师幼年的抚育之恩。”郕王抬起眉眼,瞄了一眼太后的神情,只是点头应下,不敢多言。
静慈法师一身朴素道衣,不着粉黛,素面朝天,显得超凡脱俗,不落凡尘。她出来便要行礼,被太皇太后阻拦,显得有些尴尬。太皇太后满面笑容地看着静慈法师,一脸慈爱,慢条斯理地说:“慌什么,你是他们的长辈。大家都是一家人,今日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地规矩,快来哀家身边坐着。”又扭头吩咐身旁的侍女,换一盏静慈法师最爱的苦荞茶。静慈法师局促地笑了笑,对太后施了一个道家的礼,拘谨地坐在太皇太后身侧,一言不发。自打静慈法师出现后,太后一直神色异常,沉闷不言,想必是憋着满肚子的怨气和火气。偶尔说几句话,也是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气氛逐渐变得僵硬而凝重,四公主跳出来,站在中间,落落大方地背了一首近日诗歌。“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儿臣祝太皇太后、太后、皇上、郕王哥哥、各位姐姐和静慈法师新岁理想,平安如意。”我偷偷观察太后的脸色,许是四公主将太后置于静慈法师之前,她的眉宇稍稍舒展,露出一丝欣慰和满意的笑容。
太皇太后满意地点点头,转过头看向皇帝,笑着说:“近日,我听师傅说,皇帝在读书文墨上不大用心。皇帝不该只顾着弓马骑射,也该学些经事治国的孔孟之道。”皇帝不以为意,他蛮不在乎地说:“公主方才背诵的正是北宋王安石的名篇。他推行改革之道,只可惜一群文人终究是救不了这个国家。中原大地,铁蹄肆虐,烽烟四起,连那徽钦二帝都沦为金人的玩物和奴隶。可见,满腹诗书不如武义在身,之乎者也不能保家卫国。”说到此处,皇帝全无悲悯同情之意,反而尽显不屑讥讽之相。
太皇太后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收敛了笑容,皱起眉头,不悦地说:“皇帝自然有皇帝的要务,领兵打仗是将军的事情。皇帝终究不能做个只知道穷兵黩武的皇帝。”太后见形势不对,赶忙出言缓和气氛,温柔地说:“皇帝与先帝脾气秉性大不相同。先帝素日最爱水墨丹青,琴棋书画,却生了皇帝这样一个活泼好动的儿子。我时常觉得奇怪,有一次问先帝,才知道他幼年跟在成祖皇帝身边,也是舞枪弄棒,一刻也停不下来。这才知道,原来皇帝的勇猛和胆识是与成祖皇帝一脉相承。”
“母后此言甚是。”皇帝骄傲抬起头,兴奋地说,“朕有今日,也是得益于父皇的教导。父皇也时常同朕讲太祖和成祖皇帝的事迹,教导朕做一个勇毅果敢的皇帝。朕记得,幼时父皇将朕抱在膝上,问若是来日蒙古铁蹄侵犯,是否敢披挂上阵。朕回答,敢。父皇甚为满意,只叫朕不要忘记此誓言。朕以为如今虽然是太平盛世,但是绝不轻视怠慢尚武风气,断断不敢忘记父皇的教导和当日的诺言,否则徽钦二帝的悲剧又要重演。二弟,你说呢?”郕王听到皇帝询问自已,心惊胆战一般,僵硬地站起来,看着抛出问题的皇帝和神情严肃的太皇太后,只觉得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太后看出郕王的为难,体谅他年纪轻轻,不敢得罪太皇太后,又不敢忤逆皇帝,再度开口帮助郕王解围。“好了,今日是除夕,取消了朝议。咱们便如同最普通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只管说些家事闲话,不谈国政。”众人又围坐在一起,闲聊了片刻宫内宫外、皇亲国戚的琐事,渐渐地也就没有话题。太皇太后心情欠佳,不满皇帝的刚愎自用,不听劝阻,便以劳累休息为由,遣散了众人。
众人在仁寿宫前各自散开,休息片刻,等待晚上的合宫宴会。太后坐在高高的轿辇上,一路只是直愣愣地望着前方,并不说话。到了坤宁宫外,她快步走进殿中,来不及将繁琐宽大的朝服解除,已经掩盖不住内心的怒火,随手抓起一把象牙梳子重重地摔在地上。伺候的宫人们不知缘由,吓得跪了一地,口中不停念叨着“太后息怒”“太后恕罪”此类的话。我和玉竹姑姑一直随侍,自然明白太后的怒火从何而来。玉竹姑姑不慌不忙地走到角落,捡起扔在地下的梳子,随手递给一位近处的宫女,示意跪着的宫人们起来。她几步走到太后身边,口中说些柔软安慰的话,哄着太后平静下来后,带领她们继续侍候太后更衣。待更衣完毕,太后屏退了左右,不满地抱怨:“静慈法师是什么?她的地位竟然也敢越过哀家,当真是以下犯上。当初,若非先帝怜悯,特赐恩旨留她在宫中带发修行。否则,她这条小命能不能活到今日还未可知。”
玉竹姑姑递上一盏茶,笑着说:“太后所言甚是。既然如此,太后又何必与她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宫中人人皆知,后宫之中,太皇太后之下便是太后,又有谁真的在意她呢?”太后仍是满面怒容,手用力地捏住炕桌的一角,心中憋着一股气。玉竹姑姑见状,继续宽慰劝说:“蟪蛄不知秋。太后是明事理的人,读书见识都远在老奴之上。自然明白,什么叫做来日方长。”
太后听了这番话,豁然开朗,心情放松了许多,慢悠悠地依靠在软枕上,悠闲地看着自已水葱一般纤细白嫩的手指,一边看一边思量。忽然,她轻笑了一声,拿起一旁的茶盏,漫不经心地看着杯盖上的花纹和杯中的茶叶,气定神闲地说:“正是如此。大公主病病歪歪,自顾不暇,二公主幼年夭折。她无儿女傍身,孤苦伶仃。如今,太皇太后可怜她,可是太皇太后终究是年岁大了,自打入秋后,大病了几场,身子已大不如前。这世间,怎么可能真的有万寿无疆之人呢?待到太皇太后驾鹤西去,哀家倒要看看宫中还有谁能护着她。”听了这话,我心头一惊,一向只觉得太后是个宽厚温柔的妇人,一心向佛,慈爱善良,但却从未想到她也会有心狠手辣的一面。
玉竹姑姑站在一旁,小声地提醒太后:“任凭她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起什么大风浪。老奴倒是担心郕王,他幼年时多得静慈法师的照顾,若是来日将她接入王府颐养天年……”太后不以为意地摆摆手,神情放松,淡定地说:“哀家是太后,我儿是皇帝,宫内的事情还轮不到郕王做主。”说罢,太后缓缓走进寝殿,拉上帐子,合上眼睛,稍作休息,只等待今日黄昏日落后参加除夕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