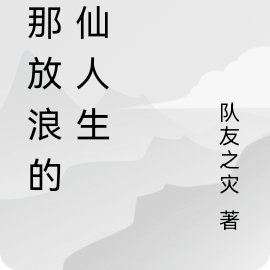当送殡的喇叭吹响,小小的房红文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只知道,疼爱自已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自已。
这一年,家里只剩自已和母亲两个人。
“房红文,没人疼,摔倒只能自已爬。房红文,没人爱,大白馒头就咸菜。房红文,没老爸,夜晚黑黑好害怕。房红文,没奶奶,从此再也没人爱……”
嘲讽的歌谣还在继续,却再也不会有任何人、会拿着扫帚来驱赶这些孩子们了。
房红文用袖子抹了抹眼泪,决定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第一次,终于将嘲笑自已的男孩按在地上狠狠胖揍了一顿:“你要是再敢唱,以后老子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呜呜……娘!”男孩跌跌撞撞地哭着跑回家了。
这一次,男孩在离开时没有再做鬼脸。因为他的脸已经成了真正的“鬼脸”。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宝宝,以后你就别再招惹那个扫把星了!你看看你啊,老被他欺负,都欺负成啥样儿了!”女人心疼地给用冰袋给儿子敷着,“那个房红文有断掌,断掌的人克六亲哪!靠近他的,没一个有好结果!他家已经死了爹又死了奶,咱们还是离他远一点!知道了吗?”
“那个房红文,先克死了他爹,又克死了他奶。”男孩的母亲在村里散播着这话,“两个手都是断掌!右断掌,克六亲哪!”
“啧啧啧……还真吓人哩!”一个婶子将袖子撸起,“哎呀,我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看你看!”
“你还真别说,老话还真是有讲究的。”另一个婶子边将瓜子皮吐在地上,“他们家现在就只剩娟子一个了。”
“我看啊……她也快咯!呵呵!”另一个女人冷笑道。
“哎!真是命苦啊!”一个女人摇着头。
“肯定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另一个女人翻了翻白眼。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小兔崽子真就是个天生的地痞流氓!把我儿子都打得眼睛都肿了好几天呢!”女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呀!这瓜娃子,这么狠呢?”嗑瓜子的婶子将一口瓜子壳“呸”地吐在一边,竟惊讶到忘了再嗑。
“就是的!”女人闻言,表情更伤心了,“只差毁容了不是!”
尽管再也没有孩子敢在房红文面前唱那首歌谣了,村里却开始出现:房红文断掌克六亲,先克死了爹、接着又克死了奶的说法。
那一年的秋天,村里突然来了一个游历四方的道人。
道人一袭深蓝色宽松长袍,脚上着一双十方鞋,行路轻快如风。衣袂摆动间,是飘逸出尘,仙风道骨。
经过稻田的时候,老道一眼就看见了正在帮母亲劳作的房红文。
遂呼喊到:“小娃娃,你来!”
房红文抬起弓着的腰,见老道喊的是自已,便迅速从稻田里跑了过来。
老道拿起房红文的双手,翻看了掌心,又问过房红文的八字。掐了掐指头以后、摸着胡须,低头怜爱地看着脸蛋红扑扑、黑色大眼忽闪忽闪的房红文。
“此子命格特殊,若遇贵人指点便可一飞冲天;然命运多舛,只适合孤身寡宿,方可保家中安宁……”老道叹了口气,“孩子,珍惜你与家人最后相处的日子吧!切记,你不单要离开家人,而且要离得越远越好啊……”
娟子打小没读过书、不识字,也没有什么文化。虽说自已听不懂老道到底在说些什么,这些话又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最后那句,她却是听得懂的。
她当然听得到村里人谣传的:右断掌,克六亲那句话了。只是她一直告诉自已,这不过是农村人眼界的狭隘、以及封建迷信的劣根使然,无需理会便是。
“老先生,您说……什么叫珍惜与家人最后的日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娟子的口吻里是深深的担忧。
“孩子是个好孩子啊!但只有离开家乡,而且得离地越远越好,家中方能平平安安。至于他,最终到底是成为人中龙凤、还是一个市井之徒……一切,也要看他自已的造化了。”老道谦和地微笑道。
“您是指……我必须和红文分开吗?”娟子难以置信地问道。
有哪个母亲愿意过与孩子分离的日子呢?
“没错。”老道捻着胡须点头道。
“不能啊……孩子现在才七、八岁,离开家,他一个人又能去哪里呢?”娟子欲哭无泪,“我就是死,也不要紧。但是,不管是我死了、或者孩子一个人过,这都要怎么办才好呢?”
“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老道叹了口气,“好好珍惜剩下的日子吧!”
娟子只将老道的话藏在了心里。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倒也过得平静。二人也渐渐忘了这事。
虽不免活在流言蜚语中,贫困的处境让二人也总是不被村里人待见。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房红文倒也是极其懂事和孝顺。
转眼,房红文渐渐长大。
像父亲一样小麦似的健康肤色,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紧致结实的肌肉和身材,彰显出他男子汉的气概。十五、六岁的房红文,已经生得比村里其他孩子都高挑、俊朗了。
尽管村子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告诫过自家姑娘:千万不要靠近房家。然而,思春期的女孩儿们在干农活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对房红文流露出充满好感的眼神。
众人之中,尤其属村长的女儿毫不避忌。就像她那位总向人施慈爱的父亲一样,平日里不论发生点啥,姑娘总是独独对房红文偏爱,直偏爱到了帮亲不帮理的程度。
“明明是你家的牛踩烂了房家的地,你不看好你家的牛,还有理了?!”春喜双手叉腰,气势如虹。
“我家的牛爱走哪里走哪里。再说,房家人自已都没说话,用得着你管么?”黑黑瘦瘦的彪子不甘示弱道。
“我就偏要管!怎么地了?”春喜骄傲地说:“我是村长的女儿,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帮我爹管这事儿!今天你就直接说,这踩坏的稻谷得赔多少钱吧!”
对方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又觉得自已无法反驳:“反……反正你又不是村长,我干嘛要听你的。”
“因为今天就算村长来了,这公道也得是这样主持!没区别!赶紧的!拿钱!”春喜蛮横地说完便伸出手。
“要钱没有。”彪子丝毫不肯松口。
無錯書吧“那好!没钱是吧?欺负人是吧?看我不打死你!”
正当春喜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只听得身后一个声音怒吼道——“常!春!喜!”
原来,是春喜的母亲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