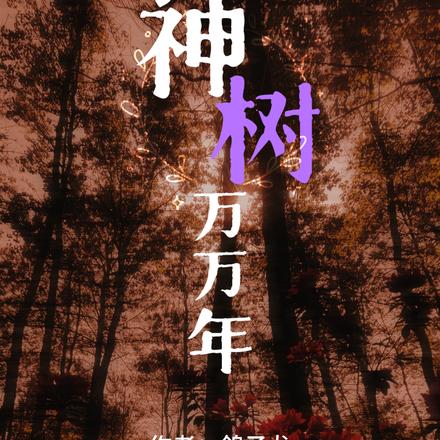二人抬了酒桶回去,日已过午,均觉饥肠辘辘。老人心情甚好,解了细索,来到钓鱼台上捉鱼。江离有心要让老人熟悉捉鱼的技巧,便不去帮忙,只生了炉子,坐在炉边出神。
风吹芦苇,呼啦啦响。江离盘算着时日,只觉过得飞快。几年前,塞北蝗祸,盗贼丛生,他那时已有几分功夫,帮着村民锄强扶弱,如今已历数载,功夫自然是越来越好了,但却总觉得自已孤零零的,也没什么亲人。
他长于塞北,但收养他的一家人,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只告诉他曾有一枚泛青的血色晶石挂在脖子上,后来辗转弄丢了,也许是变卖了,毕竟灾荒和瘟疫频仍的年月,活着已很不易。后来家人离散,他就流落边陲,跟着猎户上山打猎。再后来,便认识了师娘。师娘虽不苟言笑,却数次帮他料理了麻烦,还给他找了教书先生,又亲自教了他吐纳术。这种感激之情,是埋藏在心底的,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格外温暖。但刚刚在院子里听到的消息,却让他不由得神经绷紧。他从不怀疑师娘的本事,可是人心鬼蜮,他也领教过。龙虎寨人多势众,更兼工于心计的缥缈神龙,师娘假如真的去了,难保不会遭到埋伏。
他下定决心,只在今晚,便要下山。
做了决定之后,顿觉心中一宽,朝老人望去。只见老人挥动着细索,不断大喊着,偶尔还咒骂两句,江离知道定是捉鱼落了空,倒也不急。午后阳光正盛,透过水面,直射到塘底,整个水塘空灵清澈,宛若世外仙境,江离望着一起一伏的芦花,觉得融融的暖意。
过了一会儿,老人突然哈哈大笑,朝江离投来得意的一瞥。江离走过去,只见老人手中抓了一条肥鱼,正神气地跟鱼吹胡子瞪眼。江离嘴角含笑,帮着将鱼剖了,放在铁盘上,又拿了瓷碗,到石柱旁的铁桶里舀了一大碗酒,递给老人。老人迫不及待接过去连喝几口,眼睛眯起,仰望着碧蓝色的天空。
江离默不作声,耐心地用匕首翻着铁盘上的鱼片。老人回过神,盯着他看了一阵,叹了口气道:“要去龙虎寨,最好今夜就下山。”
江离愣住。老人又淡淡道:“老夫知道你在想什么,只是如今老夫已是残废之身,帮不上你。那龙虎寨虽然跋扈,但也讲江湖规矩,你与他们并无仇怨,又有一身以假乱真的玄天门内功,去寨里暗中查访一番,就算被发现了,也有转圜余地。”
江离点头道:“晚辈打算今晚就去探寨。”
老人摇摇头:“那倒不必。龙虎寨既然有事发生,这几天的守备必然很严,你贸然探寨,容易坏事。他们不是说了嘛,过几天要招待客人,现今大雪封山,人手必然不足,老夫估摸着,这一两日便会下山去招些伙夫。你娃娃只需赶在他们前面到歇马岭,那儿有个小村子,是去龙虎寨的必经之路,你在那儿扮作伙夫,定能入寨。”
江离点头称是。老人喝了酒,接着道:“龙虎寨的底细你也要知道一些。这龙虎寨原本叫“威虎寨”,是侯四爷当家,手下一干人等都遵“虎”字辈,后来又来了那姓杨的,也招揽了一帮人,遵“龙”字辈,这才有了龙虎之说,寨中着实聚了不少江湖人物,这几年声势也越来越大了,但老夫偶尔偷听一些闲言碎语,知道这帮人嘴上好勇斗狠,其实功夫都不过尔尔,唯有一人,你要多加小心。”
“谁?”江离奇道。
“褚天雄。”
“追魂门的褚天雄?”江离有些吃惊。
“你娃娃知道他?嗯,看来他确实是有两下子。老夫也只是听说,未曾亲见。据说这人虽不经常待在龙虎寨,却是一个高手。”
江离便将来时在路上偷听到的那两个师兄弟的话说了,又把自已听到的江湖传言也约略讲了,老人听罢眉头皱起,道:“听你这么说,追魂门这些年内斗不休,已经衰微到这般田地,委实可惜……”
江离道:“追魂门是闻名江湖的大派,虽然衰微,但影响力仍在。这褚天雄因为门主之争远走,竟然藏身在龙虎寨中,却不知是何缘故?”
老人想了一会儿,道:“多半是躲在这里修炼武功,希望有朝一日找回场子。唉,这些个不争气的东西,也难怪追魂门会遭难。”
江离听老人言语之间颇有微词,问道:“难道前辈和追魂门有什么渊源?”
老人道:“渊源谈不上。只是他们的前任长老杜泽,乃一代豪杰,和老夫曾有结义之情。如今老友虽已不在,但追魂门沦落至此,岂不伤感。”
江离没听过杜泽之名,此时也不及去问这些,道:“传言中的追魂门两大绝技,前辈怎么看?”
老人道:“名门技艺,自然是非同小可。那追魂钉,纯以内劲激发而出,打出时宛如细钉,只要钻入身体,便能麻痹穴道,算得上是独门暗器。”
江离道:“那不是和银针一样?”
老人嘿了一声,道:“大有不同。银针毕竟是有形之物,总能防范。可追魂钉练到纯熟之后,辅以高深内功,能化有形为无形,察无痕迹,极难防备。你见过无形暗器么?”
江离摇摇头。
老人突然提手至胸,四指并拢,微微向前挥出,江离顺着老人手势往前看去,只见水面一丛芦苇中的一杆突然折断,跌落在水面上。江离睁大了双眼,几乎不敢相信。老人淡淡道:“老夫曾得人点拨,对这追魂钉略知一二,但是真正练得到家的,劲力发出时如一缕细线,贯穿力极强,攻击距离也远,非老夫能比。”
江离不禁叹服。老人道:“仅此一门功夫,追魂门便足以称雄江湖了,但这还不是追魂门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难道是流云袖?”江离问道。
老人点点头,道:“江湖以为追魂钉是追魂门最强绝学,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见过流云袖。流云袖的功夫,追魂门内也只有门主才能完全修习,非门主不可擅学,只能由门主酌情教授,而且不能尽数授之。”
江离道:“这想必是为了门主的权威。”
老人道:“那是自然,但也不是全部原因。其实放眼天下,凡传承悠久的门派,都是有显隐之学的。行走江湖多凭显学,出手之际力求克敌,往往招数大开,倘若遇到武学高手,将一招一式记了去,反复推敲,便可能被破掉。所以一个门派要基业长青,还须依靠隐学,身怀利器,不示于人,才能形成威慑。流云袖便是追魂门的隐学。因此这路神功,老夫也只在机缘巧合之下见过一次。嘿嘿,你是不知道老夫见此神功的感受,用“失魂落魄”来形容也毫不为过。那江湖上说什么老夫踏雪飞霜,他们哪里知道老夫这点道行,在流云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江离笑道:“前辈只怕是过于自谦了吧。”
老人缓缓摇头,正色道:“老夫向来有一说一。武学的较量,岂能有半分不实之言?你娃娃莫要以为老夫在假模假样,故作神秘。”
江离脸上一红,不禁吐了吐舌头。
老人见鱼已熟,道:“不说这些了,反正听你所说,那褚天雄只会追魂钉,并不会流云袖,就算难以对付,多增些小心也就是了。趁着天色还早,你一会儿再练练薛家枪,万一与人动起手来,不至于仓促应战。”
江离应了一声,胡乱吃了几口鱼片,便提着枪走到空地上,一板一眼地练习。老人酒瘾甚急,又连喝了几口,已是飘飘欲仙,口中吟道:“寄情于山水之间兮,不闻谣诼;探微于索隐之际兮,唯吾寸心。”就势往后一躺,昏昏入睡。
江离直练到夕阳落下山,才终于将薛家枪每一式的细微之处领会明白,舞起长枪时,招式也越发干净了,心中暗暗高兴。忽然耳旁轻微声动,江离持枪荡开,见老人已来到近旁,正以离魂引向自已喂招,当即精神抖擞,和老人斗在一起。只见细索倏来倏走,围着自已不断包抄,只要有任何空隙,立时便朝要害攻来,江离用枪守住近身,不断变换招式,试图打破细索的围困,可是每当尝试以铁枪强力突破,细索立时横住,自索上传来一股惊人的钝力,长枪无论如何也递不上去,江离撑得片刻,始终无法突破,呼吸逐渐紧促,枪法也开始凌乱。老人见状便收了手,道:“休息一会儿再来。”
江离默不作声回到炉边坐下,凝神细思,老人也不来打搅。过了一会儿,江离一跃而起,道:“请前辈再赐教。”老人信手发招,二人又斗做一团,这次老人虽然仍能困住江离,但江离已能在间隙之间攻出几招。如此斗了几个回合,江离继续休息,苦思应对招式,而后每次较量,便都能出一些新打法,迫得老人不断缩短攻击范围。老人心中甚喜,哈哈笑道:“孺子可教,让你再来几次,老夫却要困不住你了。”说罢,收了离魂引,回到钓鱼台上。
江离深深鞠了一躬,道:“多谢前辈,晚辈受益良多。”老人摆摆手,道:“说什么谢不谢的,你娃娃在一夕之间冲破老夫的离魂阵法,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这离魂阵,取“余意不尽”之意象,乃是令人知难而退,三思后行,你以后遇事,也要牢记这一点,不要逞强,更不要意气用事。”
江离用力地点点头。老人不再多说,带江离去凌虚渡。夜已尽黑,二人很快来到大石上,对岸漆黑一片,老人问道:“记得你娃娃说是路过这里,那么你本来是要去哪儿?”
江离不答,自怀中取出一个小木盒,递给老人。老人接过打开,只见里面是一封书信,便还给江离,道:“你是去送信?”
江离点头道:“两个月内,要将信送到西余的忠义祠。”
老人沉默了一阵,又道:“送完信呢?”
江离道:“送到之后,如果不耽搁,当然还回来,到时候只怕前辈这儿芦苇都发芽了,一大桶秋露也喝干了。”
老人嘿嘿一笑,道:“一来一回,少说个把月,莫说一桶,两桶也早喝干了。”
江离道:“那咱们现在趁着没人,把另一桶也取来。”
老人摇摇头,道:“不必啦,咱们占了人家的便宜,总要给人留一些,一桶秋露,余愿足矣。”停了一会儿,又道:“你娃娃此去龙虎寨,事事千万小心,别把个小命丢了。”
江离咧开嘴笑了,道:“至多三五天,晚辈查探明白后,再来与前辈把盏。前辈到时候若是想下山,晚辈这双腿脚,但凭前辈使唤。”
老人微微一笑,问道:“你可曾瞧见我那小屋的名字?”
江离道:“看到了,起名叫”寸心居“。”
老人道:“不错。可是在几年前,它另有一个名字,叫“困心居”。老夫当年避世独居,情由无奈,因此心中愤愤不平,总盼着将来有朝一日,重入江湖。所谓困心,不过是“蛟龙自困,或跃在渊”。如此十数年,老夫日思夜想,终于不负苦心,悟出了许多武学的道理,只须趁着身体还未全坏,再杀入江湖,便能再搅出一番天地。可是人心潜替,真到了要下山的时候,老夫却恍然发觉,原来旧日的那些恩怨,早就随时日淡化了,费力去寻当年那些人一较高下,也变得没了滋味。老夫心灰意冷,以为自已年迈衰微,连志气也磨灭了。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因为心中没了挂碍,原本日渐僵硬的身体,反倒因此得了好处,上肢的麻痹感日渐消褪,老夫这才真的开悟,便将“困”改为“寸”,直到今天,也还是这般。因此,这下山之念,再也休提。”
江离还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老人更不多言,轻轻挥起铁索,凌空悬在铁链上,再一挥,卷了江离到对岸,然后倒立走回,跳上大石,头也不回地去了。江离远远望着老人慢慢消失在山野,只觉喉头哽咽,眼角发涩,悄立良久,这才转身绕到龙虎寨后院,沿着山路悄悄往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