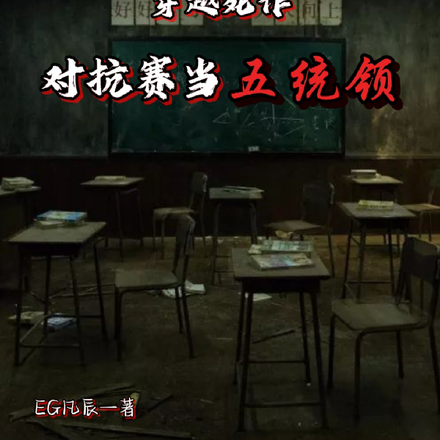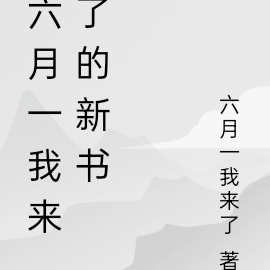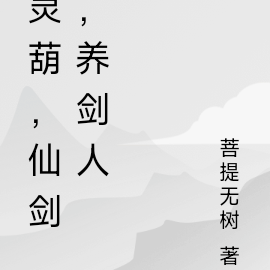第71章 病危
事情尘埃落定,年关将近,春凤宫里,一身素服的北唐皇后眼角含泪,躲在屋里,逾矩的往此处偷偷摆上的火盆里扔着纸钱,悄悄地寄给那阴阳两隔的亲人。
不再稚嫩的宋元安,带着明兰陪在她身侧默默无言。许是烟有些呛人,惹的平时很能忍咳的她时而咳嗽两声。
望着熊熊火光,她仍是想不通,为何人一站到高处便会想要敛财?明明什么都有啊,明明什么都不缺啊,明明可以本本分分,可为何?
为什么?
人之欲望如高山流水,可已经有了的东西,值得这么多人拖家带口,铤而走险吗?
……
大殿外,宋怀玉站在门口,他最近没敢来春凤宫,今夜鼓足勇气想来瞧瞧她,只是今夜已到了子时,往常这般时候她已睡下,今日春风竟不在内殿守候,他忍不住问:“……她,没睡吗?”
“娘娘在祭拜……。”
“哦……那……你多看着些,切莫让她着凉了。”
……
北唐家一倒,立马有些不知死活的朝臣揣测圣意,可北唐皇后仍是那个皇上疼宠的皇后娘娘,只是身体越来越差,许多事慢慢交由许贵妃打理。
似水流年间,一心只想在余下日子里多陪她些的宋怀玉反倒不敢多去见她了。
勤于政务却时常忙里要偷闲,总爱去瞧上她两眼,一日不见如隔半载的皇帝陛下如今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现在只敢偶尔去瞧她。
景顺六年初秋,浩瀚星河下的皇宫,正和殿里,排排烛火照的殿中如昼,小宝在一个小角落沉默不语,习以为常听越活越像孤家寡人的晋王殿下,那似醉非醉的心里话。
小榻上的宋怀玉背对着烛火,于昏暗角落拿着酒壶,时而自饮自醉地灌上两口,时而又低着头自言自语,双眼含泪,小声呜咽:“她病得越来越重了,她那么伤心,可我却不敢陪着她,我想守着她,可是我们却离得越来越远了,我把明月和明乐都送走了,她都不怪我,那年她亲自来找我,求我处置北唐家,她又该多痛?”
他敬爱她,便是喜她的通情达理,温柔体贴,可他也明白,通情达理的接受和退让,不代表视若无睹。
那些是小星星重要的人,她怎么可能视若无睹?
一个人即使再怎么沉稳,总有些软肋,有在意的东西或人,小星星的脾性和身份,从小被耳提面命的教养,注定了她遇此事会选择大义灭亲。
可风轻云淡大义灭亲的北唐皇后,不管怎么大义灭亲,仍是北唐家的女儿。
是冷眼旁观,甚至亲自跪求皇上莫念旧情,将她娘家族人以正国法的忘恩负义之辈。
是只要她苦苦哀求身侧帝王,甚至不反对,便可保北唐家不被罚那么重,以至于上一任已故鸿胪寺少卿的夫人抑郁而终,死在今年春季的不孝女。
想着被自己设计拽到身边来疼宠敬爱的妻子自剜血肉,宋怀玉便会愧疚到无以复加。
他曾借春风之口问过她要不要去见见马上要离开云阳的亲人们,她没有去,她同春风讲:“各自安好便好,他已经够宽厚了,你替我传个话,宫里的族人我会安排好,让他们安守本分,切莫心生怨念,有道是,无法国不得治。”
回想春风同自己说的话,他又觉心口堵的难受,不知是不是被酒呛的,此刻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旁边的小宝往这边看了一眼,又扭过头去。
这样酒醉的夜晚,陛下已不知一人度过了多少,北唐家的事发生以后,陛下同皇后娘娘便再回不到从前。
陛下在皇后娘娘面前成了哑巴,每次去皇后娘娘宫里都不自觉矮了一头,只简单看两眼,话也不常说。
太子对陛下越来越冷淡,幸好小公主和小皇子对陛下仍旧热情,每次陛下去皇后娘娘宫里,她们都嚷着吵着要父皇抱,四公主和皇后娘娘也总是在陛下身旁温眸柔神地看着他,这对陛下来说,便是胜过千言万语的最大安慰。
“陛下?”
安静的夜晚,殿外响起不合时宜的声音,春风不经通报便脚步匆匆推门走了进来,醉醺醺的九五至尊抬手蹭了蹭脸,迷迷糊糊问:“怎么了?”
往常春凤宫偶尔也会有宫女来报,说小公主小皇子又生病之类的话,今日春风亲自来,宋怀玉有种不好的预感。
“陛下,娘娘想见你,她……她怕是不成了。”
泪流满面的春风跪在地上,声音哽咽,忽而身旁拂过一阵风,让她遍体生寒,她惊讶抬头看向风的方向,而后扭头看向自己来时的殿外。
只见那平时有妃嫔以身体抱恙为由请他去宫里坐坐时,总会习惯地赏赐一堆东西,顺口叫个太医去看看的九五至尊抢了一名宫女手中的灯笼狂奔远去,已然快要没了踪影。
夜空之下,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宋怀玉跑地泪流满面,身后以小宝为首的一众太监气喘吁吁,跟着那个同时间追逐的威威九五,跟着那个即将失去妻子的怀玉哥哥。
嫌龙辇太慢而一口气跑到春凤宫的宋怀玉满脸是汗停在她的寝殿前差点断了气,脱力地扔了手上灯笼,双手撑着大腿,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随手扔掉的灯笼倒在地上慢慢燃烧起来,她一边喘息一边往屋檐下的台阶上走,恰好撞上眼眶微红的宋元安此时推门而出:“儿臣参见父皇。”
“母后在里头等您,儿臣先告退了。”
“父皇您保重。”过了今年便满十岁的宋明兰叮嘱了一句,便跟着太子哥哥离去。
宋怀玉平复气息踏入寝殿后入里屋,就见床上那人一如往常般朝自己静静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