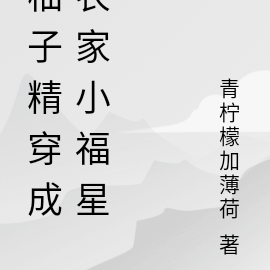邑城之战结束,楚幽辞暂时没有回都城的打算,近日,她拜访了几位富商和有名望的贤者,试图通过他们,改善民生,然而成效不佳,她自然知晓其中的意思。
那日她被客气地请出了伍家,不到半个时辰,她便收到那位叔母死亡的消息,算是把伍氏的旁支全得罪了,盈香见郡主闷闷不乐,便为其出谋划策。
“郡主可是忧心城中百姓民生?”
临香闻言插嘴道:“郡主,奴婢存了一些银钱,自小跟在您身边,银钱无处花用,虽然不多,也想帮一帮这些可怜人。”
小姑娘被两双眼睛瞧着,脸红得跟桃似的,恨不得把脸缩进脖子里,楚幽辞轻笑道:“临香都有这般觉悟,我这个做郡主的,自不能落后,盈香,备一份厚礼,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
虽说,与伍家算是交恶,但以郡主之尊,想要进门还是无人敢拦,她在正厅已喝了三盏茶,族长才姗姗来迟,可见对她的不满之甚。
“郡主驾临鄙府,老夫本该亲自相迎,奈何俗世缠身,望郡主恕罪。”说完便要拜倒在地,她是来求人的,哪敢真让他拜下去,忙亲自去扶。
“叔祖何必如此,岂不折煞晚辈,今日我的来意,想必叔祖心中知晓,不知叔祖可愿从中牵线?”
族长老神在在地回道:“郡主才是折煞老夫,您堂堂三品郡主,享朝廷供奉,您若下令,谁敢不从,怎需老夫牵线搭桥,说白了,伍氏不过是一介草民,哪有那么大的威慑力?”
见族长并未假作不知,便知其中尚有转圜余地,她暗暗掐自己一把,使劲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哭腔道:“前几日的惨事,却是由幽辞引起,我自不会推脱,我虽有郡主之名,却当真是一介孤女,那侍卫青衣,乃是皇上所赐,即便我想让他来赔罪,却是不能的,叔祖,当真明白我的难处否?”
或许真诚才是必杀技,族长长叹一声,说道:“郡主的难处,老夫怎能不知,郡主所做之事,乃是利民大计,老夫能尽绵薄之力,自是当仁不让,可,前事总要有个结果,才好与族中交代。”
“幽辞明白了,叔祖,现下最要紧的便是恢复民生,此事一了,请族长开宗祠,我便去先祖面前赔罪!”
族长见她没有玩笑之意,心下大惊,连忙摆手道:“不可不可,伍家蝼蚁,岂敢如此辱没皇室中人。”
楚幽辞不容反驳地说道:“蝼蚁尚且偷生,我既不能抵命,赔罪自是应当。叔祖不必再劝,此事就这样定了,告辞。”
族长见她离去的背影,说了声可惜了,继而唤出隐藏在后堂的其他人,众人皆是沉默相对,不知究竟在想什么。
待出得府来,盈香才问道:“郡主当真要开宗祠赔罪?这可不是小事,会坏了郡主名声,若传回都城,恐婚事生变。”
“在外人面前,青衣代表的就是本郡主,眼下所求之事已成,本郡主伏低做小很是值得,至于婚事嘛,沈家主母本就不喜我,不在乎多这一件两件的。”
盈香暗叹郡主命苦,心中还在庆幸没有带临香过来,以她的性子,恐怕早就不分场合的闹起来,平白地开罪于人。
有伍氏族长帮忙,邑城的事情算是解决了,但身边还有个不定时炸弹,想到青衣,楚幽辞颇为头疼,真是轻不得重不得,但放任不管吧,又不知他会搞出什么事来。
“那个妇人算是本郡主的远房叔母,她死了,你可知晓?”
青衣站得笔直,即使提到被他杀死的人,依旧面不改色,楚幽辞心中早有疑虑,直到此行,她才肯定了心中的猜测,青衣这样的人,一心为主,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很难逼迫他说出有用的消息。
“你当真是护主心切吗?”
他跪地行礼,平静地说道:“属下该死,请郡主责罚!”
果然没错,就是不知,他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伍家,还是她楚幽辞,他仅用一招便离间了她与伍氏族人的关系,若想要她的命,机会实在太多了,月河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那么他背后之人,究竟想要做什么呢,她百思不得其解。
楚幽辞在邑城风风火火地筹集银钱,却不知都城中已经流言满天飞了,她定亲的沈家,此时也正为这事闹心呢。
“公爹,婆母,现下满都城都是荣安郡主的流言,不知是哪个丧良心的,印了许多书稿,免费发放,这几日说书唱戏的,全是荣安郡主的光荣事迹,咱家是体面人家,可不敢要这样的媳妇啊,请公婆为我儿做主啊!”妇人三十多岁,一瞧便知是富贵夫人,此刻她完全不顾仪态地跪服在地,话说完便嘤嘤哭泣,可见真是到了伤心处。
堂上被称为公婆的年老夫妻,皆是眉头紧皱,左右为难,妇人身侧站着的中年男子见状,呵斥道:“阔儿的婚事,自有我这个当爹的做主,一介妇人懂什么,快快退下,莫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两位老人暗骂儿子愚蠢,果不其然,原本低不可闻的哭闹之声,一下子变得尖利刺耳。
“我怎么就胡搅蛮缠了,当初定亲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一个商家女,也配我沈家门楣?现下好了,咱们都成了栎阳城的笑话了。”
沈父怒道:“你这无知蠢妇,荣安虽是商家女,那也是先帝亲封的郡主,如今圣眷正浓,岂是你那没名没姓的侄女能比的?”
“好了,多大的人了,这般失了仪态,当心让小辈看了笑话。”沈家祖母打圆场道。
沈母心知堂上两人此刻仍在权衡利弊,今日若不婚事搅黄,恐怕再没有如此好的机会,许是被她嘲讽的笑容刺到,沈家祖父母皆是恼羞成怒,直言再不管了,便含怒而去,那背影总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
沈母此时完全没了顾虑,言道:“圣眷正浓有何用?哪里有晚儿贴心乖巧,她不过去了一趟云州,便被西楚兵俘虏,那可是一群男人,她失了清白,你还想让你儿子娶一个破鞋吗?”
“你你”沈父指着她的手都颤抖了,强自镇定道:“往常当你只是泼辣了些,如今竟学得这般市井妇人做派,当真有辱斯文!”
沈母依旧不依不饶,“市井做派又如何,若能为我儿推掉这不清白的婚事,死了我也是愿意的。”
沈阔听闻父母争吵,匆匆赶来前厅,听见的便是母亲这般言论,哎,母亲本就不喜幽辞,如今这满城风言风语,她应是被刺激狠了。
沈阔进得门来,便跪在母亲跟前,深深下拜,说道:“母亲,这门婚事乃是先帝允许,与赐婚无异,荣安郡主最是守礼,她为救百姓被俘,此乃大义。”
他看向母亲,目光坚决,“儿子信她,儿子断然不会退亲的!”
沈母满目绝望,口不择言道:“先帝怎会如此昏聩,竟赐我儿这般水性杨花的女子,沈家污名怕是洗不清了!”
“住口,你这个蠢妇,竟敢污蔑圣驾,我要休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