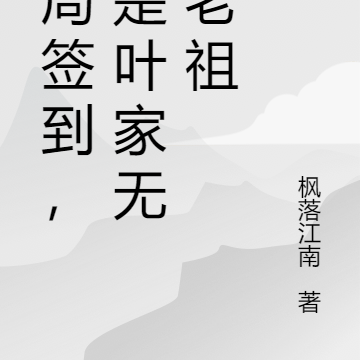第1章 先天剑体,被村长捡回家
天黑,别出门。
大墟的夜,浓重得能吞噬一切光线。
黑暗中有巨兽嘶吼,远山轮廓扭曲如魔怪獠牙,枯枝在风中发出骨骼断裂般的脆响。
一个身影却在这时踉跄奔逃,踩碎满地白骨,喘息粗重如破风箱。
那是个浑身染血的男子,怀中紧抱着什么。
他左臂不自然下垂,显然已经折断,腹部伤口深可见骨,每步踏出都在枯黄的地面上留下深红印记。
“不能再倒了…绝不可……”
他嘶哑低语,齿间溢血,视线已开始模糊。
身后黑暗中,某种庞大之物正碾过山林,树木噼啪倒塌,越来越近。
男子猛地扑倒在地,却用最后力气将怀中之物高高托起——那是个以残破布帛裹紧的婴儿,出乎意料地未曾哭闹,只睁着一双清亮的眼睛。
布帛缝隙间,隐约可见婴儿心口皮肤下,有一点极细微的金芒随着心跳明灭,似有无形剑意在周身流转,将迫近的黑暗与寒气悄然斩开寸许。
“活下去…”
男子将婴儿推向一处岩缝,自己却转身,撕下染血衣襟,以指为笔,以血为墨,在荒地上急速勾画着什么,每一划落下都引动四周空气锐利震颤,“来吧,畜生!”
惊天动地的咆哮吞没了他的怒吼。
……
天光微熹时,几道怪异的身影出现在这片狼藉的战场。
一个高大的身影被推在最前面,他双臂齐肩而断,空荡荡的袖管披散,但步履沉稳,目光如电,扫过地面那些已黯淡的血色符文时,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好烈的剑意。人已经没了,残留的意念却不散,斩了这周遭的邪祟。”他微微蹙眉,“是何方人物,落得如此下场?”
“村长,这边!”
一个软糯的女子声音响起,却发自一个体态丰满、面容姣好,偏偏挎着个针线篮子的……老太婆?她翘着兰花指,指向岩缝,“哎哟,有个娃儿!”
岩缝中,婴儿依旧安静,那双眼睛清澈地望着外来者们,心口的金芒已隐去。
被称作村长的老人走近,俯身打量。
当他目光触及婴儿时,婴儿忽然伸出小手,抓住了他空荡荡的袖管。
“咦?”
村长剑气长臂伸出,指尖轻触婴儿眉心。
一瞬间,他仿佛感到一丝极细微、却无比锋锐的气息刺了一下他的指尖。
村长猛地缩回剑气,眼中爆出难以置信的精光。
他再次凝视婴儿,这次看得更加仔细,甚至动用了某种秘术,瞳孔深处有符文流转。
婴儿周身经脉在他“眼”中无所遁形,只见一缕先天之气纯白炽盛,自丹田起,循脉而上,直贯天灵,其形…其形竟如一柄宁折不弯的微型道剑!
剑气内蕴,引而不发,却将周遭天地间散逸的稀薄元气自动斩碎、吸纳,化为最本源的精华滋养己身。
“这是……?”
村长深吸一口凉气,断臂处竟隐隐感到一丝久违的刺痛,“先天剑体!传说中的道胎剑骨,万古难觅的剑道种子!”
“先天剑体?”挎着篮子的老太婆凑了过来,好奇地戳了戳婴儿的脸蛋,“比牧儿那娃的霸体如何?”
“霸体主肉身无敌,一拳破万法。剑体主杀伐攻掠,一剑破万般神通!”
村长语气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路数不同,皆是天地极致的体质!没想到,短短时日,我残老村竟能得遇两大旷世奇才!”
司婆婆小心翼翼的抱起婴儿,发现孩子不哭不闹,反而用那双清亮的眼睛与她对视。
“小娃娃,你可知为你舍命的那人是谁?”
村长苏幕遮喃喃,目光再次扫过地上那些即将被风沙彻底抹去的血符,“没想到,这剑意…浩大苍茫,曾照耀过一个时代啊…莫非是……”
他摇了摇头,压下心中惊涛,对另外几人道:“司婆婆,药师,先把孩子带回去。此地不宜久留。”
……
残老村深藏于大墟一隅,被简陋的篱笆围着,几间歪歪扭扭的泥瓦房,村口一株老槐树半边焦黑,似是雷劈所致。
村子很残破,村里的人更“残”。
除了四肢尽断的村长,挎篮子佝偻的司婆婆,还有瘸腿的盗圣,瞎子枪神,聋子天图太子,哑巴公输天,马爷如来,药师毒尊,屠夫天刀……
几乎人人身有残疾,却个个气息沉凝,不似寻常乡民。
村长剑气抱着婴儿回来时,一个穿着开裆裤、拖着鼻涕的小娃娃正吭哧吭哧地试图举起比他还高的石锁,小脸憋得通红。
正是比李长青早几年被捡回来的秦牧。
“爷爷!婆婆!你们回来啦!”小秦牧看到众人,立刻丢了石锁,摇摇晃晃跑过来,好奇地看着村长怀里的婴儿,“呀!小娃娃!”
“嗯,以后他就是你弟弟了。”
村长将婴儿小心放入秦牧迫不及待张开的、勉强抱拢的小胳膊里,看了看玉牌篆刻的名字,道:“他叫李长青。”
“长青…弟弟!”秦牧欢天喜地,笨拙地抱着,差点一起摔倒,幸亏旁边的司婆婆兰花指一翘,一股柔力托住。
李长青看着眼前这个鼻涕娃,似乎觉得有些新奇。
从这一天起,残老村多了个婴儿,李长青。
而村外大墟的黑暗中,那曾惊天动地的血战痕迹,正被新的风沙与黑暗逐渐掩埋,仿佛从未发生。
只有村长苏幕遮偶尔望向村外深沉夜色时,眼底会掠过一丝凝重与疑虑。
那个以血画符、剑意惊世的男子,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位?
他为何携先天剑体婴儿逃入大墟?又在躲避什么?
这些谜团,如同大墟永不散尽的夜雾,笼罩在残老村上空。
……
时光荏苒,春去秋来。
残老村后的空地上,两个小小的身影正扭打在一起…或者说,是一个正试图把另一个牢牢锁住。
“嘿!长青看招!霸体三式之抱摔!”秦牧嗷嗷叫着,一个猛扑,抱住李长青的腰就想把他撂倒。
如今的秦牧已是六七岁的孩童模样,虎头虎脑,力气大得惊人,身体结实得像是小牛犊子。
被他抱住的李长青,同样年纪,身形却显得颀长一些,眉目清秀,眼神清澈中带着一股天生的锐利。
就在秦牧发力的瞬间,李长青脚步一错,身体仿佛没有重量般顺势旋转,指尖不知何时夹了一片薄薄的草叶,轻轻点在了秦牧的腋下。
“哎哟!”秦牧顿觉半身酸麻,力气一泄,噗通一声自己摔了个屁股墩儿。
“牧哥,你力气又大了。”李长青拉起他,笑了笑,指尖的草叶完好无损,“就是招式太直了。”
“直点不好吗?村长说一力降十会!嘿嘿!”
秦牧揉着屁股爬起来,不服气道,“你那是取巧!还有,你用什么戳我?又用草叶子?不公平!”
李长青摊开手,那片草叶在他掌心静静躺着,叶尖却隐隐透着一丝极微弱的锋锐之气。
“我没有。”李长青眼神无辜,“是牧哥你自己没站稳。”
“你就有!”秦牧哇哇大叫,“上次你用树枝,上上次你用鸡骨头!这次用草叶子!你总能用乱七八糟的东西戳到我痒痒肉!婆婆还说你是剑体,天生就会用剑!欺负人!”
“好了好了,两个小皮猴,别打了,过来吃饭!”司婆婆扭着腰走来,声音软糯,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专职保姆”。
饭桌上,秦牧风卷残云,抱着比脸还大的海碗呼呼大吃,浑身冒着热气。
李长青则吃得慢条斯理,但进食速度丝毫不慢。
他拿着筷子的手极其稳定,每一次夹取都精准无比,偶尔有米粒或菜叶不小心掉落,总会被他看似随意地用筷子尖一拨、一挑,稳稳当当地送回碗里,动作流畅自然,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感。
坐在上首的村长看着两人,目光尤其在李长青的手上停留片刻。
饭后,村长将李长青单独叫到村后的槐树下。
“长青,你来村子,有三年了吧。”村长看着眼前的孩子。
“嗯。”李长青点头。
“你知道你与别人不同吗?”
李长青想了想,抬起自己的手看了看:“我知道。牧哥练力气,我能…感觉到别的东西。”他指了指地上爬过的蚂蚁,“比如它,左边第二条腿好像伤了,爬的时候,力气走到那里会断一下。”
又指了指飘落的树叶:“它要往左边飘,因为风有一缕是从右边缝隙里钻过来的,比别处的风更急一点点。”
最后,他看向村长空荡荡的袖管:“还有村长爷爷,有时候那里…会疼,像有很多小针在扎,尤其是阴天的时候。是断掉的地方还在疼吗?”
村长心中巨震,脸上却不动声色。
先天剑体,灵觉竟敏锐至斯!不仅能感知万物气机流转,甚至能窥破虚妄,直指本质!这已非单纯天赋,近乎一种本能的神通了!
他沉默片刻,缓缓道:“从明日起,你随我练功。”
李长青眼睛亮了一下:“和牧哥一样举石锁、站桩吗?”
“不。”村长摇头,独臂抬起,指向不远处一株半枯的老树,“去看那棵树。”
李长青依言看去。那老树盘根错节,一半枝桠焕发生机,绿叶葱葱,另一半却干枯皲裂,毫无声息。
“看什么?”李长青问。
“看它的脉络。”村长的声音低沉传来,“看生机如何从根系起,循木质纹理,输送至每一片叶尖。看死气又如何盘踞枯枝,阻塞通道。看活着的纹路与死去的纹路有何不同。看阳光洒落,叶片如何承接转化。看风吹过,枝条如何顺势卸力。看雨打时,脉络如何疏导水流。”
“用你的眼睛看,用你的心去感觉。”
李长青似懂非懂,但还是凝神望去。起初并无异样,但当他心神逐渐沉浸,那双清澈的眼中,世界开始缓缓变化。
粗糙的树皮仿佛变得透明,内里无数细微的管道浮现出来,其中仿佛有莹莹绿意缓慢流动,如同大地呼吸的脉搏。
而在枯死的部分,那些管道扭曲、断裂、堵塞,灰败死寂。
他甚至能看到阳光落在叶片上,被一点点吸纳,转化为微弱的能量,顺着脉络回流。
能感到清风拂过,枝条内部有极其细微的震颤传递,将力量化解。
他看得入了神,直到夕阳西下,双眼酸涩流泪,才猛然惊醒。
“看到了?”村长问。
“看到了一点。”李长青揉着眼睛。
“看到了,然后呢?”村长又问。
李长青愣住。
村长独臂一拂,地上一段枯枝飞起,落入李长青手中。
“明天开始,用它,把你看到的‘脉络’,画出来。画在地上,画在沙上,画在水面上。什么时候你能一笔画出枯荣并存的完整脉络,不分毫差,什么时候才算入门。”
村长顿了顿,又道:“记住,不是用手画。用你身体里那口天生的‘气’去引着画。”
李长青握着枯枝,若有所思。他感到体内的那缕先天剑气,似乎微微跳动了一下。
从这天起,李长青多了一项功课。
秦牧在一边吭哧吭哧打熬气力,举石锁,站混元桩,拳打脚踢,虎虎生风。
李长青则拿着根树枝,对着老树、石头、流水甚至蚂蚁发呆,然后在地上、空中写写画画。
他的动作时而流畅,时而滞涩,有时一画就是半天一动不动,有时又连续画废几十次。
秦牧偶尔跑过来好奇地看,只见地上那些线条歪歪扭扭,乱七八糟,完全看不懂,便觉得无趣,又跑回去继续练他的“霸体三式”。
只有村长看着那些逐渐从杂乱无章变得隐约有了些许奇异规律的线条,眼中不时闪过欣慰与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