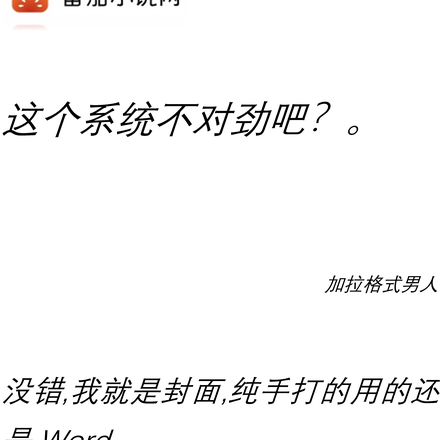福宁殿内,气氛凝重得几乎凝固。
龙案之后,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面容严峻,虽说面容憔悴,但他目光如炬,似乎能洞察人心最深处的秘密。
殿内烛火摇曳,将皇帝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更添了几分威严与孤寂。
赵和仪出身名门,端庄贤淑,宋忻更是自已寄予厚望的继承人,但权力与地位的诱惑,足以让最亲近的人反目成仇。他想。
权力的诱惑如同无形的毒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人性的底线,让他不禁开始怀疑,那些曾经以为的和谐与稳固,是否只是建立在脆弱沙土之上的海市蜃楼,而真正的暗流,却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汹涌澎湃。
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这是他思考时特有的习惯。
他回想起近段时间以来,赵和仪与宋忻之间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地会面。
这些细微的变化,如同锋利的刀片,悄无声息地切割着皇帝心中的信任之墙。
就在这时,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打破了殿内的沉寂,一名内监小心翼翼地步入殿内,声音颤抖地禀报:“皇上,张宸翰大人已到殿外候见。”
张宸翰是张玉仙伯父,进士出身,此时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百官之首。
为此,朝中不少老臣气愤不已,说陛下色令智昏,亲小人而远君子,纷纷告老还乡,不愿与其共事。
皇帝缓缓踱步至案前,手指轻轻摩挲着桌面的龙纹雕饰,声音低沉而有力:“近来朝中流言四起,皆言皇后与太子或有不轨之心,朕心甚忧。”
张宸翰闻言,身形微动,随即沉稳地跪拜行礼,语气坚定而又不失恭敬:“陛下,微臣闻此消息,亦是震惊不已。然,流言止于智者,若无确凿证据,切不可轻信。”
皇帝微微点头,表示赞同,但忧虑并未因此消散:“话虽如此,但无风不起浪。皇后与太子,一为后宫之主,一为储君,其言行举止关乎社稷安危。朕欲派人暗中查探,又恐惊动朝野,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张宸翰沉吟片刻,思虑周全后缓缓开口:“陛下所虑极是。微臣以为,陛下可加强宫中戒备,以防万一。”
皇帝颔首,道:“这几年你也知道,潞国公主之死、老七与刘县君之事弄得宫内乌烟瘴气。朕叫你来,是想叫你彻查宫廷之内的秘事。”
听到皇帝提起宋快与刘县君的事,张宸翰忙跪下请罪。
皇帝摆摆手示意他起来,道:“你是老七的舅姥爷,是张贵妃的伯伯,也是朕的伯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动不动请罪,倒像外人了。”
接着,又道:“正是因为把你们当家里人,这才安排你去办这件事。”
张宸翰忙叩谢圣恩。
春寒料峭,宋意挺直脊梁,跪在柔仪殿那冰冷彻骨的砖石地面上,双膝早已麻木,仿佛与这冰冷的石面融为一体,连疼痛都变得遥不可及。
他的目光穿越眼前的寒气,与高位上怒容满面的皇帝交汇,嘴角勾起一抹苦涩而复杂的笑:“爹爹以为,凭张大人的本事,会只查得出儿臣一人?”
龙椅上的人本病恹恹的,听了这话,不由得勃然大怒,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是铁青一片,怒不可遏地吼道:“朕不是你的爹爹!你究竟是谁的孽种,朕不想知道,也不愿去想!”
话语间,他胸膛剧烈起伏,一阵剧烈的咳嗽猛然袭来,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赵和仪忙拍着他的背安抚他,又向宋意道:“十几年来皇上待你如何你最清楚,你享天下之养,这般行为足以令天下人为你羞愤而死!”
所有人都退了下去,屋内只有他们三人。
皇帝终于缓过气来,声音虽弱却坚定:“朕已下令,将宸妃那毒妇挫骨扬灰于乱葬岗,家族受连,男丁流放边疆,女眷则贬入掖庭,永生为奴。至于潞国公主······”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与哀伤,“朕已追封她为兖国公主,愿她在天之灵······”
他声音哽咽住了,难以再把话说完。
提及宋悦,那个他曾视若珍宝的小女儿,皇帝的情绪再也无法控制,他不顾病体,猛地站起身,怒视着宋意,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她是你的亲妹妹啊!你,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畜生!来人,给朕将这个他拖出去,五马分尸,以儆效尤!”
赵和仪见状,连忙起身,动作中带着几分急切与不安,她轻轻搀扶住皇帝的臂膀,同时口中不住地劝慰着:“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
宋意望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他缓缓开口,:“皇上,还有一件事······关于……皇后娘娘。”
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向赵和仪,那眼神中既有挑衅也有几分复杂的情绪。
赵和仪知道宋意握有自已的把柄,可如今皇帝已经是半只脚踏进坟墓里的人了,自已的儿子已在朝中立稳脚跟,是以她此时倒也不慌不忙,只是冷笑道:“吾问心无愧。”
皇帝闻言,眉头紧锁,他本就对赵和仪的权势与手段有所忌惮,如今宋意的话更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
“说。”皇帝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透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与愤怒。
宋意轻轻一笑,似乎对这样的反应早有预料。他道:“皇上难道没发觉,自已的枕边人早就被偷梁换柱了吗?”
皇帝的目光刺向赵和仪。
赵和仪神色如常,端庄依旧,不徐不疾道:“妾身与陛下相伴日久,妾身是何心性,陛下心中自然明镜高悬,无需多言。”
柔仪殿内,空气仿佛凝固,宋意的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寒意,在这空旷的大殿内回响:“赵姝仪,阿姝……”
这简单的称呼,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长河,唤醒了赵和仪曾经的无尽温柔与秘密,却又在此时此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味。
姐姐,若是你在该多好。
她想。
她的姐姐赵和仪,是全京城最稳重端庄的女子。
她们虽说长得一模一样,性格却是迥然不同。姐姐最爱读书作画,她却只喜欢斗蛐蛐。
她因为小腹处长了块黑色胎记,家中最为迷信的祖母说,那是乌云压城,是谋逆祸乱的预兆。
小腹上的黑色胎记,如同命运的烙印,让她在家族的阴影下默默成长。祖母的迷信之言,如同利剑般刺痛着她的心,却也让她更加坚韧。
爹娘害怕,故而不曾将她的存在透露给外人,对外说只有姐姐一个女儿。
但爹娘很疼爱她,给她取名叫赵姝仪,小名叫阿姝。多好听的名字。
她们家世显赫,姐姐的贤良名声又广,便在十八岁那年被皇帝接到了宫中,立她为后。
后来······
她不愿再回忆,只是轻轻地拿起姐姐曾经送给自已的玉如意,抚摸着。
后来,一切似乎都变了。爹爹早逝,家道中落。
姐姐生下忻儿便病了。她心急如焚,却只能扮作小丫鬟,跟着母亲偷偷进宫探望。
看到姐姐那憔悴的面容,她的心如刀绞。姐姐却强撑着精神,将手中的玉如意递给她:“阿姝,愿这玉如意能保佑你事事如意,平安喜乐。”
她问姐姐是谁害了她。姐姐却说,她已经原谅宸妃了。
她永远都那么善良。
但她们是双生胎啊,一个离开了,另一个便要替她好好活下去。
她说服母亲,将病入膏肓的姐姐扮成自已带回家休养,自已则穿上华服,变成了赵和仪。
她威胁宫人们,若是敢说出去,脖子上的东西就别想要了。
她还处死了几个多事的。
杀人真容易啊,容易得让她害怕。
午夜梦回,她梦见姐姐一声声唤着阿姝。
姐姐······
可是宸妃那个贱人,竟然发觉了她的秘密,所以她必须死······
宋意轻浮,趁人不备凌辱公主,却以赵和仪的事要挟自已,不许自已将此事禀报皇上。
她将顾锦瑟送的宋意身边,叫她悄悄了结了宋意,谁知她是个不中用的。
姐姐,这下该怎么办啊······
赵姝仪心中一颤,但仍旧面不改色,道:“皇上,此事定有蹊跷。那小子自知罪无可赦,临死之际,不过是想拉个垫背的,以泄私愤罢了。他母亲昔日之举让妾身蒙受不白之冤,他也因此对妾身心生怨恨。只是,这怨恨不能成为他污蔑妾身的理由。他的话,字字句句皆是谎言,皇上明鉴。”
皇帝猛然间伸出手,仿佛要将所有的愤怒与不甘都凝聚在这一击之中。
赵姝仪只觉脸颊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那是皇帝愤怒之下失控的一击,却也是她入宫多年以来,首次直面皇帝的暴怒。
她心中虽惊,面上却未显丝毫慌乱,迅速跪倒在地,双手交叠于额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皇上息怒!”
可当她抬起头来,那位曾经威严不可侵犯的皇帝,此刻竟如同被抽去了所有力气般,高大的身躯颓然向后倒去,重重地砸在了那张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龙椅之上。
龙椅微微震颤,发出沉闷的声响,与周遭的静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赵姝仪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但她迅速调整了自已的情绪,强压住心中翻涌的慌乱与不安,向门外高声呼喊:“来人!快来人!”
内监宫女们忙涌了进来,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皇帝,以及脸色铁青的赵姝仪,皆是面露惊色,却也不敢多问。
赵姝仪深吸一口气,喝道:“去请太医!将陛下移至寝宫妥善安置!”
又指着跪在殿内的宋意道:“至于这个……孽子,来人,即刻将他拿下,锁入柔仪殿后殿,派重兵日夜看守,不得有任何闪失!”
臻儿小心翼翼地跨前一步,脸上交织着忧虑与急切,轻声试探道:“娘娘,太子妃已在偏殿静候多时,说是有极为重要的事务需面呈皇上,此事关乎重大,不可延误。”
“什么时候了!”赵姝仪胸脯不住地起伏,仿佛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正随着每一次呼吸而加剧。“皇上的性命要紧!速速叫人去请忻儿来,说皇上龙体违豫,请太子监国。再秘密请郑弘毅郑大人进宫!”
臻儿眉头微蹙,似乎有所疑虑,躬身道:“郑大人和张大人都是宰执之臣,娘娘不请张大人进宫么?”
赵姝仪沉吟道:“张大人是张贵妃的伯父,乃外戚一族,此时不宜入宫。”
饮溪静静地坐在偏殿的雕花梨木椅上,四周被柔和的烛光轻轻包裹,每一束光线都似乎在空气中跳跃,与她内心纷扰的思绪交织成一幅复杂的画卷。
她的目光聚焦于那摇曳不定的烛火,思绪万千,心乱如麻。
忽地柔仪殿正殿内传来一阵哭声,打破了许久的沉寂。
“云卷。”饮溪的声音微微颤抖,她努力让自已显得镇定,指尖轻轻拈起一块精致的糕点。“你去看看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突然间各宫的嫔御都聚集到了柔仪殿,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然而,云卷还未及应声,脚步甚至未及迈出门槛,一个小内监便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如纸,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乎要夺眶而出。
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道:“太子妃娘娘,不好了……皇后娘娘刚刚派奴才来通传,说是……说是皇上,皇上他……驾崩了!”
饮溪惊得忙站起身来,手中的糕点掉在地上,摔成一滩烂泥。
那股寒意仿佛是从心底最深处迸发而出,悄无声息地穿透鞋底,沿着她的脊椎骨一路攀爬,直至头皮发麻,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在这一刻凝固。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双手紧紧交握在一起,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只因心中的痛楚远胜于此。
“宋忻……”她低声呢喃,这个名字如同锋利的刀刃,每一次念及都在她心上划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他竟会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连自已的亲生父亲都能狠下心肠去谋害。
即使心中翻涌着滔天的愤怒与悲伤,眼眸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泪水似乎早已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流尽,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空洞与麻木。她咬紧牙关,脸颊因用力而微微颤抖,那是一种混合了愤怒、不甘与无助的复杂情绪。
“他不日便要登上皇位,”饮溪在心中默默盘算,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带着刺骨的寒意,“到那时,我只能是案板上的鱼肉,任他宰割。”
她深吸一口气,双手护住腹部,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但那份寒意却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