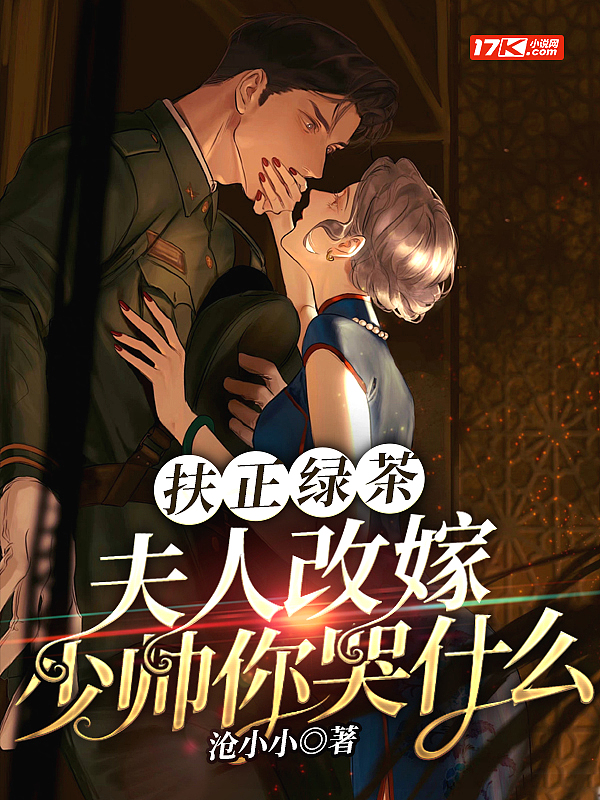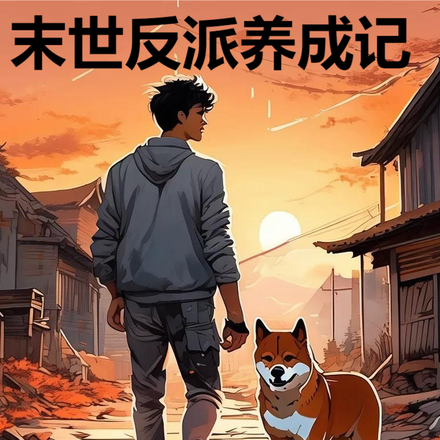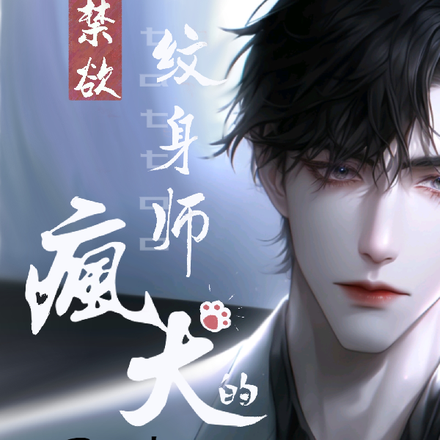王振,司礼监掌印太监,宫中太监的最高掌权者。作为宫中权力的顶峰和枢纽,他成为了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朝野上下、宫内宫外总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太监,是紫禁城中特殊的群体,因为身体上的残缺,他们或多或少有些心理扭曲。太监这一特殊职业,已经在历朝历代的深宫中存在了上千年,但是在本朝,他们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朝重用宦官,从衣食住行到朝政大权,宦官们如同一群无孔不入的苍蝇,密密麻麻地排布在朝廷的上上下下,啃噬着朝廷的血肉。然而,宦官群体内部,却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的人如同卑微的蝼蚁,有的人却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太阳。诸如王振此类,牢牢地把持着司礼监掌印、东厂提督、监军此类至关重要的位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句话就可能改变局势和发展走向。
太后听到王振的名字,毫无波澜,只是淡淡一笑,漫不经心地说:“太皇太后与皇帝争执许久,不就是因为内官吗。太皇太后素来不喜欢那些太监,可是紫禁城中和皇帝身边都离不开内官。重用内官,并非是本朝才开始的,太祖皇帝为了分割臣子手中权力,监管文武百官,重用宦官。历代皇帝,都称内官为近臣家臣。如此看来,皇帝对王振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太监之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遥想郑和当年的风姿,七下西洋,远播大明国威。要哀家说,世间万事万物都不可以妄下定论。先帝常说,宦官为了皇家作出了莫大的牺牲,因此稍微给他们些尊重和抬举,他们就会死心塌地效忠。”
说罢,她扭头对我说:“贞儿同去乾清宫送茶点吧。替哀家给皇帝带句话,哀家不反对他用王振,只要是皇帝能够明辨是非,做对大明朝好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连声应下,领命离了队伍,带着茶点往乾清宫而去。
乾清宫是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虽然壮阔威严,但自永乐年失火后,失了几分气派。年初,皇帝下令重修三大殿,连同乾清宫和坤宁宫一同修缮。眼下,修缮尚未完成,不少宫人在忙碌着,偶尔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皇帝不在乾清宫中,而是在乾清门外广场上练习射箭。
宽阔的广场上,皇帝笔直如松,双臂展开,弯弓搭箭。他将弓拉满,聚精会神地瞄准远处硕大的靶子。只听得“嗖”的一声,箭如一只敏捷的豹子窜了出去,正中箭靶的红心。“皇上中啦!”身旁的王振立刻发出一声欢呼,两只手如同一副竹板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他一溜烟地跑到那箭靶前,龇牙咧嘴地将那箭拔下来,双手捧着,一路呈到皇帝面前。王振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仿佛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极尽谄媚之态。我偷偷地捂住嘴巴,仿佛看到王振屁股后头生出一根无形的尾巴,上下摇动。“皇上不光箭法精准,还孔武有力。这箭如同钉子一般将那死死地扎在红心上,微臣费了好大的劲才拔下来。”
听了这话,皇帝开怀大笑,他将那只箭一把攥在手心,骄傲地问:“王先生,那朕与蒙古人相比如何?”王振的嘴已几乎咧到耳朵根,他的眼睛本眯成了一条缝,忽然睁大,一本正经地说:“皇上说得哪里话?微臣日日陪着皇帝骑马射箭,时常叹惋。”听闻此言,皇帝扭过头去看着他,饶有兴致地问:“叹惋什么?难道朕与蒙古人相差甚远?”王振递上一杯茶,赶忙说:“叹惋皇帝未生在那南宋。否则,仅凭皇帝一人之力,便可以力挽狂澜,哪里轮得到那些蒙古人入主中原九十年呢。”我心头一跳,默默地翻了个白眼,心中默想:真是一流的拍马屁功夫,真是一副谄媚的嘴脸。
王振的一番话,把皇帝哄得如同吃了蜜一般,皇帝像哥们儿一般拍了拍他的肩膀,将手中的箭放到他的手中,开朗地说:“朕也时常这样觉得,若朕不是皇帝,定是一名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不过,没关系,朕是皇帝也好,王先生可作朕的军师,朕同王先生一起开拓大明疆土。”王振立刻谄媚地跪下,声声高呼“万岁”。
我实在看不下去这主仆情深的画面,快走几步,将手中捧着的一壶茶高举过头顶,顺势用托盘和胳膊挡住自已的脸,恭敬地行礼。见有外人来了,王振立马从地上站了起来,蹿到皇帝身后,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正色问道:“你们是何人?”我回答道:“奴婢奉太后懿旨,特送一壶清茶和若干茶点。太后吩咐奴婢说,皇帝日理万机,特意备了今年新进贡的明前龙井,给皇帝清新润喉。太后还吩咐奴婢挑选些精致可口的茶点,都是皇上平日爱吃的。”皇帝点点头,王振从我手中接过那壶茶,差两个小内官借了茶点。
皇帝盯着那茶壶,青花瓷上勾勒出一副《三顾茅庐》景象。皇帝若有所思地问:“才从太皇太后那里出来,喝了她的陈茶。太后立刻给朕安排了一壶上好的新茶,想来是有话要对朕说。”我跪在地上,一字一句地将太后叮嘱的话悉数转达。皇帝听后哈哈一笑,一伸手,王振立刻会意,斟了一杯茶递到皇帝手中。皇帝一饮而尽,潇洒地说:“替朕转达,就说太后与朕母子情深,最是了解朕的口味。”
我办完了差事,匆匆带着两个小宫女离开。离开时,只听到背后传来皇帝和王振欢庆的声音和一句豪言壮语:来日与先生共创万古基业。我轻轻地摇了摇头,今日若非亲眼所见,我万万不敢相信皇帝与太监云泥之别,却私混到一起,如同亲兄弟一般。奈何我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宫女,紫禁城中到处都是我得罪不起的人。
眼下的局势已经分明,太皇太后与皇帝因为皇权出现隔阂,皇帝转而与王振抱团,连同宦官群体,试图逐步将太皇太后手中的权力转移到自已手中。太后本不在意朝政,但夹在二人中间,左右为难,眼见太皇太后身体欠佳,转而支持皇帝,以成全母子之情。太后为了表明自已的态度,每隔三五日请皇帝来到坤宁宫中叙话,对王振也是不闻不问。果然,皇帝常来往坤宁宫,与太后的母子情分亲近了许多。
眼下,太后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后之位的宝座。这日午后,她拿着一本名册,细细地查看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家中适龄女子的信息,拿着一只紫毫笔在上面勾勾画画。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凑到她面前,轻声说:“太后,钦天监正使到了。”太后眼前一亮,赶忙将正使请进来。
钦天监主要负责观测天象、历法编纂和宗教祭祀等事务,提供各种天象信息和预测。他们日日观测天象,根据天象信息预测未来之事。眼下,太后最感兴趣的只有凤星的事情。
凤星,意味着女性贵人或皇后出现的征兆。钦天监往往根据凤星出现的方位,推测未来皇后的所在地。然而,凤星并非选为皇后的唯一依据。当年,凤星闪耀,太后与静慈法师二人一起合凤星定位,太后却未能如愿以偿。
钦天监正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恭敬地行礼。太后未抬头,一双眼睛仍是盯在那本名册上,问道:“凤星如何了?”听了这话,正使叩头不起,吞吞吐吐地回答:“启禀太后,凤星飘忽不定……臣一时仍是不好定夺。”
“哦?”太后从名册中脱离,轻轻挑了挑眉头,眼睛中射出一道寒光,颇有威胁地说:“你的言外之意,皇后之位尚不能定,此时并非皇帝选后的时机?”太后素来是个平静温和的人,再加上甚少与前朝官员来往,此刻突然目露寒光,令正使打了个冷颤,惶恐地回答道:“皇后之位臣不敢妄议。臣只是依据所观测到的天象如实禀告。眼下,凤星闪烁,似有蓄势待发之意。但是凤星并不明朗,微臣不敢擅作主张。”
太后听闻,疑惑不解,问道:“凤星既然已经出现,为何又说并不明朗。莫非是钦天监无能,不能明断凤星。”那正使着实紧张万分,后脖颈已出了一层薄薄的冷汗,他跪在地上,颤抖地说:“请太后恕罪。凤星是天上的重要星宿,光芒万丈,钦天监任何一人都可分辨。只是当下情况有些复杂,臣与钦天监诸臣,共同观测,已经确定了凤星的位置。只是……”
“既然已经确定了凤星的位置,钦天监为何犹豫不决。”太后流露出一丝不满,不耐烦地说:“莫要吞吞吐吐,有何内情尽管奏报。哀家谅你不敢在皇后之位上胡言乱语,你只管如实奏报,若是有所欺瞒,哀家定不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