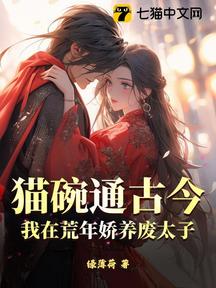李长风和陆衡带着沈父在村子里四处转,了解大凉村的风土人情,路过的村民纷纷和他们打招呼,这是沈父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淳朴又热情。
陈月听着夏堇青的意思沈父以后会在这里和他们一起长住,不走了,笑着道:“那好啊,沈叔有的是时间可以看到大凉村的好风景。”
复又想起:“以后两个小家伙是不是可以交给沈叔教导啦,堇青你不知道这段时间,长风和我变着法子教,一个头当真是两个大。”
夏堇青哈哈大笑,道:“那没事了,我爹爹很厉害,教导他俩肯定没问题。”
那边三人组,李长风也在说着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逗得沈父笑个不停,直接揽下教导重任。
陆衡道:“启蒙交给阿爹绝对没问题,等阿爹教烦了,就将两个小家伙送去镇上学堂,我看着。”
三人一路说说笑笑,将两个小家伙的未来安排得明明白白,此时他俩还在美滋滋地吃着卤香蛋。
除夕夜,爆竹声从早上开始没停过,李长风下午带着瑞宝上了一趟山,沈父在家里写春联,这会儿李长风和陆衡带着两个娃,端着米糊,贴着各自家里的春联。
陈月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夏堇青帮着烧火,院子里饭菜香味没断过。
家里今年的菜地里种了土豆和菠菜,年夜饭的菜品很丰盛,有糖醋里脊,两个小朋友的最爱,酸辣土豆丝,蒜泥菠菜,笋干烧肉,四喜丸子,鲜汁腊鱼,香辣干锅鸭,莴笋丝炒鸡蛋,凉拌海带丝。
还有一道蘑菇干炖老鸡汤,里面加了参片,给大家补一补,凑成十道菜,寓意十全十美。
每道菜的份量不多,要留着肚子守夜时吃饺子,剁得猪肉馅,包了白菜猪肉饺子,捏成一个个胖肚子的形状,瞧着就喜人。
夜幕降临,李长风在院外放爆竹,两个小娃捂着耳朵,激动地又叫又跳,开心的不得了。
堂屋里点了灯,烧着炭炉,温暖又亮堂,一起坐下吃年夜饭,陈月给沈父舀了鸡汤,道:“沈叔,里面加了参片,您多喝点,堇青和陆衡也要多喝,自已动手。”
沈父接过来,三人笑着点头,晓得她是担心他们在京里没过好,这会儿回家了给他们补回来。
李长风给陆衡倒了酒,他俩喝酒,其他人喝鸡汤,一起举杯,辞旧迎新,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后会更好。
大年初一,李长风和陆衡二人似是昨晚守夜时说好了一般,两位有心人率先起床,在厨房里一人烧火一人打鸡蛋,做了三碗糖水蛋,端进屋里,让陈月、夏堇青和沈父坐在床上吃完,寓意新的一年健康幸福。
沈父和夏堇青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习俗,体验很不错,暖人又暖心,决定以后要保持。
之后他俩带着小娃去村里跑年,陈月拿出糖果子,问夏堇青要不要拿点回去,将家里大门打开,等会儿村里小家伙们好去拜年要糖吃。
夏堇青去年见陈婆婆弄过,算是有点经验,于是带着沈父一起,端着糖果子去了后面家里。
今年萝卜头们后面缀了两个更小的萝卜,孙婆婆家的容儿领着他俩,迁就着两人的小短腿,慢悠悠地落在后面,陈月给前面的小家伙们拿好了糖果子,这三人才到她面前。
“月姐姐新年好。”
“娘亲新年好。”
“姨姨新年好。”
“哎,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糖果子放在陈月给他两特制的小布包里,摸摸荣儿的头,道:“谢谢容儿照顾他们两。”
容儿腼腆地摇摇头,他可喜欢两个小侄子了,懂礼貌,干净又可爱,拉着他们的小手又乖又听话,不像村里其他小孩吵吵闹闹。
三人跟他挥手要去别家拜年,一窝小萝头,浩浩荡荡,挨家挨户,大凉村真好。
陈婆婆他们是大年初二一早到家的,回来就马不停蹄地将家里打扫干净,过来接四人回家,两家一前一后也就几步远,陈月和李长风也跟着过去,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陈掌柜一大家子也过来了,中午又是一顿大餐,吃饱喝足还拎着不少东西回家。
陈婆婆他们落后驾着马车带了不少好东西回来,居然还有一副麻将,说是京里时下流行的娱乐活动,这下好了,可以经常打麻将了。
最让陈月开心的是好多水果,连柠檬和橙子都有,每样拿了一些送回家,李长风和陆衡带着沈父与陈掌柜四人打起了麻将,两个小娃和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玩得乐不思蜀。
回到家,用箩筐装好水果,捡了一些樱桃和橘子带去阿娘家,让大家尝尝。
陈父过来开门,“阿爹,我过来转转。”
“快进来。”
“阿娘。”
“哎,在堂屋呢。”
陈月把橘子递给陈父,自已端着樱桃去厨房清洗,进了堂屋,见阿娘和小鱼在缝制喜服,问道:“陈阳他们呢?”
“给莲素娘拜年去了。”
陈月点头,“来吃点水果,给他们留一些。”
“哪里来的?”
“堇青他们从京里带回来的。”
“怪不得,这些都没见过,他们回来了啊。”
“都回来了。小鱼嫁妆准备得怎么样啦?”
陈母笑着说:“差不多了,喜被请婶子们帮忙做好了,她的喜服自已做,还差一点。”
小鱼有点害羞:“快完成了。”
时间一晃,小鱼要嫁人了,这天还没亮,陈家一家人就起来忙碌着。
陈母给小鱼梳头,梳着梳着还红了眼睛,小鱼跟着红了眼眶,陈母嗔怪:“大喜日子不兴这个,以后嫁人了要好好过。”
小鱼抹了抹眼角点头。
陈母拿出准备好的荷包,道:“这银子少你别嫌弃,你留在身边。”
小鱼推辞:“姑母,我不能要,这些年我做工你们一分钱都不要,我自已攒了一些,连柳家给的彩礼你们也不肯要,全都给我了,这叫我怎么还能要呢?”
陈母:“给你你就拿着,傻丫头,多点留在身边备用。”
小鱼接过,眼泪还是流了出来,姑妈一家对她太好了,比起生身父母过之不及。
天亮了,院子里热闹起来,听声音像是月表姐他们过来了,这不说到就到了。
“表姐。”
陈月和莲素一起进来了,笑着道:“小鱼,恭喜你。”
两人递上红纸包的喜钱,小鱼站起来不知所措,忙摆手说不要。
陈月:“大喜日子,这个还是得要的。”
小鱼望向陈母,见陈母点头,才接过来,沉甸甸的,心里又是感动又是委屈。
陈月和莲素帮着一起梳妆打扮,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嫁。
有人敲门,“阿月”,是李长风。
陈月开门出来,见他抱着瑞宝站在门前,问道:“怎么啦?”
瑞宝要娘亲抱抱,陈月手上正拿着东西,摸摸他的小脸蛋,“让爹爹抱啊”,抬眼看向李长风示意的地方,那里站着几个人,陈月打眼望去一个也不认识,一脸疑问。
“喊阿娘出来,这些人应该是小鱼那边的。”
……啊?
陈月转身进屋子,放下手里的东西,喊阿娘他们出来。
陈母出来,看到那些人先是一愣,然后走过去,站在陈父身边,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那为首的男人还没开口,旁边的妇人抢着斥道:“大姐,你不厚道啊,我们找女儿找了这么多年,原来被你家藏了起来。”
陈母皱着眉头:“什么叫我家藏起来?我藏你女儿做什么?”
那妇人:“谁知道存了什么心思?你就说小鱼这些年是不是在你家?”
陈母望向那男子,道:“王有银,现在是什么意思?”
那人触到陈母的视线,赶忙低下头撇开。
那妇人抢道:“什么意思,当然是接女儿回家,还有这些年在你家干活的工钱结一下。”
“扑哧”,陈月没忍住笑了出来。
那夫人对着陈月喷口水:“你这小妮子笑什么?”
陈月:“我笑有的人说话真有意思,不仅有意思还特别无耻。”
那妇人要上前理论,瞥见站在一旁的李长风时突然偃旗息鼓,转过头继续对着陈母叫嚣。
陈母没搭理她:“王有银,今日小鱼出嫁,你非要闹这一出?你是她的亲生父亲,小鱼娘亲去的早,你们不怕她半夜找上你们嘛?”
后面这话是对那妇人说的,那妇人听到后肩膀瑟缩了一下,最后还是无耻占了上风,“谁同意她出嫁了,出嫁要父母之命,我们没同意。”
陈母忍无可忍:“你算她哪门子父母?”
那妇人突然坐在地上,撒泼道:“今日不还女儿我就不走了。”
屋门吱呀一声,小鱼穿着喜服走了出来,大红色的喜服真是好看的耀眼,那妇人旁边的女子盯着小鱼,露出了嫉妒的目光。
那妇人从地上站起来,跑到小鱼面前,拉着她的手,笑嘻嘻地道:“女儿,跟我们回家。”
小鱼冷漠地甩开她的手,道:“回家?回哪个家?这里才是我的家!”
那妇人又开始喷脏话:“你这小贱蹄子,不得了了,几年不见,脾气涨了啊。”
小鱼看着王有银:“爹,今日女儿出嫁,娘不在了,你是来祝福我,送我出嫁的嘛?”
王有银脸色一白,想要说什么,被那妇人打断:“你爹还在,出嫁也要从家里出嫁。”
小鱼:“今日我就要从这里出嫁。”
那妇人:“那聘礼和这些年的工钱要给你爹吧,你爹和我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
小鱼气笑了:“你养我?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养我把我送给老财主做妾换银子?养我让我睡柴房?养我让我一个人没命的干活你们在家享清福?养我就是你们一家人吃大饭施舍我一口,我还要感激涕零?”
那妇人理亏人不亏:“那也是你爹,生你的爹,没让你饿死,今日聘礼钱和工钱必须给,不然我们就不走了。”
小鱼:“工钱?什么工钱?”
那妇人:“你这些年在你姑母家干活的钱。”
小鱼无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摇头又一边落泪:“我姑母这些年可没让我干过活,我一直在镇上做工,学做工的钱还是月表姐出的,何来工钱,还是你要给我还了表姐出的学费?”
那妇人听着没要到钱还要倒贴钱,那可不答应,又坐在地上开始撒泼:“那聘礼钱呢?谁家聘礼不给父母?”
小鱼拿出荷包:“给的聘礼十五两银子都在这。”
那妇人连忙站起来要去抢,被小鱼躲过,道:“你们要聘礼,我这嫁妆呢?”
那妇人:“嫁妆不是在这嘛?”
院子里,陈家给准备的嫁妆堆在一旁,惹人羡慕。
小鱼:“这嫁妆是我姑母准备的,你要聘礼,自然嫁妆该你们准备。”
那妇人嗫嚅:“这些个东西也不值钱,顶多二两银子,你拿二两出来。”
小鱼:“这些都是我姑母精心准备的,没有十两银子可拿不来。”
那妇人叫了:“放屁,你去问问谁家嫁妆十两银子,这不是坑人嘛?”
小鱼盯着她不说话。
那妇人声音渐渐小了,比了个手势,道:“五两,只能五两!”
小鱼拿出五两,将余下的十两递给王有银,那妇人要抢,小鱼没让,道:“爹,女儿嫁的那家姓柳,这是柳家给的聘礼,你拿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此以后没有以后了。”
王有银原本瑟缩的肩膀又下垂了一些。
小鱼笑中带泪:“爹,今日我出嫁,你是祝福我的吧。”
王有银望着她,半晌,点点头,又抬起手来,摸了摸她的头,之后转身离开了陈家,银子最后还是被那妇人抢走了,几人如来时一样离开了陈家。
小鱼望着阿爹佝偻的背影,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李长风对陈阳耳语了几句,陈阳心领神会,悄悄出了门。
柳家来接亲的人到了,锣鼓声爆竹声震耳欲聋,陈母将小鱼送进了花轿,看着柳家浩浩荡荡地把人接走。
接亲队伍路过来时的三岔路口,一个男子孤身站在另一条路口,遥望着这支喜庆的队伍渐渐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才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