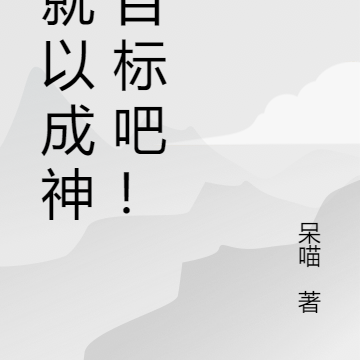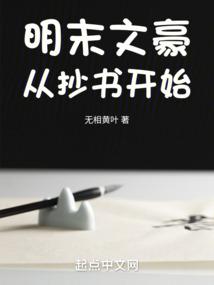第16章 乱战
董老白衣黑裈,神色豁然。
他从布衣青年手中取过木杖,狠狠一敲,余音回响中庭。
“农家董正,先闻法家…燕舟所述人性本恶,自觉不然,故有一论,请诸位听评。”董老轻轻敲打木杖,环着讲学台的边缘走,面向一众学子,身后布衣青年始终跟随。
“老夫一生与田为伴,不同你们这些捧着书卷的文人,农家之人灰头垢面,学问都是一把土一瓢水浇灌出来的,不会有文家卷言飘逸灵动之感,还请诸位见谅。”
农家很少参与学宫论战,但在座学子无一不正襟危坐。
就连三位皇子也聚精会神,灵王和苍王或许是因为董正司农卿的身份,又或是与其他学子一样对农学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但明海不同。
在卧龙智术里,明确地记录了关于农家的学术基础,即: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华夏古人将“食”放在政论的首位,足以见得农学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董老深深地吸一口气,脸上似乎显出一抹少有的紧张。
“我曾想过人性,这是各家各派都逃不开的问题,我会问自己,人性是善还是恶,当我见田里的佃农后,我便认为人性向善,继而又会开始想,为何善?”
“我曾获得过一些认不得的种子,照在太阳底下,瞧不出好坏。于是,我就把它们种在不同的地方,润水、淤荫、除杂各有所异。半年后,这些种子纷纷开花结果,我便去看,有些长得好,而有些长得不好。”
“我想什么人性,人性就像是一枚种子,好的种子会坏,但坏的种子一定不会好。因而,就意味着那些种子其实都是好的,就像人性都是善的那样,只是环境不同,有些会结出善果,而有些结出恶果。”
“我想问诸位,这世间难道没有善人吗?如一粒种子,心本恶之人无论如何,也难以开花结果,而心善之人却会受处境所扰,或是不忘初心,或是步入歧途。”
“终其而终,人性善者为恶,是人的选择!”
董老扶着木杖,只是调转目光,看向黑袍正冠的青年,微垂而正的眼睛闪着壁上的烛光,像是残火未尽时的遗憾,他的眼神透着火烧般的怒,以及余烬下的悲。
许多年的经历,塑造了老人,却也让人变得敏感。
事事都有逻辑规律,沧桑年岁使得人更容易发现端倪。
董老看见了黑袍青年藏在眼里的野心,那是一捆易燃的薪柴,已经烧起了一股足以焚烧己身的火,刀光剑影在火海里若隐若现,身居官场中心,刀剑寒芒越是显眼,火势也越是浓烈。
眼看火势高企,而纵火之人安然自得。
董老转眼怒视卫公,对方那身黑袍像是一枚刺眼的针,落在讲学台的中央。但卫公像是没注意到董老含怒的目光,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学生。
“董老以种收为例,学生收获匪浅。”燕舟长拜,而后话锋一转,“然而,董老如此断言,实为大谬!”
讲学台上一阵惊呼,排山倒海似的波及到台下,凝聚成更大的惊呼声。
顷刻间呼声四起,众人议论纷纷。
燕舟再次走出,朝着董正的另一个方向走,“古往今来,恶人不胜枚举,恶事更层出不穷。古人有四喻,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能被如此形容之人,在座诸位可有觉得其性本善的人吗?杀人无数者,烧杀抢掠者,屠城者,下令活埋者,这样的人真的心中存善吗?”
“其一,人性未必存善,这便是缘由。”燕舟望向董老,面无表情地说。
“其二,若是人性本善,是否还需要德治教化?若人皆善人,何需教人行善?天下无恶,圣人之言中还需要去强调修养教化吗?人行善道,为何还要制定法律?法治人,人故而不向恶,非恶者,即善人也,此为法治!”
“其三,董老所谓之环境,无非是人制欲望,若是面有千金,多数人会拾起,少数人会嗤之以鼻,但当面前不止是千金,还有百家书卷,有……万收之粮种,慕金者拾金,好学者阅卷,农者……为万民而珍收粮种,这就是欲望。”
“欲望即为贪念,贪为劣根,若是嗜血之人则拾刀剑,若是善战者则握紧缰绳,此为人性,必不会弃刀剑而清心,更不会放下缰绳卧马而歌。人性随心而起,心有欲望,便是恶,即人性本恶也!”
他讲完,一片寂静。
就在众人还没喘过气的时候,董老健步而起,来到讲学台的中央。
他瞪了一眼燕舟,杖拄地,朗声道:“所谓欲望,是为人之本能,肚子饿了就要吃粮食,这是恶吗?而嗜血善战,这是人之本能否?非也,此为人之悟性!”
“另外,善非教也,而在乎行!圣人强调修养教化,是要人去行善,而非教人行善,善者行善,是因为他们相信世间有善,故而行善也!”
“至于你所谓的四恶喻词,老夫懂,更比你懂得要多了多,可你所言之恶,比起权谋斗争,不过尔尔!”
虽然话不多,但董老阐述了人为什么做善事的原因,就是因为做善事的人相信被帮助的人是善人,所以才会想着去帮助其他人啊。
明海虽然觉得人性本恶,但似乎是受到了“卧龙智术”的影响。
他的脑子里已经开始回想起无数先贤名言,犹记得“卧龙智术”的祝福奖励,他精读包括《申子》《韩非子》在内的十余本书籍,换而言之,明海目前所掌握的学识是诸葛亮在青年时所研学的全部。
然而,在前世,明海始终相信一个道理。
绝对没有绝对的事情。
因此,虽然明海回答八皇子人性本恶,但要说人是善是恶,他心里也不会有绝对的答案。
忽然间,一名黑袍文士站起身,拱手朗声道:“事无节制,人之天性,若不加以制止,世间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
董老眼一瞥,正好看见卫公在与门下弟子比起身的手势,再转头看着身边的布衣青年,后者咧嘴露出一个憨笑。
董老无言,嘴角微微抽搐,这老东西是要仗着人多欺负人少啊。
就在这时,民家弟子突然起身。
白袍文士拱手向荀老行礼,旋即对法家弟子问:“人皆有善心,教书育人者当从善方可成师,故而,若世人本恶,何来圣人教化天下?”
法家弟子又有人起身,“邦国兴亡之大事,君寄希望于圣人复活,实则人治,而非民治,有悖于所谓民学之道!”
民家弟子毫不示弱,起身作答:“人治侍德,至少强过先生权术治国,尔等所谓法家,乱世之学也!”
法家弟子面露怒意。
卫公脸色一变,轻敲法简,沉声回应:“法家三派,其根同一,皆以认同法治为根本,而在推行中各有侧重。若无视法家根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为谬论也!”
荀老忽然走出来,补充一句“民家讲究仁爱、礼义,认为人应以德治国,通过教化百姓达到社会和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让人们明白道义,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卫公不言,看了一眼燕舟。
燕舟会意上前,朗声道:“法家主张法治,强调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只有严格执法,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权益。民家的德治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民家大弟子当仁不让,反驳道:“法治固然能维护秩序,但过于严苛的法律只会让百姓心生畏惧,难以真心归顺。而儒家的德治则能让人们从内心产生敬畏,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
讲学台上,火药味愈发浓烈。
黑袍白袍交织在一起,彼此引经据典,唇枪舌剑,犹如舞池里踩在书卷上的黑白天鹅,共同将这一场论战推向了高潮。
忽然间,明海觉得自己的袖子被轻轻扯了一下。
白凰嘟起嘴,示意他朝一个方向看去。
那是在讲学台上,黑白人影攒动之中,董老拄着木杖,身后跟着那名布衣青年,宛如箭矢般切入论战中心,而与其相面对的,是卫公和燕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