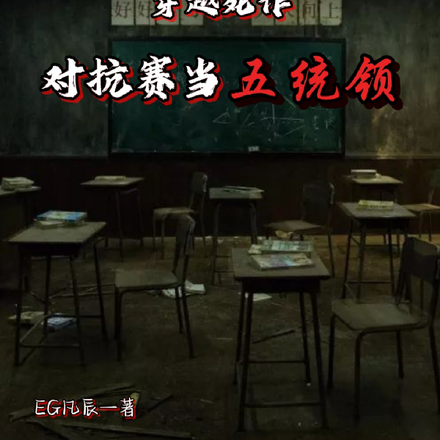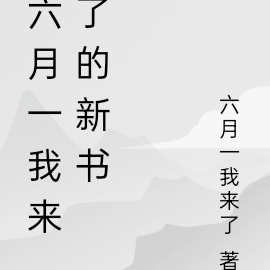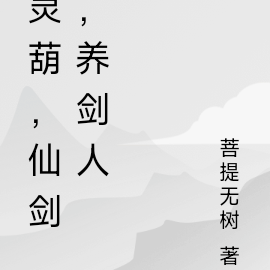姜云抱病休养将近两个月,期间从未露过面,引起了不少人怀疑。
房间内,姜流云坐在桌前,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眸子微垂,神色忧愁。
这些日子,她在思考,思考是否该结束女扮男装这场闹剧。
本来重生后,她不想再过上一世军旅生活,只想补偿柳尚,嫁他为妇,在大宅中平淡地度过此生。可是……
柳尚的人生出错了,辜负了她,他和其他人结婚了,一个星期前已携家眷南下去了江都任职,此生他们两人可能再也不会相见。
突然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她变得迷茫,连续几日闭门不出。
是该以女子身份困在后宅之中,还是以姜云的身份在驰骋沙场,和上一世一样最后落得个为国捐躯的下场,死后和神仙所说一样入地狱?
她不清楚,也不明白。
但是她知道姜云再不出面,其他人要坐不住了。
祁连落棣早就开始向姜朔行打听姜云的消息了,但姜朔风固执地不让其他人接近姜云的院子,所以姜朔行也只能作罢,回复祁连落棣姜云还在修养。
姜云不在,折冲府那边,重虎那些人不服管教,直言只听姜云的话,其他人没有资格和他们说话。
萧贺被凌迟,青阳侯府也因此受了重创,青阳侯自然不肯作罢,将姜云和姜朔风视作仇人,不时派人潜入姜府。
皇帝祁连泽昨日也下了旨令,要求姜云在这个月内必须露面。
“咚咚咚……”
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姜流云的思绪,她低下眸子,将思绪藏了起来。
门外传来声音。
“流云姐姐,是我,姜朔风。”
“进来吧,门虚掩着。”
闻言,姜朔风推门而入,进来后,又转身将门从尽然锁上。他手上拎着一个食盒,走到姜流云旁边,将食盒放在了桌子上,随后又走向窗户前,将窗户关了起来。
看着面前的食盒,姜流云不禁摇头笑了起来,“朔风,你上次不是看过了吗?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全部都结痂了。”
食盒里不是糕点,而是药和一些纱布,食盒只是伪装,防止别人怀疑。
姜朔风走到姜流云旁边坐了下来,神色认真地看着姜流云,一字一句道:“是结痂了,但是要尽可能地不留下疤痕。”
上一世,有一次,他给姜流云处理伤口的时候,姜流云看着满身的伤痕,苦笑说:“我这一身伤疤,哪里像个女孩子家?”
他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姜流云再飒爽,也是个姑娘。母亲说过,姑娘家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即使姜流云再活泼,调皮,母亲也将小时候的姜流云打扮得美美的。
从此,他刻苦钻研,总算是研究出了能够去除疤痕的无痕膏。
姜流云摇了摇头,“留疤就留疤吧,我不在意。这一世我不嫁为人妇,以女子身份孤独终老也好,以男子身份在外打拼也罢,并不会有人关注我身上的伤。”
姜朔风一愣,许久方才回过神,说:“你可想好了?”
姜流云自是知道姜朔风在问什么,她摇了摇头,道:”我不是什么大义之人,他的存在并非我所愿。可乱世有国才有家,必须有人为国家牺牲。”
祁天之前重文轻武,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与敌军交战的武将并不多。纵观上一世,各国混战,在军营中出头,大名鼎鼎的人很多,而祁天只出了她一个忠武将军,最后还死在了青山峡中。
“所以……”她忽然正视着姜朔风,眸子睁大,很认真地问:“朔风,你觉得我该如何?”
只见姜朔风睫毛颤了颤,低眸说:“天高海阔,你的人生如何,应由你来决定。只要……”
说到这,他突然停了下来,同样抬眸认真地看着姜流云,“不让别人伤害到你就好。无论如何,用什么手段,别人都不可以伤害你,伤害你的人,都必须下地狱。”
伤害她的人?
姜流云眸子中有不解,“此话何意?”
姜朔风却避而不谈,抬手将桌上的食盒拉过来,打开,将里面的药盒取了出来。他拿着药盒,微微笑着,桃花眼中流露很温柔,很温柔的光,“没事,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上药吧。”
姜流云眉头微皱,打量了眼姜朔风,见他并没有想继续刚才话题的意思,于是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你不想说就不说吧,我不为难你。”
说着,她站起身,走向床边,背对着姜朔风将身上的衣物利落地脱了下来,直到只剩下里面和里裤,然后上床,头靠着枕头,趴在床上。
姜朔风拿着药走了过来,轻柔地将姜流云身上的衣服往两边拉开,露出白皙但伤痕累累的后背和肩膀。他眸光微暗,眸底满是心疼。
这一世,他还是没保护好姜流云。
本不该,本不该让她有这么伤痕的。
他闭上眼睛,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特别是临死之前的一幕,疯马驮着晕过去的姜流云远去,生死未知。
他猛地睁开眼,下定了决心。
他将药盒打开,挖起一小坨药膏,温柔地涂抹在姜流云结痂的伤口上。他的动作很轻,很轻,像是羽毛掠过皮肤一样。
窗外大雪纷飞,积在枝头的雪压断了树枝,啪嗒一声掉落在地。房间内很安静,除了炭火滋滋燃烧的声音,就只剩下两人均匀的呼吸声。
姜流云觉得很安心,思绪和身体放松了下来,渐渐的,她闭上了眼睛。
等姜朔风给姜流云上完后背的药,正准备叫人翻一个身时,就发现姜流云已经睡了过去,呼吸声很轻很轻。
他微微一笑,笑容宠溺,还带着由衷的开心。
随后,他弯下腰,在姜流云额头轻轻啄了一下,又快速站直身子,僵直地站着,像是偷吃了糖的孩子。
心脏砰砰地乱跳,他耳根变得通红,俊美的脸上也浮现红晕,望着姜流云,眸光闪烁。
他一直将爱藏在心底,藏得很深,不敢表露出来,哪怕一点点。他怕,怕姜流云会因此抛弃他,无法再和姜流云保持亲近的关系。
他从未对姜流云有过非分之举,最过分的也不过是在姜流云耳边轻语。他也从不敢想象有非分之举,给姜流云疗伤上药时,也只是单纯将她当做病人。
原来,亲吻喜欢之人是这般奇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