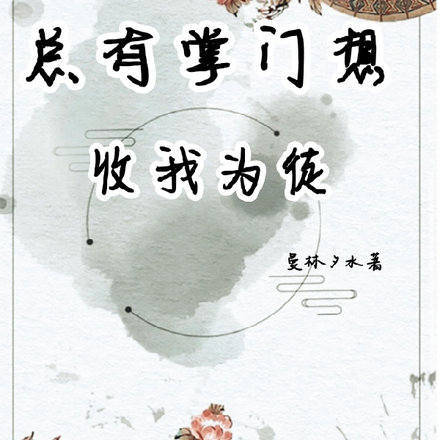两人都还无法担负起长时间的变幻之术,但就这样无功而返,难保邪祟会不会察觉到异常逃逸出城。
明笑打量了眼自己十二三岁的瘦小身板,视线逐渐了一旁环手抱臂而立,蹙着眉头思索着对策的小师弟陈鹤上。
十五岁的少年身量还没开始疯长,稚嫩的脸庞没什么棱角,介于清秀与俊朗间。
唇红齿白的师弟,若是换上套妆容,似乎看着就像是肩头稍微宽一些的适龄少女。
在这热切的目光注视中,陈鹤终于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眼见着师姐的眼神越来越诡异,嘴角还露出了不太熟练而更加显得扭曲的笑,他心里莫名升起一种不妙的预感。
“小师姐,怎么了...”
你这样子我害怕,别笑了!
后半截话他没敢说出来,迎着这样的目光不由心生退意。
在他把自己近一年做过的事都翻出来抖一抖,百思不得其解是哪里做错了的时候,心中捕捉到了一个念头。
“总不会是要让我去扮新娘子吧?!”
在得到明笑肯定的回答后,陈鹤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师姐,我是男子啊!我怎么可能扮得了姑娘,你看我这这眉毛,这肌肉,多英武!”
“师弟,这里头的人也只有你的身量适合,况且,以你的修为,简单修饰容貌很轻松。”
陈鹤看了看孩子身高的小师姐,又看了看虎背熊腰的壮汉宋年,虽然嘴上不松口,却无法否认他自己是最好的人选。
面相浑厚恭敬的宋年也笑呵呵地附和,仿佛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火上浇油,“大人,我们东临城可有顶好的梳妆娘子,我见过一次,那巧手啊,灵的呦,可以把丑的变为美的,让少年变为五六十岁的老丈。”
明笑拉住炸毛想跑的陈鹤,露出个温柔关切的笑容。
她一点也不记仇,真的!
该死的熟悉的笑容让陈鹤想起了被坏女人谢兰烟欺骗得团团转的记忆,心中半是惊恐半是麻木。
道歉的时候小师姐明明笑着说不会记恨当时那些不懂事的怠慢和轻视的!
谁说小师姐不记仇的!这肯定是赤裸裸的报复!
胳膊拧不过大腿,陈鹤最终还是乖乖地坐在绣凳上任由梳妆娘子大展身手。
“师姐,这样看着好奇怪,不太协调。”
明笑扶正“新娘”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扫视着会露出破绽的地方。
“问题不大,那邪祟都是在新嫁娘上了花轿后才出没,走动的时候收敛一些便好。”
“噢。”陈鹤乖乖应下,又把发饰掰了回去,“这个这样歪着戴好看。”
说着,拖拽着厚重嫁衣的少年猛地就要站起来,裙角绊到了桌角又被弹了回去,发出很大的绣凳划拉地面的声音。
他浑然不觉地嚷嚷着,“小师姐,快帮把我选的那个蓝底有紫色小花的镯子拿过来!”
还一边兴致勃勃地对着铜镜比划,好像准备亲自操作似的。
谢明笑:......
無錯書吧一个积极好奇的配合对象,总比被赶鸭子上架黑着脸扮新娘要好。
经过梳妆娘子那双巧手的妆点,陈鹤变成了个略有些高挑的漂亮姑娘,配合上变换之术,罩上盖头,不熟悉的人很难看出破绽,看起来还真能扮作新娘子去勾引邪祟。
梳妆娘子绕着大红喜服的“新娘子”转了个圈,拍了拍手,“请小公子走动两步。”
陈鹤依言照做,走了几步后,大家都沉默下来,他茫然地挑开盖头。
?怎么这个表情
梳妆娘子很快又咧出大大的笑容,指间点点他的脸,顺势揽上了他的胳膊,“小公子,啊不对,姑娘,女儿家走路自有一番姿态,就让妾身来教教你吧。”
她掐着兰花指掩唇娇笑,“妾身保管把姑娘调教的看不出破绽。”说笑间,还抛了个情意绵绵的媚眼。
师姐救我!
陈鹤汗毛炸起,却见自家师姐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溜至屋外,心如铁石地合上了门。
仅半天,宋年就商议出了户适合“办喜事”的人家。
这事儿说来有些巧,倘若是别人家或许都不会选在这档口冒着风险办喜事,便是姑娘硬生生拖过了适龄的年纪,不也比招惹上邪祟强吗?
但这户人家偏偏有些不同。
东临城中,有位富户关老爷,年过五十,颇有资产,发妻早逝,唯独剩了个二八年华的独女关莹莹。
关老爷老来得女,自然是把闺女当眼珠子一样捧着呵护着长大。
女儿关莹莹出落得如花似玉,性子也单纯娇俏。关老爷待她如珠如宝,生怕女儿受人欺负,因此生出了招赘的心思。
哪曾想关莹莹被人哄骗去了,誓要嫁给心上人胡文矢志不渝,在东临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矢志不渝的故事在茶馆中流传,甚至有被打动的文人墨客还歌颂过她的忠贞。
可心上人胡文高堂具在,坚决不愿意入赘。
低嫁本来倒也无妨,同在东临城,不过是隔了几条街的事,想要去看女儿不过是出个门的功夫么,可问题出在胡文这个人身上。
“那胡文,我悄悄地遣人去看过,除了一张好面皮,肚子里装的尽是些哄小姑娘的情话,在家里连根扫帚都不愿意扶的人,嫁过去,可不是要让莹莹受苦吗!”
明笑与陈鹤听得目瞪口呆,手中的事情不自禁慢了下来,“那这些事,没有同关小姐说吗?”
屋外头娇气清脆的声音响起,随即嫩黄春装的娇俏姑娘推开虚掩的门进来了,“爹你又偷偷背着我说胡郎坏话,胡郎那双手是摆弄书卷,用在书法丹青这种雅事上的,那里需要他干什么粗活呢?”
说罢,关莹莹又向两人见礼,才转头安抚气呼呼的老父亲,“爹爹,胡家那里敢使唤我呢?况且便是嫁入胡家,我这不是隔三岔五还能回来看您吗?”
“你净是说这些好话来唬我,那小子平日尽是吟那些酸诗,说什么银钱皆为阿堵物,根本不通庶务。胡家又连个稳定点的营生都没有,嫁过去恐怕全靠你养着。”
关老爷越说情绪越激动,“那我问你,你爹我在时还能为你筹谋,等我老的走不动路了,这些铺子又谁来接手,又有谁来替你养这一家子人?”
“当然是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