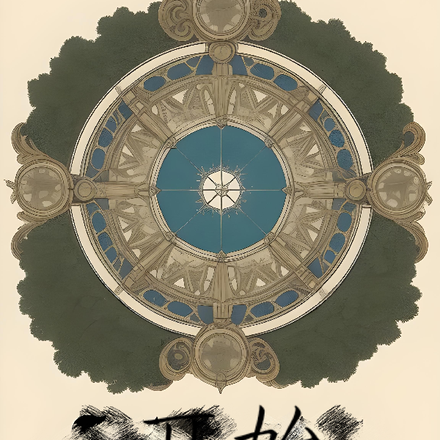在我们家这棵梧桐树的正南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机井,那个机井不是太粗,井沿高高地,我每次路过那里,总想伸出头往里面看看。
有时,我也能看到有几个花的或者绿的青蛙,浮在那不深的水面上,有时也能看到一条比胳膊稍微细点的花红蛇浮在那水面,我就总是一手推着那凸出来的厚厚的井沿,一手扳着机井边上栽的那棵不粗的松树,头探着往那机井里看。
那时的机井里,水面根本都不深,反倒是很浅,那花红蛇,就跟一根棍子一样,在里面浮来荡去,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水面总是来回晃荡着,就跟这水面下有什么大东西在乱动一样。
那花红蛇就想游过去,逮住那比我巴掌大很多的青蛙,可是那青蛙一看这长虫荡过来了,就猛地一下子扎了下去,那长虫就捕了个空,等一会,那长虫正在左右犹豫着时,那青蛙就又在井壁边边上,偷偷冒出头来。
我一直在那里乐不知疲地看,那个花红蛇,就跟个笨蛋一样,一直对这长得很花哨的青蛙束手无策。那时的机井里的水,都非常干净,而且还能直接喝,我看到过好多次。
無錯書吧大人把水桶系下去,左右摇摆着晃荡几下,然后猛地松一点手里的绳子,那水桶就底朝上扎了下去,慢慢地那水桶里就灌满了水,然后轻拽绳子,那水桶就站正了。
再攒足了劲往上拽,三五下就把装满清水的水桶拉到了井沿边上,趁桶里的水还没有洒到外面,赶紧用手去抓住那个桶鼻子,往一边一拎,满满一桶水就打了上来。
一般这个时候,打水的人都比较渴,就连忙蹲一身,双手抱着水桶,探出头来,把嘴直接往水桶里一凑,跟饮牛一样,咕吱咕吱饮上一大气,然后再站起来,看着太阳打个饱嗝,那个爽歪歪啊,就别提了。
其实就算这机井的水里落进去一些草屑或者柴禾啥的,也不影响这水的洁净跟清凉的,在生活条件还不太充裕的时候,喝一口这样的井水,常常也是相当的解渴和惬意的。
我也是常常看到因低了头喝水的人,在站起来之后,脸憋得红杠杠的,在愣神好一会儿之后,那脸色才慢慢回转,可那人的神情却是极度享受与舒爽。
在这机井边上,有人家种了几畦豆角,刚开始发芽的时候,我还在那里逮过蚂蚱,当时也没觉得这豆角能长成啥样子,后来人家弄了很多细竹杆,插在那豆角苗边上。
然后在那竹杆上攀了很多布条子,那些面条子各种颜色都有,而且攀出来的形状都是差不多大小的菱形,我就觉得这些菱形块,有些琳琅满目,煞是好看。
所以就几乎每天往那里跑,在那些竹杆攀出来的菱形块下面钻着玩,一会儿逮一个蚂蚱,一会儿抓一个蛐蛐,反正如果不是家里大人喊我回家吃饭,我能一直玩下去,乐不知疲。
不几天,那些豆角就开始往这菱形块上爬了,这些豆角秧好像很有灵性一样,就绕着这竹杆,转着圈往上爬,爬到顶上,再沿着这些菱形块再往边上爬,边爬边长出叶子,开出白的紫的花,这些花还没有落的时候,就有青的红的细豆角长出来。
没过几天,这些豆角就长得比筷子还要粗还要长,有的甚至能拖到湿漉漉的地面上来。那些长着大板牙的蛐蛐看到了,就偷偷摸摸跑过来,屁股撅着,一下一下地把这些豆角给嗑断了。
不几天,这些豆角便爬满了菱形块,我再过去玩时,就看到原本五颜六色的菱形块消失不见,进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可以遮挡阳光的天然的去处。
只是这豆角架子下面,经常往下垂着长长短短的豆角,每回我看到人家过来摘豆角,都是擓着一个大箩头,没一会儿,人家就摘了满满一大箩头豆角。
人家吃不完,就装进背笼里,往车子上一挎,一大早就去赶了早集,等太阳出来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的时候,人家的这些豆角就已经卖完了。
说老实话,我们家一直就缺乏这种做生意的思维。家里种的北瓜结了那么多,有的时候摘回来根本吃不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把这些北瓜卖掉,换些钱回来。
而我大姨家那个大姨父,一直是以种菜卖菜为营生的,所以人家的日子,一直以来都过得相当滋润,好像从来都没有受过缺东少西的窘迫。
我大姨家门前种了好几棵柿子树,按照常规的思维,一到秋天,这些柿子树上的柿子都熟了,如果是我爹肯定会摘了送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偿地去吃。
而我大姨父把这些柿子抽下来之后,用车子拉过来,叫我爹帮忙到庄上去卖,你别说,我们这里还真没有人种柿子的,所以,一大车的柿子,一天不到就卖得净光。
当我大姨夫拉着车子,揣好了钞票美滋滋回家的时候,我爹却从来都没有醒悟过来,自己的日子为什么越过越穷的原因。如果单论个人的能力,我爹绝对不比别人差。但是就是在过日子精打细算方面,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我很小,还真的不懂大人们过日子的道理。但是,我却看到了人家很明显的比我们强出了很多。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人家比我要能很多,虽然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但由于言传身教,或者说是潜移默化吧,对于出门做生意,或者当小工去挣钱,好像在我们家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和抵制,所以,宁愿饿着,穷着,窘迫着,也不想去努力挣点钱来。
所以,我们家的日子,就慢慢地衰落了,以至于后来,看着别人家都天天能吃得上又大又虚的白面馍,而我家却只能在自己屋里,默默无声地啃黑窝窝头,吃煮不烂的红薯干。
我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虽然我也很不想这些东西,但实在是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啊。所以,有时我能去二婶家吃这吃那,就感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二婶把我当儿子看待。
可是我家里的爹妈却顿顿只能吃这些以前都是喂猪的东西,每当我想起这事,都会在心里剧烈地翻滚,总觉得自己早晚有一天,得实现一种抱负或者是理想吧,来彻底改变自家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