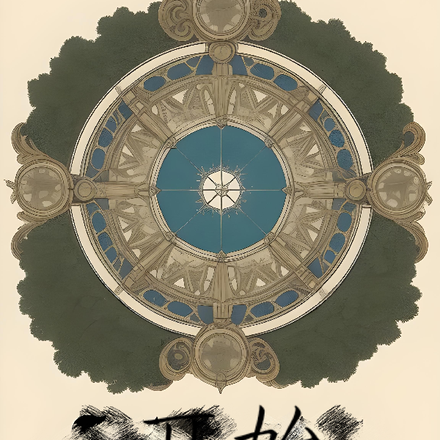身上光泽明亮,头部粗大,嘴尖尖的,有一根半筷子长,比我的胳膊还要粗。那两人一个个把这些钳出来,牢牢把着,趁着没有咬到手,就塞进了蛇皮袋里。等他们好一阵忙活,抬头看到我,对我友善地笑笑,说这是黄鳝,就是太大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西河这长年不断的流水中,还有这么大的黄蟮啊。这个头怕是一条有一两斤重吧。
后来那两个人就背着蛇皮袋返回河堤,扶起自行车,顺着河堤一路往北骑去,一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风里,我才回转身,上了东岸的河坡,慢慢走回家去。
后来,我就跟三叔说,西河里有那么大的黄鳝,三叔说我吹牛逼,死也不信。我就摇摇头,不信去球,哪天你见了就知道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天气还没有太干旱,庄上每个队里,都在每块田地上,修有机井房,和浇水用的水渠。那时,东河里每天都还淌流着丰茂的河水。
东河一直是河两岸庄稼地浇地的水源。而早些时候,石碑桥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在一次暴雨过后发大水中,那桥上的几块大青石板,还有下面垫的几条大石碑,都被水冲跑了。
后来庄上组织人打捞,当然是在水退了之后的事了。没人追究,打捞的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听说那些石碑,多是洪家坟上的,因为没有东西修桥,大队部那些干部们,就去人家坟上拉了石碑来修了桥,以方便农忙时来来往往的人拉车通过。
这个确实也方便了很多。只不过,河的上游,多是村庄排水的河沟,每逢暴雨连天的日子,这东河河水,就跟疯了似的,迅速漫上堤岸,横冲直撞地往下奔涌。
那河水恣意奔腾了好几天,才会慢慢平息。而河岸两边的杨树槐树,有的被冲跑,有的被淹了很高。洪水退后,岸边的水草上还挂着枯草和朽木屑,岸边留着清晰的水漫上来的印渍。
那是一个太阳朗照的午后,刚刚下过暴雨没几天,东河水也才退却,石碑桥边的大肚子坑里,还有半漕水,汪汪地泛着粼光。父亲背着背笼,背笼里放着老虎爪,打算去岗上红薯地里刨点红薯,再薅点红薯秧回来喂牛。
父亲刚刚走到石碑桥边上,就看到有一个木桩子一样的东西,浮在大肚子坑边的水面上,那一漾一漾的水晕,一圈圈地向边上散开着。
父亲就那么扫了一眼,没成想,那个东西竟然不是木桩子,那是一条大鱼,在水草边像是吃水草的样子。我父亲一看不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家伙,赶紧悄无声息地把背笼放下来,从里面拿出老虎爪,蹑手蹑脚地就走了过去。
那家伙竟然毫无查觉,父亲举起老虎爪,猛地往下就抓,扑的一声闷响,老虎爪的三个长长的铁钎子就扎进了那鱼的身上。没成想,那大鱼吃了一痛,头尾一个收缩,几乎把老虎爪从父亲的手里挣脱。
父亲拼命地拽着老虎爪的长把,经过一番激烈的拉据战,好不容易才把这大鱼拖到岸上。那大鱼,竟然跟家里灶屋里的桶口一样粗,跟老虎爪的把一样长,父亲拖不动,就一点一点地挪进了背笼里。
由于这鱼太大,一个人根本背不动,父亲就爬到岗上,大声往村庄的方向喊。我叔他们几个听到了父亲的呼喊,以为是跟人打架了,就都咋咋呼呼地拿着铁锨扛着老虎爪就过来了。
没想到是逮到了一条大鱼。大家手忙脚乱地抬着背笼回了家。在场院里搭起一个门板,拿一个很长的杀猪刀,一块块地把这鱼给分解了。
你家一块,我家一块,那天村上像是过年一样,左邻右舍都分到了鱼肉。天黑的时候,村庄上空就飘起了炸鱼的油菜籽油的香味……
端午节前后,小麦就慢慢变黄了。那时,村庄上空,就会时不时地飞过来几只大鸟,那鸟飞得很慢,看着很悠闲的样子。
而且边飞边很清脆地叫,碗豆多多,碗豆多多,那声音,叫得很有节奏,抑扬顿挫,此起彼伏。父母便开始准备割麦子的镰刀,磨石,米酒,还有竹叶茶。
那几天基本上都是很晴朗的,蓝蓝的天空里,偶有几片白云飘过,就是这碗豆多多那清亮亮的声音,在头顶上盘旋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听话地跟着父母,一起去地里割麦了。
無錯書吧家家户户都有麦田,一块挨着一块,田间小路仿佛是一条条尺子,把这些金黄的麦田直直地割开再重叠。常常是一大早,天还蒙蒙亮,妈叫醒我,要去割麦了。
父亲早就要院子里开始磨起来了镰刀,那一来一回的摩擦声,还有牛圈里哐啷哐啷的牛铃声,相互交错着,仿佛时钟滴滴嗒嗒的催促。
我穿着长衣长裤,脸上蒙着擦汗的毛巾,一手提着装开水的白塑料桶,一手拿着磨好的镰刀,跟在父母后面,出了院门,顺着村东沟边的土坡,往自家地里走。
天蒙蒙亮,地里已经有了瓮声瓮气的人声,有人跟父亲搭话,父亲一边应着,一边在旱烟袋里装着烟叶子,然后掏出洋火擦着了就着烟袋锅去点,嘴里吧嗒吧嗒地吸。
我跟在妈身后,高一脚浅一脚往前走。好几次,都看到路边被惊动的长虫,沿着草棵子没命地钻。那长虫有的很长,细得不得了,黄黄白白的,也不咬人,就那么像过火车一样地往地裂缝里钻,好一会儿就钻得没影了。
我常常看得心惊肉跳,父母却丝毫没当回事,也许是他们根本没看见。到了地里,妈指了指我要割的,他们各自选了几垄,就开始边割麦子边捆麦捆。
就这样,埋头干活,偶尔说几句话,不一会儿,我头上就开始冒汗,那麦地里的灰尘,带着熟悉而特有的味道就直往鼻子里钻。
割到了地中间,太阳已经出来了,满眼都是金黄的麦子,远远望村庄那高高的绿树,还有远处那整齐延伸的电线杆,还有偶尔在路上拉着架子车走过的人们。
这些,都织成了农忙收割的最好的记忆了。回头望,已经捆好的麦捆,一个个如同成熟的姑娘横卧在麦茬上,我看到,有野兔灰色的身影,在麦捆边一跳就没了影。
清清嗓子,感觉喉咙里有东西,咳了一声,吐出来一口痰,那痰过半的成分就是这麦垅间的黑灰。用手巾擦擦脸,喝一口米酒和凉开水,就又低头割麦子了。
常常能看到,麦垅间,那薄薄的长长的长虫皮,贴着地面跨过几条麦垅。我一看到这个,就轻轻地把蛇皮收起来,卷成卷,装进口袋里,往往半天下来,口袋里能装好多条。
有时,镰刀过处,也能看到白的黄的还有虎皮色的长虫,惊恐万状的呲呲地往边上爬,那个速度是非常的快,有些慌不择路的样子。
有时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癞蛤蟆,在麦垄间慢慢的爬,那个身形显得很笨拙,身上的无数的疙瘩,很是扎眼。有时能看到极大的癞蛤蟆,身上背着小小的,就那么伏在麦垅的脚印里,头往下扎着,眼睛闭着不看人。
等人割麦过去了,才爬出来,慢慢地隐在麦地里。有时,一下子就割到了鹌鹑窝,经常是窝里还有四个五个鹌鹑蛋堆成一堆,老鹌鹑受了惊吓已经扑楞一下子飞走了。
而这些鹌鹑蛋就留了下来,我从来没有去踩烂这些鹌鹑蛋,也不让父母捡回家,我一直想,等我们割完麦子,老鹌鹑会回来把这些蛋叼走的吧。
有时还能遇到尖着嘴巴满身是刺的刺猬,沿着麦垅,四脚并用慢慢地往前爬,那样子看着笑人,用镰刀轻轻一碰,那刺猬就停下来缩成一团动也不动地呆着。
等我们往前割麦了,才慢慢在展开来,身子一耸一耸地跑开去。有时能遇到田鼠,那东西,贼头贼脑地看见人就跑,跑得很快,人根本来不及抓它就没影了。
就在低头默默割着麦子时,那碗豆多多,从村庄那边慢慢地飞过来,一声声地叫着碗豆多多,碗豆多多,这时,我便抬起头看好鸟,那鸟慢慢地飞,清亮亮地叫。
我就学了它,摘了捂嘴的毛巾,用口哨吹起来,也是一声声的碗豆多多。那鸟就扭了头,慢慢地朝我们这边,边叫边飞过来。我的哨声在麦地里一声声地传出,它的叫声则在头上盘旋。
近了那鸟看着还真不小,黑黑的,头一扭一动地到处找发出叫声的东西。我不住地吹,那鸟就不停地在我们周围盘旋,而且叫声越发地清脆悦耳。这引得我父母和周边割麦的人不停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