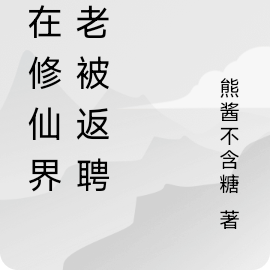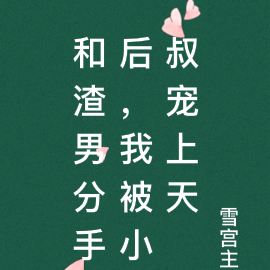第241章 棒梗留下的“大礼”
“没错!我说今天怎么没见他在院里晃荡,原来是早就踩好点,卷包会了!”
“易中海这是引狼入室啊,养了个白眼狼,把自个儿给咬死了!”
众人的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向易中海,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抽在他那张老脸上。
易中海疯狂地摇着头,那张脸涨成了猪肝色,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是一条条扭曲的蚯蚓。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棒梗那孩子改好了,这几天他多听话啊,还管我叫爸呢!他就是贪玩跑丢了,绝不会偷我的钱!你们这是污蔑!是落井下石!”
他嘶吼着,试图用声音压过众人的议论,可那声音里却透着一股子心虚和绝望。
何雨柱看着易中海这副死鸭子嘴硬的模样,摇了摇头,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一边磕一边补刀。
“一大爷,您就别自欺欺人了。那棒梗是什么货色,您心里没数?那是属狼的,喂不熟。您那钱要是还在,他能跑?他这是拿着您的血汗钱,去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了。您在这儿替他辩护,他在那儿数钱骂您傻呢。”
易中海身子晃了晃,眼前一阵阵发黑。
他不信,他不敢信。要是承认了棒梗偷钱,那就等于承认了他这下半辈子的算计全是笑话,承认了他易中海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就在这时,刘光福眼尖,指着易中海手里攥着的那团纸。
“一大爷,您手里拿的啥?那是证据吧?”
易中海下意识地想把手藏到身后,可已经晚了。何雨柱眼疾手快,一把将那纸条扯了过来,展开一看,顿时乐出了声。
“哟呵,大家快来看看!这棒梗还是个艺术家呢!这只王八画得真传神,这是留给一大爷的纪念品啊!”
何雨柱把那张纸往众人面前一亮。昏黄的路灯下,那只歪歪扭扭的乌龟显得格外刺眼,旁边还用铅笔写了一行狗爬一样的字:“老绝户,谢了。”
轰!
全院的人都看见了那行字,爆笑声、嘲讽声瞬间炸开。
这一刻,所有的遮羞布都被扯了下来。那只乌龟,那句“老绝户”,就像是两把尖刀,精准地插进了易中海的心窝子,把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搅得粉碎。
易中海看着那张纸,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他想去抢回来,可手脚却像是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何雨柱把纸条随手一扔,那纸条飘飘荡荡地落在易中海脚边,被风一吹,翻了个面,像是在给易中海磕头。
“三大爷早就说过,您这是在赌命。这棒梗就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您非要把他当亲儿子养,现在好了,儿子拿着爹的钱去逍遥快活,留个老爹在家里喝西北风。这剧情,连戏台上都不敢这么演。”
何雨柱的话字字诛心,每一个字都把易中海往绝路上逼。
易中海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纸条,脑海里回荡着棒梗那几声甜腻腻的“爸”,回荡着自己把工资条锁进盒子时的安心,回荡着自己给棒梗买槽子糕时的期待。
原来,全是假的。
全是算计。
他在算计别人养老,别人在算计他的棺材本。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还落了个全院的笑柄。
那五十块钱的赔偿,加上这次丢的全部积蓄,少说也有好几百块。那是他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来的血汗,是他在这个院里挺直腰杆做人的底气。
现在,全没了。
被那个他寄予厚望的干儿子,那个他以为能给他养老送终的人,连锅端了。
一股腥甜的气息猛地涌上喉头,压都压不住。
易中海张大了嘴,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紧接着,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在寒冷的空气中化作一团刺眼的红雾,洒落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
“一大爷!”
“老易!”
人群发出一阵惊呼。
易中海两眼一翻,身子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
那张老脸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嘴角还挂着血沫子,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夜空,似乎在质问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無錯書吧何雨柱看着倒在地上的易中海,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但眼神里并没有多少同情。
“自作孽,不可活啊。”他轻声嘟囔了一句,转头对着惊慌失措的二大妈喊道,“还愣着干嘛?赶紧叫人,送医院吧!别真死在这儿,晦气!”
夜风卷着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从易中海身上刮过,那张画着乌龟的纸条被风吹起,贴在了易中海那满是血污的脸上,显得格外荒诞而凄凉。
那一抹刺眼的猩红在灰扑扑的地面上显得格外惊心动魄,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浓重的铁锈味。
易中海这一口血喷得实在太有水平,不多不少,正好糊在那张画着乌龟的纸条上,把那只本来就歪瓜裂枣的王八染得更加狰狞,仿佛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索命的小鬼。
二大妈手里的木盆彻底拿不住了,咣当一声顺着台阶滚下来,在寂静的夜里砸出一串脆响。
几个胆小的邻居吓得往后缩,生怕这老绝户一口气上不来,直接死在当场,到时候沾一身晦气。
许大茂倒是胆子大,往前凑了两步,拿手电筒往易中海脸上晃了晃。
光柱下,易中海那张脸白得跟刚刷了大白的墙皮似的,没有一丝血色,只有嘴角那抹红还在往下滴答。
这哪是被气吐血的,这分明就是半条命都被那小白眼狼给顺走了。
易中海只觉得胸口像是被一把钝刀子来回锯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烧般的剧痛。
他想爬起来,可四肢百骸都像是被抽了筋,软绵绵地使不上劲。
刚才那一口血喷出去,带走的不光是他的精气神,还有他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最后一点体面。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像苍蝇一样在他耳边嗡嗡乱叫,每一个字都像针扎一样往他耳朵里钻。
刘海中背着手站在台阶上,大肚子挺得老高,脸上挂着一副痛心疾首却又掩饰不住看好戏的表情。
何雨柱把茶缸子里的最后一口水喝干,咂摸了一下嘴,那动静在安静的现场显得格外刺耳。他根本没打算上前搀扶,只是冷眼看着地上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