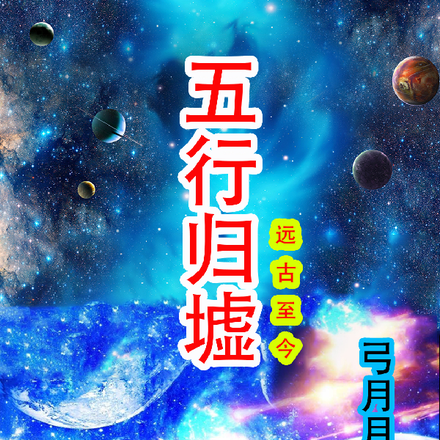第89章 难道你想【6K】
陈光蕊听到路人口中念叨的“袁大师”,心中一动。
顺着人流涌动的方向走去,果然在一处气派的卦摊前看到了被众人簇拥的额,袁大师。
眼前的袁守诚与当初在西市口躲着人算命时的穷酸模样判若两人。
只见他坐在一张崭新的紫檀木案后,身穿一袭剪裁合体的锦缎道袍,其上绣着暗色的云纹,阳光下隐隐流光。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插着一根墨玉簪子,脸上虽然还是那副风霜刻画的轮廓,却透着红润的光泽。
他原来的那个破摊子早就不见了,就看到一杆崭新的青布幌子,上面那个硕大的“卜”字都是用金线绣成的。案上不再是破竹筒,而是摆放着一个金漆的签筒,嗯,一尊小巧玲珑的金蟾吐宝香炉,袅袅青烟升起,那叫一个讲究!
围观的人群拥挤着,争先恐后,眼神里满是热切,纷纷喊着“袁大师”、“活神仙”之类的称呼。
“十贯一卦!只算十卦!先付卦金后起课!”
哦,这袁大师身边还有个小童,此时正是这个孩子在高声吆喝着,声音洪亮。十贯一卦,这价钱比长安时翻了百倍还不止。
陈光蕊算是长见识了,没想到出了长安,还是袁守诚混的最好啊,卦金都敢翻这么多了?
可即便如此,求卦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铜钱在案角堆了一小堆。袁守诚则半眯着眼睛,捋着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胡须,拿腔拿调地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富商批命:
“贵人此去东南有财,然驿马星动,需谨慎车船……”
说完了话,还滋溜溜喝了一口上好的茶水。
还是那一套,神棍味十足。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问道,
“袁大师!您神通广大,能不能帮我算算,咱这片儿,哪条河、哪个深潭里容易打到金色的鲤鱼?俺们家有头老牛,就想吃这一口鲜的。”
此时,正志得意满的袁守诚听到“金色的鲤鱼”这几个字,仿佛被蝎子蛰了一下,猛地睁开眼,捋胡须的手顿住了。他那的眼睛立刻去寻找声音的来源。
紧接着,他的目光越过了人群,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穿着朴素、却站得笔挺的人影。
刹那间,袁守诚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原本那副气定神闲的神仙架子瞬间垮了一半。显然,他根本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遇见陈光蕊,而且对方看上去还活得好好的。
他娘的,你不是应该死了吗?
袁守诚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翻江倒海。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能露出太多破绽。
他立刻清了清嗓子,脸上瞬间又堆砌起那种职业的笑容,对着挤在前面的香客拱手,
“诸位,诸位!实在抱歉,我老婆在家生孩子呢,改日再来,改日再来!”
说完,竟不由分说,也不顾众人的错愕和抱怨,急急忙忙起身,连案角的铜钱都顾不得细数,冲开人群,一把拉住陈光蕊的胳膊就往僻静的巷子里拖。
只留下了刚刚的那个小童子还在人群中凌乱。
一直拐进一条无人的深巷,确定四下无人,袁守诚才猛地松开手,转过身,一双小眼睛里满是审视,压低声音,语气又快又急地质问,
“你……你到底是谁?他不是死了么?你冒充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谁派你来的!”
陈光蕊看着袁守诚紧张又的样子,反而笑了笑,语气轻松地反问,
“你不是会算吗?袁大师,你算一算啊?”
袁守诚被这态度噎了一下,他那谨慎最终被强烈的好奇所压倒。
他盯着陈光蕊,飞快地从袖中掏出几枚油亮的铜钱,口中念念有词,手指飞快地掐算起来。
几枚铜钱落地,弹跳几下,排出一个诡异的卦象。
袁守诚看着地上的铜钱,又猛地抬头看向陈光蕊那张平静的脸,脸上的表情从狐疑变成了惊骇,像是见了鬼一样,
“你……你没死?非但没死,你还一步登天了,你身上这气息……这不可能,你怎么、怎么攀上了三十三重天那位了?”
他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显然推算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陈光蕊耸耸肩,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会算吗?自己看呗?”
袁守诚被堵得翻了白眼,没好气地摆摆手,
“得!别逗我了!三十三重天那位谁敢轻易算?他老人家一个念头下界都抖三抖,万一被他老人家察觉了……”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后果,忍不住缩了缩脖子,“那不是嫌命长嘛!”
他话锋一转,又仔仔细细上下打量陈光蕊,搓了搓手,“嘿嘿……状元公……不,该叫陈道友了?你现在可真是发达了!一步登天呐!”
陈光蕊则摆了摆手,“只是一个烧火的。”
“那也是在三十三重天上烧火的,那也不是凡间烧灶能比的。多少人八辈子修不来的天大机缘,多少神仙想贴过去都找不到门路呢,你可千万别不知足喽!”
陈光蕊只是淡淡应了句,“机缘而已。”
他不想在烧火道人这个身份上多谈,转而问道,
“倒是你,袁道长,你不是费尽心思、拼了命也要去寻找那西海龙王三太子的转世吗?现在怎么放弃了寻人,又跑到这地方摆起摊来了,排场还不小,比那泾河老龙王排场都大。”
一提到“西海龙王三太子”,袁守诚的脸瞬间垮了下去,像是泄了气的皮囊,眼中闪烁的光芒也黯淡了,深深叹了口气,,
“唉……别提了,别提了!寻他?寻个……算了,说粗话得罪佛门。我们这一脉费尽心力,祖师爷留下的推演,都算定那西海龙王三太子早已因为‘忤逆’被玉帝罚的魂飞魄散了,我们一心想捡个漏,续上祖师爷的大因果……”
他摊摊手,满脸的无奈和认命,
“谁……谁他娘能想到他没死啊?还就在鹰愁涧里好好呆着呢!他压根没死,既然没死,身份金贵得很,哪是我们这种小门小道能捡漏沾光的?没指望啦,不等啦!”
袁守诚说着说着,语气又恢复了那种混不吝的老油子调调,
“既然捡不了漏,我这把老骨头总不能白忙活吧?不如趁机多挣点钱,赚他个盆满钵满才是正经,你看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半只脚入土的人了,总该享受享受了吧?这身行头、那卦幡、那金蟾……哪样不要钱?”
他瞥了一眼陈光蕊,似乎在观察对方的反应,然后主动探询道,“陈道友,你不在天上清净,跑这穷乡僻壤来做什么?”
看到陈光蕊的眼神,袁守诚直接摆手,“好好好,我自己算。”
他又一次习惯性地掏出铜钱,口中念念有词地算了起来。
片刻之后,他收起铜钱,脸上露出一种极其困惑的神情,眉头紧锁,疑惑地看着陈光蕊,
“怪哉……老君这次派你下凡,我算出来与你那次进老君观,被他老人家亲自召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
他顿了顿,更加不解地问,“你既已下界,那就是天上那位传的旨意,你不好好去做,为何又对那两个童子做的事情袖手旁观?任凭他们胡闹,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陈光蕊一脸坦然,语气毫无波澜,“老君吩咐得很清楚。我只需要在旁边观察,确保没有别的势力插手两个童子做的事即可。其余的,有金炉、银炉两位童子主持,哪里需要我这‘烧火的’多嘴?”
他语气里带着一丝自我调侃。
袁守诚显然不信这套说辞,撇撇嘴,“哼,说得轻巧。那两个小娃娃懂个屁?”
“懂不懂,那也是老君座下的童子,随身还带着羊脂玉净瓶那样的宝贝呢。”
陈光蕊平静地说,“我刚上天几天?那两位童子跟了老君多少年?人家说不定每天都能见到老君他老人家请安回话。我呢?说不定几百年也未必能近前一次。在这种事上与他们冲突,实在没这个必要。”
他显得非常清醒且务实。
袁守诚听了,沉默片刻,眼珠滴溜溜地转了几圈,似乎在消化陈光蕊的话。他并未点头称是,手指却又下意识地开始掐算,显然习惯性地想再窥探天机。
很快,他猛地抬眼,小眼睛里闪着精光,像是突然抓住了关键,压低声音道,
“我看不是不敢插手!你是早就算定了……不,是猜定了这事儿不好办!那两个童子靠不住,办不成!所以你在这儿冷眼看着,等着他们撞了南墙,回来求你帮忙?”
陈光蕊闻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意味深长地反问道,
“袁道长,你既然能算到这一步,那你再算算,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连你这一脉费尽心思都能看透几分……你觉得,以老君他老人家的神通,他能算出来吗?”
袁守诚被这个反问噎住了,脸上的精明神色僵了一瞬,随即变得有些心虚。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脯,声音却不自觉地低了几度,带着点色厉内荏的味道强调,
“不…不一样!这怎么能比?我们这一脉是拼着天谴才敢窥探这些事!这是拿命在算,他们呢?坐在天上俯视下界,掐指一算,什么都不用损失就想知过去未来?那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没有这样的道理。”
但他越说越觉得没底气,声音也越来越小,最后讪讪地补充了一句,像是自我安慰也是警告,
“而且……要说这天上地下,真正能把一切算得明明白白,连一粒灰尘都不错的……我敢说绝对超不过五指之数,其他的,谁都不行。”
虽然猜测这天上也有能人,
“但是,他算别人,别人也在算他,算人者人恒算之。算着算着,就乱了。天机迷雾重重,相互牵绊干扰,谁都不敢说自己算的一定就对?就像我们这一脉,算了那么久,不也算错了西海三太子生死吗?还差点扑了个空。”
他像是找到了例子证明自己的理论,说得愈发溜了,
“再比如老君那么厉害,不也有跟燃灯古佛聊个天,转个身的功夫,连带着整个兜率宫的丹药都被那猴子偷了个遍的事?所以说啊,这天机变数太多,不是谁厉害谁就绝对能掌控一切的!”
他这话里明显有为自己“算不准”开脱的味道。
他顿了一下,带着点好奇和提醒的意味,斜眼瞟着陈光蕊,
“话说回来,你现在都攀上老君这艘大船了,还敢去招惹五行山底下压着的那个泼猴?你的胆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啊,老君可不怎么喜欢这猴子,你不好好的去帮那两个童子,天天就在这边转悠,怎么?难道你想……”
陈光蕊没等他把那个可能的答案说出来,直接截断了话头,抛出了自己新的问题,
“既然你知道了五行山,那就应该清楚那边的情况,你能算出来五行山那里,现在是谁在看守那只猴子吗?为什么我进山去见那猴子,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出来拦我一下?”
陈光蕊目光灼灼地盯着袁守诚,
袁守诚一听“五行山看守”、“佛门”这几个关键词,刚才还侃侃而谈的脸立刻绷紧了,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嘿嘿嘿,陈道友,这可不行,这绝对不行,你这不是害我嘛,牵扯到佛门、牵扯到那猴子的事情,那就是一滩浑水!深不见底!这些事是不能随便算的!要折寿的!不算不算,这次给多少钱……呃,给多少?”
听到袁守诚的话,陈光蕊却笑了,那笑容着实让袁守诚看了有些心慌。
“袁道长,你那心心念念的西海龙王三太子……是叫敖烈吧?”
陈光蕊不紧不慢地说,“就压在鹰愁涧底下的那个?当初,这条龙的下落,你说找不到线索,非得求我。现在嘛……我倒是觉着,把他弄出来这件事,你还得求我。”
袁守诚那双小眼睛“噌”地瞪圆了,他下意识环顾四周,生怕被人听见,接着又死死盯着陈光蕊,脸上满是怀疑已经很浓了,
“你小子……诓我的吧?天上掉馅饼也没这么掉的!你刚还在打听看守猴子的事儿,转脸就有办法放了人家龙王三太子?当我三岁娃娃耍呢?”
陈光蕊脸上的笑意淡了些,带着点嘲讽,
“诓你?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你是怎么从长安城躲到这西牛贺洲地界来的?没我给你指那‘向西’两个字,你这会儿还在两界山附近当没头苍蝇呢!我陈光蕊什么时候空口说过白话?”
这话戳中了袁守诚的软肋。他确实是被陈光蕊一句“向西”指引,再加上“两界山”的模糊方向才慢慢摸到这边,确实在附近找到了更多的线索指向鹰愁涧的西海龙王三太子。
他顿时被噎住,脸上的精明已经褪去大半,他上下重新打量着陈光蕊,那眼神,嘴里还念叨着,
“这次,怎么感觉跟上次一样呢?”
“……行!我……我信你一次!”没有办法,袁守诚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终究是抵不过“西海龙王三太子”这几个字。
想到三太子的诱惑,压低声音,干脆利落地说,
“你进山见那猴子,没神仙拦你?这事儿我知道!看守他的五方揭谛、土地、山神,一个都没出来,对吧?”
陈光蕊点头,这正是他想问的。
袁守诚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透着点幸灾乐祸,
“嘿,哪有什么仙规森严、恪尽职守的事和人?那是佛门派去看守猴子的人,时间长了,几百年了,谁能不出点岔子?神仙也一样的!”
他脸上露出“你懂的”那种表情,
“我算不到太细的因果,但知道个大概。就在前几天,那五方揭谛,不知道为啥事,把那倒霉催的土地公和当地的山神给狠狠揍了一顿,兴许是看守不利?也可能只是脾气上拿他俩撒气?反正,打得那俩家伙现在都缩着不敢冒头呢。”
“你以为五方揭谛为啥不管那猴子了?”
袁守诚啧啧摇头,“他们打完了人,大概是觉得气顺了,也想着歇歇。又觉得反正有土地山神在下面看着猴子呢,就……偷懒去了,而那俩被揍的心里有气,又不敢对五方揭谛发作,也跟着摆烂,根本没去管猴子。”
他两手一摊,“嘿,这就有趣了,谁都以为别人在干活,结果都没干!所以你一去,嘿,赶上好时候了,畅通无阻。你想打听谁在看守,怎么联系?别费那劲了!”
陈光蕊想一想,“看来,只有先找到五行山附近的土地山神再说了。”
袁守诚脸上的幸灾乐祸立刻被一种谨慎取代,
“联系土地山神?趁早歇了这心思。今天这事能被你撞上一次,是你小子祖坟冒青烟,走了大运。”
“要知道五行山那边是佛门看守猴子最关键的一环!今天这漏洞,明天就会被补上。你要是傻乎乎主动去联系他们,他们都是佛门的人,”
“你找他们,那不是明摆着告诉佛门:‘喂,我知道你们的看守有漏洞了,我钻过!’这不是找死吗?佛门马上就会知道有人惦记那猴子,第一个盯上的就是你!”
陈光蕊听完,眉头微蹙,随即又舒展开。确实,第一次进山没被阻拦是天大的运气,但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强求只会招祸。
“既然这样,”陈光蕊神色平静,“那这个路暂时是走不通了。只能等机会了。”
“等机会?”袁守诚好奇地问,“你要去哪等机会?”
“去哪?”陈光蕊整理了下身上的衣袍,露出一个笃定的笑容,
“当然是回李靖李大元帅的行营。别忘了,我现在可是领了行军记室官职的大唐官员。我的‘正事’在军营里。”
他刻意在“正事”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袁守诚一听“李靖”、“行军”这几个字,那点算命先生的直觉立刻冒了出来。他掐着手指头,眉头越皱越紧,嘴里念念叨叨,
“不对劲……不对……李靖的大军……”
他猛地抬头,看向陈光蕊,
“你小子别光顾着看天,也看看脚下成不?老道我虽然算不透佛门那种浑水,但这行军打仗,牵扯些凡间因果,还是看的很准的,你跟着李靖走,恐怕会有危险。”
陈光蕊挑眉,“危险?别的我不好说,李靖这次出征。肯定赢的。”
“李靖用兵如神不假!按常理,稳扎稳打下去,那突厥兵败是板上钉钉!”
袁守诚的小眼睛闪着担忧,“可他娘的,问题就在这不正常上!我算出,突厥那边,怕是……沾上了妖怪。”
“妖怪?”陈光蕊眼神一凝。
“对!黑气缭绕啊!”袁守诚用力点头,手指指向远方那片连绵起伏、看着就有些不祥的黑色山脉,
“要是我猜的没错,李靖恐怕会走黑风山那条路。”
他脸上堆满了“别去送死”的表情,语气急促,
“黑风山啊!那不是普通山头,那山里可是有妖怪的,李靖的军队再精锐也是凡人,万一突厥兵跟山里头的妖物勾搭上了,来个里应外合,或者是来个偷袭……嘿嘿,那可就热闹大了!再神的名将,遇上不讲理的妖怪手段,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你别不信,老道我这感觉灵验得很!”
袁守诚看着陈光蕊,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李靖的大军现在那就是个大靶子,你要是过去,说不定就是送死了。
然后,袁守诚好像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多了,就不再说了,而是笑呵呵地向着陈光蕊那边凑了凑,
“那个,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办法把那个西海龙王三太子给放出来?这个事,是怎么个说法来着?”
“西海龙王三太子?啊!对啊,我是这么说的。”
陈光蕊为人正直,说过的话从来不会不认。
“那个……”袁守诚让自己的态度尽量好,“要不你先把这龙太子放出的办法告诉我?”
“啊!你说这个啊!”
“啊!对对!就是这个。”袁守诚眼中带着希翼。
谁知道陈光蕊摆了摆手,“这事以后再说。”
“哎我说,小子!你是不是又把我当成鱼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