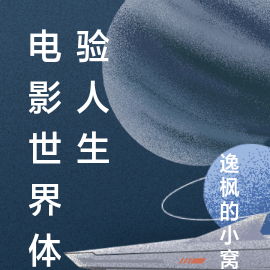实际上,石明香看中罗七的,不是罗七的风度,也不是罗七的气质,她倾慕他口袋里那六七万块钱,有了这笔钱,可以在广州城吃喝玩乐几年。她不能在罗七面前显示自已的虚荣和好吃懒做的本性,她要牢牢把罗七捆住,听从自已的安排。
石明香知罗七已经进入自已的圈,要开始行使享受自已的战利品的权利了。她尝试着要罗七给自已买一个高档包,罗七毫不犹豫满足了她的需求欲望。
有了第一次的成果,石明香故技重演,接二连三得到了自已想要的化妆品和金银戴坠,她再提出非分要求时,罗七迟疑了。他不是舍不得,而是这几天的赌运并不顺利,几乎都有拿出去的,进来的很少。所以石明香又要一件法国香水时,罗七不耐烦了,道:
“这两天运气不好,输了很多,待几天后时来运转,赚了大钱,我自会犒劳你的。”
石明香翻开罗七的衣带检查,见里面的确只有一万多块钱了,这才收敛强烈的占有欲。软绵绵躺在罗七怀里,撒娇卖萌。
石明香心里虽不悦,但也知道不能逼得太紧。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亲爱的,既然赌场运气不佳,咱们换个赚钱法子呗。”罗七疑惑地看着她。石明香接着说:“听闻城西有个斗蛐蛐大赛,奖金丰厚呢。”罗七心动了,觉得可以一试。
于是两人来到城西。罗七精心挑选了一只蛐蛐,信心满满地参赛。然而事与愿违,他的蛐蛐连连败退。这时罗七才意识到,自已对斗蛐蛐根本一窍不通,只是听石明香几句怂恿就冲动而来。
罗七又来到朱家赌场,希望在这里能够翻本。可是今天手气依旧很差,没几个回合,他剩下的钱也所剩无几了。石明香在一旁干着急,不断催促罗七下更大的赌注,想一把捞回所有损失。罗七被她说得心烦意乱,头脑一热,将最后的钱全部押了上去。结果毫无悬念,罗七输得精光。
罗七抓耳挠腮,想办法找赌资,要翻回本钱。他瞟了自已外面的轿车一眼,对值班的冬至道:“去请朱爷来,我有事求他。”
冬至不敢怠慢,上楼去告诉朱爷,说罗七有话要说。朱爷知道罗七肯定输光了,要找自已借钱。故意迟疑了二十多分钟,才慢吞吞从楼上下来。
“小老弟,有何贵干啊!”朱爷道。
“朱爷,我明人不说暗话,输光了,能不能周济点,翻个本儿,才有玩的。”
“不瞒老弟说,这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上次你大闹本娱乐室以来,玩的人已经很稀疏了,我一天开资这么大,现在实在是没有钱借你啊!”朱爷做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道。
罗七知今日朱爷是不会借钱给自已的了,因为干这行的老板很会识人气,一个赌客运气来了,红光满面,即使输了,没有本钱,也会借钱给他,一两天之内就能翻本。而今的罗七,额头晦暗,身体疲软,长时间内根本缓不过好运来,故朱爷必然推辞。罗七见朱爷拒绝借钱,手指外面的轿车,道:“用这个抵,你你能出多少钱?”
朱爷喊自已的春夏秋冬四个心腹去看看车,能值几个钱。四人看了看,不约而同伸出三个指头,表示只值三万块钱。朱爷对罗七道,你这辆车他们四人估价只值这个数,你愿意卖,交钥匙,然后我让凑钱给你。罗七此时也没有办法,只得拿出车钥匙递给冬至,朱爷让冬至开车进停车室,拿了三万块钱,交给罗七。
此时的东家是个白脸、留着小胡须的中年人,看样子就是个经历过赌场中磨炼无数的高手,只见他两手拿着一副新扑克,一挤,牌就像离弦之箭,相互交叉而去,摞在一起。
白脸开始发牌,每人三张,今天的赌家是,一个兔裂口补过的年轻人,小白脸和罗七,三人面前摆上了三万块钱,看来今天罗七要孤注一掷了。
白脸发完牌,并不急于看,眼睛死死盯着罗七,看罗七的一举一动。罗七也不看牌,只说了句:“焖。”丢五百块钱进场,兔裂青年看了看自已的牌,道:“不跟,丢。”
轮到白脸了,只见他不慌不忙,道“继续焖。”说完,捉两千块钱丢进场子。
罗七也不示弱,抓了五千块丢下去,也道:“跟。”
眼看面前赌资只有两百块钱了,罗七才拾起三张牌,仔细端详到底是什么牌数,只见是三张红桃A、黑桃A、方块A赫然排列,罗七顿时心花怒放,旁边的石明香更是惊叫起来,喊道:“撬,可以撬了。”
撬牌需要翻倍的数,刚才白脸焖鸡时放的是一万块钱,现在必须要两万才能撬。罗七看了看石明香,石明香掏出自已的私房钱两万丢下场子,就要去撸钱。
只听白脸大声喝道:“慢,我没有翻牌,你怎么这样心急就要拿钱?”
白脸不慌不忙一张一张翻开自已的牌,旁观者齐声大呼:“2,3,5!”
罗七见状,瘫软在地;石明香呆若木鸡,张大的嘴合不下去了。
原来,翻金华牌规定,2,3,5通杀一切豹子。完了,完了,罗七突然失去理智,起身抢向赌桌,抓起钱就想往外跑,朱爷大怒,喝道:“阻住,不要让他跑了,报上次大闹赌场之仇。”
春华、夏崽、秋波、冬至、白脸及三十多人冲上前去,将罗七和石明香团团围住。罗七虽懂些拳脚,怎能打得过几十人的狂打乱踢?片刻功夫,罗七被打得鼻青脸肿,晕了过去,石明香则被强行拖走了。原来这一切尽是朱爷精心安排的,他要报复罗七上次害他名誉的人。
半夜,罗七醒来,发现自已躺在一个垃圾坑里,痛苦的拍拍身上的泥土,向周边看了看,繁华的街头变成了萧条的农村模样,有几只狗在向着自已狂吠。罗七明白,自已被打晕后,被拖到郊区来了。
忽然感到肚子饥饿,摸摸身上衣带,在内衣袋里还有一百元,罗七拖着疲惫的身子往村里走去。看到一家狗肉馆还在经营,店里飘出肉香,让他更觉饥肠辘辘。
罗七走进了店。老板是个精瘦的老人,看到罗七狼狈的样子,眼中闪过不屑的光芒。罗七要了一碗便宜的面,边吃边和老板闲聊起来。老板说这家店其实快经营不下去了,主要是狗资源少了。
罗七问这样的狗肉店一天能卖几只狗,老板狡黠地问罗七:“看样子,你是落魄外地的吧!我不想瞒你,如果有狗的话,一天卖过千把块钱的,像闹着玩的。”
罗七眼睛一亮,咸鱼翻身的事一下子向他袭来,他打算在农村搞狗卖给老板,获取赌资,去把自已输掉的赢回来。
罗七吃完面,忍着剧痛,走出店门,找一堆稻谷草,扯些铺上,躺下休息。这时一只土狗闻味而来,大声叫唤。罗七骂道:“是你自找苦吃,自已送上门来了。”猛然一扑,两只手抓住狗的前腿,奋力一掼,那狗嗷嗷叫了两声气绝身亡。罗七背着狗来到刚才卖狗肉馆子,对老板道:“缺狗,这不是吗?”
老板压低声音道:“有人看见没有?”
“半夜三更的,谁能看见?给多少钱?”
老板衡量了狗的重量,道:“四十斤吧,给你四百块钱。”罗七没有喊价,点头同意。
老板看罗七有胆有识,拉着罗七进内屋,道:“以后你只要搞到狗,只要没有人发现,你尽管卖给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罗七点头答应,要求在狗肉馆老板家休息半夜,老板同意,让伙计安排罗七一道去睡。
第二天,罗七起床,买了碗狗肉面吃了,去找诊所看了看被打伤的皮肉,贴了几个药膏,吃了几颗三七和两瓶云南白药,然后搜索农村狗的人家数,一一记在心里。
罗七找了一棵细小的钢丝绳,放在竹筒上,留有狗头大的圈儿,用树桩、石头做试验,套上使力一拉,反反复复练了多回,感觉熟练了,晚上便开始了偷狗行动。
罗七来到一个偏僻处,将事先准备好的肉坨丢给贪吃的狗。那狗开始显得害怕,后来经不住诱惑,离罗七越来越近,说时迟那时快,罗七的钢丝绳套住了狗脖子,再一拉,狗挣扎两下,叫都没有机会叫两声,便一命呜呼了。狗肉老板很高兴,马上现钱现货,交易完毕。
此后的日子里,村子里的狗越来越少,人们都知道与狗肉老板有关系,但又找不到证据,所以也没有人敢对狗肉老板怎么样?
本村的狗基本被罗七盗光,罗七下一个目标就是邻村。去邻村偷狗,没有交通工具,一旦被抓住,比在赌馆里挨打还要厉害。城市赌馆懂些法律,知道打死人会被追究,而农村人就不同,被抓住,重者丢命,轻者痨伤,这辈子休要站起来走路。罗七想到这,决定搞一辆摩托车。
罗七进城买二手摩托,路过一个村庄,发现一个骑嘉陵摩托的干活回家吃饭,车停了,却忘记扯钥匙,罗七见了,灵光一现,轻脚轻手跨上摩托,飞也似跑了。摩托车主出来,哪还有车子的影子,只得自认倒霉。
罗七有了交通工具,一夜能给老板提供三五只狗的货源,自已也能赚一千多块钱。罗七想,这事虽是犯法,但钱来的快,比卖苦力和看人脸嘴生活自由自在快活的多了。
此后的日子里罗七继续肆无忌惮地偷狗。然而,村民们也察觉到了异常,各个村落纷纷组织起了巡逻队。
一天夜里,罗七如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潜入邻村。正当他锁定目标,抛出诱饵之时,隐藏在暗处的巡逻队员迅速围了过来。罗七惊恐万分,发动摩托车企图突围,却不小心冲进了田地里,连人带车摔倒。村民们一拥而上,将他绑了起来。
罗七被拉进一个晒场里,愤怒的农民手持木棍雨点般直往罗七身上落下,只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
面对暴怒的村民,罗七苦苦哀求,但这次没人同情他,拳脚不停不断狠狠狂击,不久,罗七昏死过去。
村民提冰水泼醒罗七,村长决定把他送到派出所。
罗七这下彻底慌了神,他深知一旦入狱,不仅自由全无,名声扫地,而且再也无法重回赌场翻本。但他已无力改变局面,只能被众人押送着缓缓走向未知的审判。此刻,他满心懊悔,后悔自已走上这条邪路,可为时已晚。
派出所根据罗七所犯下的罪行,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罗七盗窃罪,三年有期徒刑。
罗七被押往劳改农场第一天,有个牢头就盯上了他。牢头想在新人面前立威,好方便日后管理。于是牢头带着几个手下,走到罗七跟前。
“小子,新来的就得守规矩。”牢头一脸横肉抖动着。
罗七刚想辩解,牢头一脚就踹了过来,“你敢打我?”罗七侧身一闪,躲过了牢头的一脚,翻过身,岔开五指,在牢头脸上就是两耳光。其他犯人看到这一幕,有的幸灾乐祸,有的默默低下头不忍直视。
牢头大怒,招呼心腹上前狠狠教训罗七。罗七左手掐住牢头脖子,喝道:“我看谁敢上前。”
心腹见状个个都呆住了,不敢乱动。
罗七挥着拳头,左右开弓,狠狠击打牢头,他要把对打他村民的怨气发在牢头身上,牢头见没人帮他,只得求饶。
牢头蜷缩在角落,罗七仍不罢休,继续狂揍。
“住手!你们在干什么?”监狱长大声呵斥。
罗七立马换上讨好的表情,“他不问青红皂白,见我就打,我只有反抗了。”
监狱长皱着眉头,“这里是改造人的地方,不是让你们打架斗殴的场所。”随后让人把牢头带去医务室检查。
自此,罗七在热带农场里改造,没有一个犯人敢来欺负他,他也不欺负其他犯人,各自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