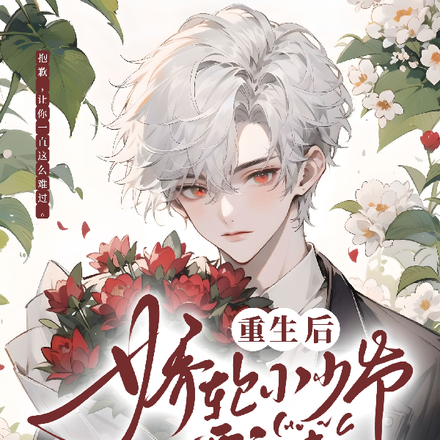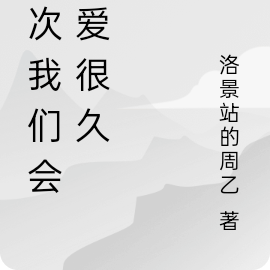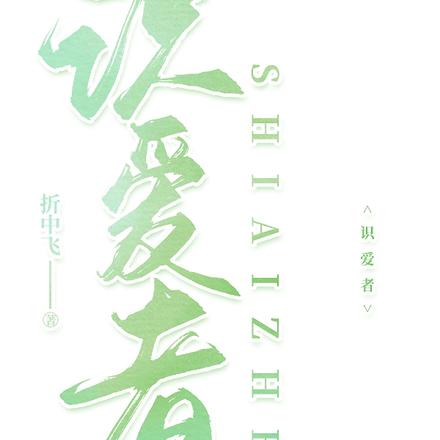第24章 阿秀的父母
魏迁随着炊烟的方向走去,越接近,那烟雾就越浓,如同一条条灰色的龙在天空中游弋,指引着他前行。
当他到达炊烟脚下,面前展现出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遍地是密密麻麻的棚屋。
这些棚屋像是突然间从地里冒出来的小蘑菇,它们零乱而拥挤,彼此间几乎没有任何间隙,仿佛是在竭力挤出生存的空间。
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木头、泥土和食物的气味。
距离魏迁最近的一间棚屋,有一个忙碌的身影上。
那是一个年纪约莫三十的男子,皮肤雪白,肌肉线条明显,显然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痕迹。
他正弯腰驼背,小心翼翼地用几根木棍和破旧的布料搭建着一个简易的棚屋,动作熟练而迅速,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
“这位大哥,打扰了,”魏迁走上前,礼貌地开口,“请问这里是哪个村子?”
男子抬起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便露出友善的笑容。
“这里哪有什么村子,我们是山上矿场的,只是暂时扎营在此。”
魏迁接着问,“我正从草海山上下来,矿场一个人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这男子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活计,找了个干净点的地方坐下,魏迁也跟着坐了下来。
“前两天,矿场的管事突然下令停工,说是上面有命令,具体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我们都被赶了出来,走得急,连东西都没拿齐。”
“那你们怎么又聚集在这里了?”
“唉,”男子摇头苦笑:“我们这群人,在矿场上干了数年,身子骨都快散架了了。
有的人想着在此处好好休养一番;
有的本就是无家之人,矿场没了,也就没了去处;
还有的,听说家里遭了战火,亲人离散,无处可归,只好又聚到了这儿。
我们这些人,就像是被风吹落的叶子,落到哪儿算哪儿。”
魏迁闻言,心中五味杂陈。
他看着眼前这男子,看着这片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屋群,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和飘零感。
魏迁接着问道:“请问大哥,此处可有中营县的人?我有些事情想要打听。”
男子摇了摇头,回答说:
“中营县?这个地方我没听说过。这里的人员好几千,伤病的、残疾的都有,每天都有人来有人走,人员轮换得厉害,你不如进去多问些人,说不定有人能知道。”
“好的,多谢。”
魏迁谢过,从怀中掏出了昨日在酒楼结余的几块碎银:
“大哥,这点银子您收下吧,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魏迁说着,将银子递给了对方。
“使不得,使不得,这哪里用得着,”男子连连摆手,不似客气模样。
魏迁态度坚决,他执意要把银子
这男子无奈,只拿了其中的一块碎银,再三谢过。
魏迁微笑着向先前帮助他的李三告别,然后开始在人群中穿梭,试图找到任何与中营县有关的线索。
他逐一询问,从棚屋的入口到角落,几乎问遍了大半个区域,但得到的回答总是摇头或茫然的眼神,令他心头的希望逐渐冷却。
“难道,阿秀的父母已经离开了?”魏迁心中暗自揣测,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他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宛如沙漠中的一泓清泉,让他瞬间振作。
“这位小兄弟,你可是在找中营县的人士?”
那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声音略带沙哑,但眼神中却闪烁着一种洞悉世事的睿智。
魏迁立即停下脚步,转身面向她:“正是,我从中营县黄途村来,受人所托捎来一份口信。这位大姐可知道什么消息?”
那女人点了点头,她的脸色苍白,显然是长期在地下矿场工作,不见阳光造成的。
她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棚屋,说道:“我认识个工友,是中营县黄途村人,我带你过去。”
魏迁心中一喜,这突如其来的转机让他感到无比激动。
“多谢大姐!”
他感激地说道,随即从怀中掏出一块碎银,递给了那女人。
那女人,她没有推辞,而是坦然地收下,接着提醒魏迁:
“他一向开朗,为人热情,只是最近他妻子刚病逝,心情不太好,可能话有些少,你多担待。”
“不过,也许见了家乡的来人,他会振作些,”大姐轻轻一叹。
魏迁心中有一股不妙的感觉,中营县黄途村的夫妻,这......
魏迁跟随着这位大姐,穿过狭窄而蜿蜒的小径,拐过十几个棚屋,最终停在了一间格外简陋的屋子前。
这屋子看起来比其他棚屋更加破败,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散。
门前,一位中年男子静静地坐着,他的脸色也是煞白,看上去憔悴不堪,不知是哭过还是太久没有睡的原因,双眼布满了血丝。
而这男子的面容,让魏迁心中一震。
他的眉宇间透露出的气质,以及脸型轮廓,无不与阿秀惊人地相似。
就像是镜子里的倒影,只是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更深的痕迹。
魏迁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阿秀的父亲。
魏迁转头问身旁的大姐:“就是他?他的妻子前几天刚病死了?”
大姐轻轻地点了点头,眼中的神色充满了同情与惋惜:
“是啊,眼瞅着就可以回家了,结果……”
她的话语中带着叹息:
“两个人感情一向很好,相依为命,听说家里还有个女儿,他也就是靠着这个念想活着吧。”
魏迁听罢,心中五味杂陈,不禁有些慌乱,他犹豫起来,开始怀疑自已是不是该上前。
这大姐带着魏迁来到屋前,她对坐在门口的中年男子说道:
“大哥,这位小兄弟在找中营县的人,我记得你是那儿来的人,所以我就把他领过来了,看能不能帮上忙。”
说完,她从怀中取出那块碎银,塞到男子手中,轻声道:
“这银子你拿着,是这位小哥的问路费。”
中年男子原本眼神呆滞,但当他听到眼前之人是从中营县来时,突然间仿佛有一股力量注入他的体内。
他抬起头,望向魏迁,尽管声音依旧有气无力,但那双眼睛中却闪烁着一丝希望的光芒:
“小兄弟,你从中营县来?那里现在怎么样了?”
战乱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四面八方,即便是这几近与世隔绝的矿场,人们也或多或少听闻了外面世界的动荡。
魏迁犹豫了一下:
“中营县现在已经无事,部队开拔到别的地方了。”
他温和地说道,尽量让自已的语气显得轻松一些。
中年男子听后,神情放松了一些。
魏迁试探性地问。
“大叔,你可认识黄途村的村长一家?”
男子一听,瞬间精神焕发,仿佛被电击一般,眼中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你是谁?我就是黄途村村长家的。”
他激动地说道,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和紧张。
“那正好,我受阿爷的嘱托,来给你们捎个口信。”魏迁回答,眼前之人确实是阿秀的父亲没错。
“我爹还好吗?阿秀呢?”中年男子迫不及待地问道,他的双手微微颤抖。
魏迁微笑着说道:“你放心,都好。”
见魏迁这般说,中年男子的脸上掠过一丝宽慰。
“是这样,去年冬天黄途村的日子不好过,饿死了不少人,”魏迁缓缓道来,“幸好,有个路过的大户人家老太太看上了阿秀,将她买回去当个丫头,如今应该是不愁吃喝、衣食无忧的。”
“而阿爷还有黄途村不少人,都跟着义军上了前线,做些后勤的轻松事情。”魏迁继续说道,“他怕你们回家找不到人,所以托我来捎个口信,还有那户人家买阿秀留下的银两。”
说着,魏迁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了那张银票,这是昨天在酒楼结账时找回的,一张价值五百两的银票。
“五百两?”
阿秀的父亲和身旁的大姐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银票,他们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一个小姑娘能卖出五百两?”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声音中充满了震惊。
“大叔,这个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有钱人,”魏迁解释道。
“五百两……”阿秀的父亲再次喃喃自语,眼中闪过复杂的光芒。
他脸上的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最初,他的表情中满是伤心,毕竟女儿被人买走,对于任何一位父亲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事实。
但紧接着,他的眼神中闪烁出一丝欣慰,至少,在大户人家中,阿秀不用再忍受饥饿的折磨。
在古代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其生活水平可能远远超过普通百姓。
对于阿秀而言,能够在大户人家中做丫鬟,虽然身份地位并不高,但却能享受到相对稳定的生活,远离了黄途村的饥荒与苦难。
可他又想到从此以后,和女儿难再见一面,又陷入恍惚。
他看向魏迁,心中充满了感激。“小兄弟,谢谢!”声音已是有些哽咽。
魏迁笑了笑,轻轻拍了拍阿秀父亲的肩膀:
“大叔,这是阿秀的福分,不是谁能强求来的。”
阿秀的父亲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期盼与好奇,问道:
“小兄弟,你可知道这户人家姓甚名谁,府邸在何处?”
他心中似乎在盘算着,将来是否有那么一天,他能够去看看自已的女儿,哪怕只是远远地望一眼,确认她过得好。
“大叔,大户人家的规矩,不让人知道太多,否则天天有人上门受得了?”
魏迁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解释着,希望能够缓解阿秀父亲的期待。
如果透露出太多细节,可能会给阿秀的父亲带来不必要的幻想和失望。
一旁的大姐也插嘴道:
“大哥,你女儿以后可就天天不愁吃不愁喝了,伺候人总归是安稳的差事。”
她的话语中带着羡慕与欣慰,仿佛是在提醒阿秀的父亲,阿秀能够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做丫鬟,比起许多同龄女孩,已经是幸运的了。
阿秀的父亲听着这些话,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这泪水,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绪——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对再也见不到女儿的悲伤,也有对阿秀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欣慰与释然。
魏迁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切,心中同样五味杂陈。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默默地俯身拱手,向阿秀的父亲示意告别。
随后,他大步离去,心中没有一丝此间事了的如释重负,反而觉得胸口仿佛压着一块石头,沉重而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