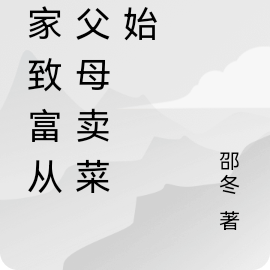“一班的人又闹事了?”
“正常,他们三天两头就打架……”
“因为有人总是英雄救美。”
教室外的走廊有人在罚站,男孩双手插兜,散漫地背靠着墙,仿佛被罚的人不是他。
就算这般,他依然是众人环绕的中心。
初中的祁肆很叛逆,温文尔雅这个词,与他沾不上什么边,他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善心,全给了那女孩。
那女孩是他的同班同学,但他整整三年也没记住对方的名字,或许有印象,但他没那么在意。
两人成为同桌后才有交集,她性格懦弱,胆小如鼠,总是会被班上的人欺负。祁肆不是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某次看见她扎着两个丸子的头发被人扯住,他的内心还是动摇了。
谁也没想到祁肆会动手,他不知道的是,那群人对待女孩的态度更加恶劣,女孩只能缠上他。
所有人都说祁肆喜欢那个女孩,就连那个女孩也误会了,之后的之后,他总能收到她的各种礼物。
其实,他只是见她可怜才出手。
跟人打架的次数变多,饶是他成绩再好也抵不过去,老师劝他不要动不动就惹事,可他没办法。
如果那些人能不找麻烦,他就此罢休。
祁肆没有辟谣他和女孩的传言,他明白如果说出来,女孩的下场只会更惨,所以他不作回应。
毕业那天,女孩单独约他到操场聊天。
“初中三年你帮了我太多,我想对你说声谢谢。”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可我太害怕了,我那时只想找个人寻求庇护,而你愿意帮助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很感激。”
“还有一句话,我想说出来。”
“我喜欢你。”
祁肆耐心听完了她说的话,女孩也知道自己是一厢情愿,留下话便离开,从此两人再不相干。
他的叛逆期很短,成长得太快,也变得太快。
以至于上高中后,他的性子愈发收敛起来,变得温和待人,心却冷起来,对外界漠然置之。
再看到被人欺负的女生,也只会无视。
这些事,与他何干?
祁肆习惯了那些女生的目光,从未正眼回应,除了认真学习,其余的事他都不关心。
高中三年,甚是无趣。
他考进全国前几的医科大学,选了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在本地的中心医院就职。
祁肆是普外科医生,每天工作繁忙,查房看病人开医嘱,然后再上手术,不停地上手术,值班室休息。
他的生活忙碌,没有时间谈恋爱。
祁肆被父母催着相过亲,女方很满意他,两人有试着相处过,但因为他严重洁癖,几欲离开。他礼貌结束了双方接下来的计划,开诚布公地回绝掉女方的心意,然后删除联系方式。
之后,再也没相过亲。
祁肆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如果谈恋爱让他感到负累,他会果断选择摒弃,因为他需要的是理解。
换一种方式说,他不愿让人轻易打破自己的天平。
他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也爱美人,不是字面上的美人。
有时候,他更愿意独处,但他也讨厌孤独。
时间于他来说就是一个计数器,不断增加延长,而某天,有人扰乱了这个机器,让他故障重修。
祁肆走出手术室时,口罩还没摘下,但他老远便听见救护车的警报声,没多久推车从他身边急促而过。
他看到躺在上面的人浑身是血,比她身上的红裙还要鲜艳,长发遮住了她半边脸,祁肆看不清。
那一瞬间,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等到推车从他眼前消失,祁肆才恢复正常,奈何生离死别,世事无常,按理来说他早该看淡。
祁肆推了推眼镜,只当自己医者仁心。
他收起那廉价的怜悯,心想世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人,总不能事事为之惋惜,从而悲天悯人。
祁肆收拾干净后,准备下一台手术。
日子依旧忙,直到一周后有人联系他见面。
咖啡厅里,昏黄的灯光,极具格调的装饰,无处不彰显着来人的品味,祁肆在沙发上落座。
“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一杯冰美式。”
“好的。”
服务员礼貌问完就走了,他抬手看着表。
没过半分钟就有人推开门,身上还穿着警服没脱,他对服务员说了什么,然后朝祁肆这边走来。
“祁医生总算肯抽出时间来见我了。”
祁肆慢条斯理地拿起咖啡喝着,等人坐下才抬眼。
“不比沈警官忙。”
“那你铁定没时间谈恋爱。”
服务员将一杯拿铁端到沈盎然面前,他赶紧喝了一口,本以为会很苦,没想到味道还行。
“这咖啡不错。”沈盎然点名表扬。
“找我有事?”
祁肆察觉到放置在桌旁的牛皮本,封面沾满血迹。
沈盎然见他并不想叙旧,只好拿起桌上的本子,他用手拍拍封面的灰,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切入了正题。
“一周前,有司机撞到人肇事逃逸,被害者经抢救无效身亡,当时死者是送到你所在的医院。”
沈盎然接手这个案子时,并不知其中缘由,只因死者的闺蜜是他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所以呢?”祁肆不明白他的话。
沈盎然沉着声继续说道:“肇事者已抓获,这案子与你无关,是我受人所托,交付一样东西给你。”
“这是,死者的遗物。”
他将牛皮本慢慢移到祁肆的面前,神情严肃而沉重,仿佛是在执行一场艰巨的任务。
祁肆低头扫视桌上厚实的牛皮本,表面已经饱受风霜,这种款式的本子,他依稀记得自己在高中时期也买过。
年代久远,与他有关。
“什么人托给你的?”
祁肆把咖啡推远,以免碰洒到牛皮本上,他知道沈盎然不会随便帮人送东西。高中时有人托他递情书,他直接拒收,不管别人用尽任何法子,他像个铜墙铁壁。
沈盎然很有原则,不会轻易做出这种事。
“我的……青梅竹马。”他挠着头。
“顾春意?”祁肆思考几秒说出名字。
“是。”
祁肆的记忆中,他与顾春意并无太多交集,唯一的联系就是沈盎然,更别说死者,连面都没见过。
“如果我不接受呢?”
祁肆有洁癖,碰不得脏东西,这个牛皮本污成这般,他根本就下不去手,再者他有权拒绝。
沈盎然的表情为难,但他没有强迫人的习惯。
“随你。”他的语气故作轻松。
“但我的青梅可是抱住我的腿,哭着求了我好几个小时,我好不容易答应人家,你让我如何交待?”
沈盎然说完一长串的话,端起咖啡喝。
“毕竟,死的是她挚友。”
他的声音微不可查,仿佛也在替死者惋惜哀悼。
祁肆又看向那本笔记,心中松动,他有种感觉,如果不接下他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
“她有留其他话吗?”
沈盎然回忆着,顾春意当时情绪不稳定,哭了几个小时,他哄了半天才停下,话倒没留下几句。
“她让我告诉你……”
沈盎然顿了顿,继续把话带下去。
“那天,她是为你而来。”
“她想说的话,都在这里。”
沈盎然带完话后,空气都安静下来。
“挺巧的。”他干笑一声。
祁肆沉默了许久,到沈盎然喝干净咖啡,他强忍不适拿起牛皮本抚摸着,翻开了第一页。
【你好,74号同学。】
【我是,67号同学。】
他合上本子,不打算在这里阅读。
“我还有事,先走了。”
“嗯。”
沈盎然说完整理好自己的警服,他去前台结完账便离开了。
祁肆目送他的背影,杯中的咖啡有些索然无味,稍坐片刻后他带着那本牛皮笔记走出咖啡厅。
咖啡还有一半,服务员见人离开便收走了。
祁肆难得的休息时间,上午与沈盎然见面谈话已经花费半天,回到家时快到中午,他换上拖鞋走进洗手池。
将手清洗过好几遍后,他戴起医用手套拿着牛皮本,用酒精喷完又取出纸巾包裹严实,摆在茶几。
做完这一切,他才闲下来用餐。
等到晚上九点,祁肆坐在房间里,牛皮本已经让血染红一半。
祁肆的手不受控制地翻开它,开始阅读起来,很多字迹已经模糊不堪,但大致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笔记主人的字体看起来自由洒脱,不似墨守成规的工整,反而要跳出边框飞起,漂亮得很。
都说字如其人,不知她长什么模样。
祁肆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得有些入迷。
自称67号同学的她,没有过多在日记里描写自己的生活,只记录她认为重要的事,包括74号。
看得出来,她很有仪式感,祁肆能从笔记中感受到浓厚的情感。
【再见到你的那天,我是开心的。】
【你一定不记得儿时的事,但我记得就好。】
【总不能,两个人都忘了吧。】
【你的优秀,是我的触不可及。】
【我努力想跟上你,但痛苦也伴随着我。】
【你还是离开了,我找不到你。】
【我该去哪找你?】
【孩子们能带给我欢乐,你也是。】
【我找到你了!真的找到了!】
【你这么累,我也无法安慰你。】
【原来,你已有家室。】
【从现在起,怕是不会再见你了。】
【人总要往前看,但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决定,再见你最后一面。】
【我没穿过红裙,我想让你见到我最美的样子。】
【我希望,我们还能有下辈子。】
【祁肆,我喜欢你。】
祁肆,我喜欢你。
……
三年后,在香火最旺盛的寺庙。
祁肆择良辰吉日在早上七点便到达寺庙,里面香客众多,他有先见之明,准备妥当才出发。
寺里的主持眼熟他,特意走过来交谈。
“主持好。”
祁肆对面前的人身子下躬,双手行合十礼。
“阿弥陀佛,施主您好。”主持回礼。
“家中的风信子开得可还好?”
“多谢主持关心,很好。”
祁肆笑了笑,他每个月都会来寺庙上香,寺里的主持那时看见他后将人留住,给了他一个建议。
“施主,您试着在家养养风信子。”
“应该对您会有帮助。”
祁肆听话照做,养了三年的花,好在风信子不难养,怕麻烦的他也变得有耐性,心中平静。
“主持,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上香。”
“阿弥陀佛,您会如愿以偿。”
“感谢您的帮助。”祁肆又行了个礼。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主持双手合十闭着眼,最后摇了摇头。
轮到祁肆时,他将香在佛案上的烛火中点燃,走到跪拜的凳前站立,正对佛像,双手持香。
他举香过前额,曲着腿直直跪下来,闭紧双目请愿。
三拜过后,祁肆站起身把香规矩地插进香炉。
他在佛像前注视了半晌,最终行礼离开。
祁肆在寺庙上了三年的香,也养了三年的风信子,他每次都不会耽搁吉时,更不会迟到片刻。
这么多年,心里的愧疚感该消失了。
那个女孩不会再回来,祁肆不承认这是遗憾。
祁肆在寺庙当中,把她对世间仅剩的那点留念用一把火给焚烧掉了,火星纷飞,他用手抓住一角。
那一角上的字迹清晰夺目。
【祁肆,我叫游琴。】
他掌心被火的余温烫得发红。
祁肆摊开手,纸片随风飘向不知名的地方。
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
祁肆依然养着风信子,只是没再去过寺庙。
在医院工作时,他的身子体力不支累倒在地,眼镜滑落到一旁被急忙跑过的护士踩碎,最后没有意识。
再次睁眼,他发现自己趴在教室的桌子上。
祁肆不了解情况,坐在旁边的人是个女生,他的头痛不止,完全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祁肆,你怎么了?”
女生看到他那么难受,连忙关心道。
“这是哪里?”他虚弱地张开嘴。
“啊?”女生没听懂。
祁肆站起身往教室外走,迎面撞上了一个女人。
“祁肆,上课你想去哪?”女人眼神不善。
“上课?”
因为头太痛,他扶着脑袋分散不开注意力。
“头疼?”
“整个初二年级的人,就你让我头疼!”
“初二?”
祁肆瞳孔微缩,眼神充满疑惑和震惊。
教室墙上的音响发出熟悉的打课铃,一声声敲打着他的心,让他的脑子开始变得迟缓。
祁肆脑海里回想起那位主持的话。
“施主,您会如愿以偿。”
家里的风信子快开了,他能看到吗?
点燃生命之火,便能再见那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