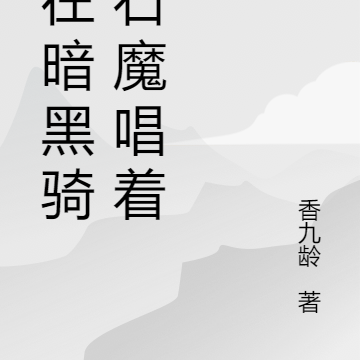第22章 宁家人各个是坏种
宁筝起初并不敢全然相信自已脸上的疤痕可以消掉。
可是接连泡冷泉几日,她惊喜地发现,那些疤在变淡。
原本深褐色的疤痕变成了淡粉色,用手摸一摸,也越来越平滑。
她看着镜中的自已,勾起唇角笑了一下。
好像,并不是那么吓人了呢。
虽然宁筝为此开心不已,可每当到了要去泡冷泉的时候,她还是不由地心底发怵。
以前她听老乞丐讲,官府里有种最重的刑罚叫凌迟,就是把人刮成一片一片的,据说没有人能扛过一百刀。
她觉得,每天在冷泉里的自已,就像被凌迟的人。
不同的是真正的凌迟削肉,而那冷泉水,削骨。
更不要提还有谢羡在。
给她的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凌迟。
而且,宁筝觉得,谢羡近来更加让人捉摸不透了。
他没有再像第一日一般失态,却也没再同她说一句话。
总是去了便下水,二更一过便准时离开,偶尔宁筝触及他的眼神,觉得比那冷泉水还要刺骨。
很快到了驱毒的第十日。
想到今日之后,就再也不用受冷泉的罪,眼瞧着脸上的疤痕又淡了一些,宁筝的心情格外轻松。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原本沉默了多日的谢羡,在这最后一日会突然对她发难。
宁筝像平日里一样来到后山。
谢羡已经等在了那里。
今日他并未着急下水,而是负手立在岸边,似乎是在等宁筝。
宁筝放慢呼吸,放缓步子,来到了冷泉边,对着谢羡恭恭敬敬地行礼。
可下一秒,整个人却被谢羡带了起来,箍在怀中。
谢羡让宁筝背对着他站立,骨节分明的手握着她的肩胛骨,逼她不得回头,直视前方。
他用了九成的力气,宁筝觉得自已的肩胛骨快被他捏碎了。
那日被锁喉的记忆浮上心头,宁筝的身子开始微微发颤。
她将刚刚自已的一言一行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实在没想到有哪里做的不对或犯了他的忌讳。
“宁筝,你们宁家人,很好。”谢羡俯身,在她耳边低语。
什么宁家人?
宁筝糊涂了,她哪里有家人,就连这个名字都是谢羡给她的。
谢羡在收到北地密信的第二日,便去信帝都,查实了这事的源头。
原来,源头竟在宁无忌身上。
宁无忌将谢家与前皇后的家书呈给皇帝,不知信上写了什么,让皇帝震怒,才派了天使到嘉陵关传话。
宁家人果然各个是坏种。
先在宫中弃了她,又在朝堂上弃了谢家。
谢羡那一刻,几乎差点没忍住,将宁筝提来捏死,用她的血告慰谢廷安受的罪。
宁筝不知道谢羡何意。
她只知道自已再不自救,今日有可能又要折在他手中了。
她拼命挣扎着,想要从谢羡的掌心里逃离。
可她于谢羡,就如蚍蜉撼树。
拉扯之中,宁筝身上的单衣半褪到了胸前,再往下一寸,便遮不住胸前的春光了。
谢羡看着眼前莹莹如玉的瓷白光泽,觉得眼底有些发烫。
他不着痕迹地收回视线,也松开了桎梏着宁筝的手。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的巧合,多一分有缘,少一分遗憾。若那单衣再往下褪去,若谢羡没有收回视线。
便会发现,宁筝肋下,有一枚小巧精致的粉色月牙状胎记。
宁筝慌乱地将衣服拉了上去。
谢羡没再看她,径自到冷泉中坐下屏息调神。
宁筝抱着手臂小心翼翼地踏进冷泉中,她不敢离谢羡太近。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她本已经将听水榭中的事忘的差不多了,可今日,谢羡又提醒了她。
她不过低贱之身,一介蝼蚁。
若没有自保之力,便随时都可以任人捏死。
宁筝的心底第一次涌起不甘。
做天上振翅的鸟雀,还是做水中的蜉蝣,亦或是土里的蚂蚁,对宁筝来说,并不需要做选择。
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