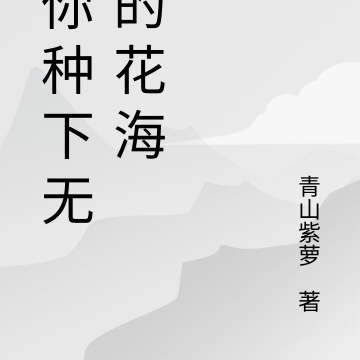“我顿时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戏弄,再也忍不住,直接破口大骂。她却只是冷冷地看着,并不阻止。不知骂了多久,我口也渴了,词也穷了,便从骂过的话里挑了一句接着骂,她却突然道:“这句重复了,蠢材!”我一愣之下,便住了口。”
“她见我停下来,道:“骂够了么?”我看她脸上丝毫不着恼,心想这女婆子不吃骂,便说:“骂够了。”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说:“你一共骂了三十五句,但最后这一句是重复的,那不能算,因此就三十四句好了。我老婆子活了这么久,从来没人敢这么骂我,你小子有种。就凭这一点,我给你一次机会。”我心中好奇,便问道:“什么机会?”她哼了一声,道:“这俩孩子你想要,那就拿你最宝贵的东西来换,只要价格公道,我老婆子就不难为你。””
“我心道因为自已鲁莽,杀了孩子娘亲,正是有恶因得恶果,能以自已这条命,换这两个孩子活命,倒也合算,便将手中戒刀往地上一抛,说道:“前辈只要说话算数,来取我性命便了。”说罢垂手而立,闭目就死。谁知话刚落下,脸上竟吃了一耳光。”
“只见她满脸怒容道:“我老婆子的话,你当耳旁风么?说了要拿最宝贵的东西换。”我愣住,实在想不通,便问她:“难道还有比性命更宝贵的东西吗?”她脸上露出轻蔑的神色,说道:“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派的,一个个把自已的性命瞧得这般轻贱,你们自已尚且看不起自已,我老婆子要这贱命来作什么?”我听她这话,似乎是不要我的性命,但除了性命,我还有什么宝贵的东西?金银珠宝么?那我可没有。”
“我正感觉难办,只听她自言自语道:”既然是出家人,最宝贵的,应该是香疤。”她朝我的光头一望,眼中顿时放出光,手上拿了把匕首朝我走来,接着我便感觉头顶传来一阵剧痛,鲜血淋漓。她在我的头顶连戳三十四下,才住了手。”
“我以为自已要死了,可她刀刀戳下,却都只是伤了头皮。只听她笑道:“毁了你的香疤,没准你还会再香上,可毁了你的头皮,香疤就别想再长回来,妙极!妙极!”我又疼又怒,骂道:“你个疯婆子!”她却不理会,将两个孩子往我怀里一丢,又道:“你既然没了香疤,就休想再当和尚,否则你徂徕寺便赔我三十四条人命吧。”说完,如一道青烟,消失在暮霭里。”
众人听到这里,纷纷往鬼王头上瞧去,只见他满头癞包,确实无法再点上香疤,有人觉得滑稽,忍不住笑出声来。鬼王不以为忤,继续往下讲:
“我抢回了两个孩子,当真是喜不自胜,顾不得头上疼痛,寻到一个住处,安置好孩子,才将头上伤口裹了,去见芈盟主。芈盟主看了我的伤势,又听了我描述,说道:“你遇上的只怕是列缺门的右护法,叫洛扶风,是个杀人如麻的女婆子,一身出神入化的轻功,极难对付。你能从她手下活着回来,已经很难得了。”我听了这些,知道报仇无望,彷徨无计之下,便辞了芈盟主,修书一封给我师兄,直言自已杀戮心重,尘念难制,决定还俗。师兄一怒之下,便将我逐出门墙。”
众人均想,这定然是因为担心牵累师门,才找的借口,由此来看,此人倒是个有担当的汉子。院中许多人投来钦佩的目光。
只听鬼王又道:
“此后我便带着两个孩子,离了西余往南走,一路之上艰难乞活,虽然有了上顿没下顿,总算没有饿死。半年之后,我在南楚界上,见了一对夫妻,男的丹凤眼,女的柳叶眉,长得甚是不俗。他俩见我一副恶僧模样,还带着两个孩子,觉得奇怪,便尾随着我。我那时心情极差,孩子不时哭闹不休,更惹得我无名火起,将孩子放在一块高耸的石头上,停下来质问他们。”
“那男的倒是很有礼数,拱手道:“在下黄兴嗣,请问贵驾?”我拱了拱手,道:“无名僧一个,不劳问驾。”那女的便伸手指着孩子,问道:“既是僧人,这两个孩子,从何而来?”我哼了一声,不去理会。谁知那女的伸手便将佩剑拔出,叫道:“师哥,这恶僧定是杀人越货,抢了别人的孩子。咱们联手除了他。”我心想,好大的口气,便坐着不动,只等他俩来攻。”
“那男的却道:“不可鲁莽。咱们即日北去,不必多生事端,只要问清楚,不是贩卖人口的,便随他去吧。”说着,走上前来,道:“大师劳驾,不知这孩子父母是谁?”我那时心中烦躁异常,便说:“不知道。”那女的见孩子哭闹,我也不闻不问,更是愤怒,手腕一抖,便朝我攻出一剑。”
“我见她剑法虽不甚精,但一招一式,俱是名门气派,不愿和她一般见识,只守不攻。谁知她竟然越发狠辣,几乎是拼命的打法,我心中怒气上冲,一声断喝,便要出招。却不料石头上的孩子被我这一声惊吓到了,直从上面掉了下来。我背对着石头,没有察觉,那女的却看得真切,将剑一丢,发疯一般朝我扑来,我心中惊异,微一侧身,接着一掌拍过,只听”啵“的一声,正中她后背。”
“那女的一口鲜血吐出,抱了孩子挣扎着站起来,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她是扑过来接孩子的,幸好我出手不重,她虽然受了伤,倒也无大碍。我见她两眼盯着孩子,满脸俱是喜色,一刹那间,灵台骤然清明,便知机缘到来,见那男的正走上前查看伤势,立即躬身下拜,道:“二位侠士,请恕罪。”那二人见我行了这个大礼,很是疑惑,我便请了他们坐,将这俩孩子的来历说个清楚。”
“那二人才知是误会,便要起身赔罪,我却直言,这俩孩子跟着我一个行脚的僧人,实在太苦,今日有缘遇上贤伉俪,不如便领了孩子,妥善管教。那女的甚是喜欢,男的本有些犹豫,却也拗不过,终于是答应了,于是我便将孩子托付了他俩。”
众人听到这里,纷纷点头。
“一晃就是几年,我走南闯北,始终不敢称自已是徂徕弟子,一日突然想起那对夫妻和两个孩子,便悄悄潜回西余来寻找,几番打听下,才知他们已去了塞北安家,也换了名字,男的称作黄文卿。”
高娘子听到这里,“啊”的一声惊呼。原来这黄文卿不是别人,正是几个月前被杀的黄家七口的当家人。朱不吝一声叹息,他听到黄兴嗣的时候,便已经有所怀疑,不料故事往下发展,竟真是这样。
鬼王朝高娘子微微点头,脸上有些凄然,接着道:
“我跟着来塞北,去见黄家夫妇,他二人甚是高兴,便称我作大哥,想让孩子叫我义父,我心中感激莫名,却还是推掉了。彼此聊得一深,这才知道,他二人乃是旧日南楚的子弟,师承楚家,后来南楚覆灭,便流落江湖。来到塞北后,觉得地面虽乱,比之西余的江湖忌讳,仍是宽容得多,这才安了家。他二人劝我也留下,待孩子再大一些,便教他们轻功。”
“我那时只怕自已是个不祥之人,便承诺将来一定教孩子武艺,但却不能在他们那儿安身。于是每隔一年,就去看望一次。自已闲来没事,便在江湖飘荡,时日一久,渐感厌烦,这才真正明白过来,那女婆子洛扶风的确高明,她拿走的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皈依之所。”
“她让我既背负着误杀的罪名,又不能回徂徕寺里忏悔,就如同一个孤魂野鬼。终于我决定要有所改变,打算做一件有功德的事,来减轻内心的罪孽。可是该做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佛门提到的“救苦”。于是我逢人便问,什么人最苦?有人说,耕田的最苦,我便去找耕田的,看到那些农夫白天干活,的确很辛苦,但晚上一回到家,却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竟然一点也不苦了,我只好作罢。又有人说,生病的最苦,我便来到药店,看到很多人愁眉苦脸,确实很苦,但过不几天,他们的病就好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根本半点苦也没了。我还不死心,一直不断地去问。”
無錯書吧“终于有一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一家茶棚喝茶,听到两个人谈话,说的是当地一家妓院里有个叫如茵的,从良无门,日日哭泣,附近的良人们每天去安慰,她却还是哭得梨花带雨。我心想,这还得了,这是受了多大的苦啊,于是便立刻到那家妓院,不由分说,拉了如茵姑娘,道:“跟我走。”如茵姑娘心中害怕,可能是那老鸨平时虐待她,竟然不肯走。我很是生气,见老鸨找人来拦我,于是一拳一掌地都给打发了。如茵这才哭哭啼啼地跟着我离开。”
“救了如茵出火坑,我心里格外高兴,当晚便睡得很香。不料第二天一醒来,如茵姑娘竟然赤条条地躺在我床上,我当时吓得魂飞魄散,心想:好哇,我救你出火坑,你却恩将仇报,把我往火坑里推,这淫戒一破,最后一点和尚的体面也没了,我心中恼怒,只好将她赶走。”
“过了几天,我忽然听说如茵姑娘又回到妓院了,心中好生奇怪,难道是老鸨又逼她?于是便去那家妓院问清楚。那老鸨见了我,怕得要命,便带了我去见如茵。如茵见了我,就开始哭,我心便软了,说道:“救人救到底,跟我走吧。”于是帮她收拾细软行李,没想到如茵竟突然拔出一只匕首,朝我后背用力刺了进去。我只觉得后心一阵疼痛,险些晕厥,便回过身来问她为什么要杀我?她一边哭一边后退,突然纵身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当场摔死了。“
“我实在是摸不着头脑,那一刀离我心口其实只差半寸,只因我皮糙肉厚,才没被戳死。周围的人都冷冷地看着我,眼中充满了仇恨,好像我是个瘟神一样,眼见我失血越来越多,竟然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我只好强行挺着,离开了那里。”
鬼王讲到这儿,便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来。那匕首虽然已经陈旧,但刀把上绣着一朵小花,还有个模糊的鸳鸯戏水,分明是女人的东西。
朱不吝看了匕首,淡淡说道:“大师可知是谁害死了如茵姑娘?”
鬼王愣了半晌,道:“只怕是我自已。”
朱不吝不再言语。
鬼王见大家都沉默,便继续讲:
“如茵姑娘死后,我心里最后那点想要积德的想法也没了。与其受那良心的折磨,何不干脆去做个恶人。一个人的过往,照不见他的将来,师兄当年的话,我再也不听。我回到塞北,见到好人,便觉得虚伪,非逼着他干了坏事,才算罢休。后来终于活出点滋味,原来一个人一心向善,总要受尽委屈,可是只要作恶,就酣畅淋漓。那些假模假样的大善人,见你谦逊卑微,就可着劲儿作践你,但是你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却比马还老实。”
“那几年里,我劫了很多财,也散了很多财,是对是错我也不在乎,反正知道自已是要下地狱的,又何必对将来必然的命运担惊受怕。师兄以前说,行善举“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让我们万不可懈怠,我活了大半辈子,师兄的觉悟是做不到了。但我觉得,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一个人总被劝说向善,其实就像是推着石头上山,恶念不是被消灭了,只是藏在石头里。他只要是推不动,恶念就会滚滚而来。与其这样,还不如都先去做鬼,鬼做腻了,再来当人。于是便给自已取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号——地藏鬼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