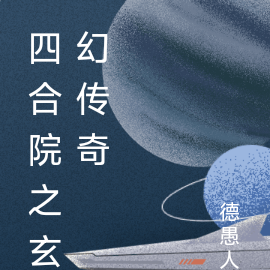第128章 冠礼
穗欢依照萧云祁的指示找到了洪嬷嬷,将洪嬷嬷送到了长宁宫中。
宁筝原本凄然的情绪在看到洪嬷嬷的那一瞬间尽数化成了委屈。
她又变成了幼年时跑到嬷嬷怀里缠着她讲民间趣事的小姑娘。
“嬷嬷......”宁筝唤了一声,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她好像透过洪嬷嬷看见了那个美丽的华贵女子,她的母亲,大殷的谢皇后。
洪嬷嬷手足无措地立在寝殿中,两鬓斑白,手上带着做粗活留下的裂口,走进来时一跛一跛的,身上的粗布衣服满是补丁,连普通乡绅家最低等的婆子都不如。
宁筝心里一紧,走上前就要扶洪嬷嬷。
洪嬷嬷吓了一跳,慌忙跪下告罪道:“奴婢恐脏污了贵人的手。”
这拘谨小心的样子,也不知道在柳条巷受过多少管教。
宁筝记得从前洪嬷嬷是最爱讲笑话的,脸上总是红扑扑的精神气满满,和如今萎靡枯槁的老妇不像是同一个人。
宁筝压下心头的酸涩,柔声道:“嬷嬷仔细看看我是谁?”
洪嬷嬷小心翼翼地抬头,打量了宁筝半晌,突然她眼睛亮了一下,颤着嘴唇说:“宁......宁姑娘?你不是......不是同娘娘一起......”
话说了一半,洪嬷嬷不忍心再说下去,眼眶发红。
宁筝挤出一个笑容摇了摇头,轻声哼唱:“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着鼓来了,什么鼓,雷公鼓,梆当梆当二十五......”
这时幼时洪嬷嬷教给她的家乡童谣。
许多个夜晚,她都是听着这首童谣入睡。
洪嬷嬷震惊地睁大眼。
然后抬起手捂着嘴,眼泪夺眶而出,顺着指缝啪嗒啪嗒掉落在寝殿的地上。
声音很清晰,像砸在了宁筝的心上。
“公主......?”洪嬷嬷从喉咙里挤出了这两个字。
在得到宁筝肯定的点头之后,洪嬷嬷眼泪掉的更凶了。
宁筝安抚了她许久,才终于将话题引到了玉玺之上。
她原本找洪嬷嬷只是为了碰碰运气,没想到洪嬷嬷对内情知道的不少。
那日之后宁筝几乎在长宁宫闭门不出。
很快到了璟王冠礼的日子。
徐皇后想为璟王办一场盛大的仪式,没想到受到了朝臣们的反对。
他们说宸王还未行加冠礼,璟王不能越过兄长。兄弟有序才合乎人伦。
还说宸王生母谢氏虽然已逝,但说到底也是陛下的发妻正室,宸王占嫡占长,冠礼应该比璟王更加隆重。
徐皇后听到朝堂上的议论,气得大发雷霆。
“谢嬛那个贱人,死了还不让本宫清净,什么发妻正室,她不过是反贼谢氏的一条狗。她的儿子怎么配跟我的皇儿比,这些大臣被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帮着萧云祁那个小杂种说话!”
一盆血色欲滴的硕大红珊瑚被徐皇后推倒在地上,这珊瑚是南疆进贡的价值连城的极品,就这样被摔得七零八落。
宫侍们吓得在地上跪成一片,谁也不敢触皇后的霉头。
这么多年,谢嬛就是徐皇后心里的一根刺,是她曾经为妾耻辱的元凶,只要和谢嬛有关的事,就会让她失去所有的仪态和冷静。
当然更让徐皇后不安的是皇帝的想法。
皇帝虽然表面上惩戒了谢氏,但还是依礼厚葬了谢嬛,对萧云祁也是嘴上苛责却从没有伤及内里的责罚。
还有赐婚萧云祁和户部尚书之女,对他放权重用。
甚至这次朝臣说宸王占嫡占长时,皇帝也并未表明态度,似乎默许了朝堂上的争论。
这些都让徐皇后不由地多想,她隐约觉得有人在背后下一盘大棋,而她和徐家被网罗其中,要步步小心,一步走错就会万劫不复。
“去,请璟王来。”徐皇后好不容易镇定下来,思索了片刻着人去请璟王。
她想试探一下陛下的意思。
萧云睿没多时便来到了皇后寝宫,寝殿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他施施然行了一礼,说:“母后唤儿臣来有何要事 ?”
晨起请安时皇后还是一副和悦之色,怎么这会儿脸上覆着一层阴沉之气。
徐皇后看着眼前芝兰玉树一般的儿子叹了口气。
如果有选择,她真的瞧不上宁筝。
宁筝不过是大理寺少卿的孙女,父亲官职不显,母家是低贱商贾,自已又在外流落多年,谁知道有没有学会一些腌臜市井气的东西。
而萧云睿,自小用功天赋过人,又容颜出众,举手投足间如朗月清风,在京中颇具盛名。
他值得最好的女子。
徐皇后本来打算冠礼之后就求皇帝废止璟王和宁家的婚约的。
只是现在时移世易,萧云祁回京后对徐家多番掣肘,为了拉拢陛下信任的宁无忌,也为了制衡宸王一党,只能咬牙认了跟宁筝的婚事。
徐皇后幽幽地开口道:“冠礼在即,去求一道赐婚旨意吧,你与宁家姑娘的婚事拖了太久,是时候让钦天监挑个好日子成婚了。”
闻言,萧云睿诧异地看向徐皇后,如玉般的眸子闪过喜色。
他还以为,徐皇后不喜欢宁筝,会阻挠他们的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