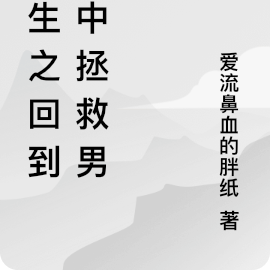第三十二章 濒临死亡
张泰转头看向说话之人。
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蓬头垢面让人看不出他的年纪。
手里那缺了口的破碗,不住地抖动着里面的几枚铜钱。
刚才的话正是他说的。
张泰见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开,便转身走向叫花子。
从衣袖里掏出一串铜钱,丢在了破碗里,淡淡开口:“劳驾问下,你可知这院子的主人去了何处?”
叫花子看着碗里的铜钱,语气明显好转了不少了,不再用阴阳怪气的语调说话了。
“这位老爷,您问的是这院子的新主人还是旧主人?”
张泰出来时并没有穿扎眼的官服,而是一身员外富商的打扮,所以叫花子并不知他的身份。
听到叫花子的反问,张泰不禁有些意外:“这院子被人买走了?”
叫花子嘿嘿一笑:“买不买的不知道,反正这个院子不是原来那个浪荡书生的了。说起来,那个家伙对我还是很大方的,每次出门怎么也得给我一吊钱。
不像那个姓许的白面书生,面善心恶,这世道多的是这样的人……”
“休要聒噪了!那王若虚现在何处?”张泰有些急切的打断了叫花子的喋喋不休。
那叫花子也是个混不吝滚刀肉,见张泰急于知道王若虚的下落,反倒住嘴不说了。
身后的吏员大骂:“你这厮该死,我家大人向你问话,还不快说?!”
张泰不想浪费时间,又是一小串铜钱抛出。
那叫花子立马眉开眼笑:“几个时辰前,长平县差役把那个书生给抓了,说是意图谋反。”
“真是乱弹琴!”张泰听后骂了一句,急匆匆上轿子离去。
过了有一炷香的功夫。靠着墙根的叫花子,正喜滋滋盘算等天黑了吃顿好的。
嘚哒嘚哒的马蹄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抬头看,三匹高头大马风似的冲向自己所处的位置。
飞驰而来的马匹,离自己只有几尺远时,那骑马之人才勒住马缰。
叫花子吓的裤裆里都有些温热了。
马上的左开疆透过矮墙,耳目一扫便知小院内空无一人。
“李乘风,你确定那小子是住在这里的吗?”
李乘风环顾左右:“应该错不了,就是这个坊市街道。”
李月娘一抖缰绳,马匹缓步前行绕着院墙走了一圈。她看见了呆愣着的叫花子。
李月娘一边下马,一边从兜里摸出几个铜板扔进破碗里,开口问道:“花子,这院子的主人可是一个书生,叫王若虚?”
本来被吓得惊魂未定的叫花子,听到李月娘的问话后,心里瞬间乐开了花:哎呦,今儿我是撞大运了,又是一波儿找那书生的!
乞丐低头看着碗里那几枚铜板,心中不由鄙视:和刚才出手阔绰的老爷比,这位明显太小家子气了!
他心里打定主意:“嘿嘿,给的不够,老子可不回答。”
看着置若罔闻的叫花子,李月娘的小脾气蹭蹭的就上来了。
“嘿,你莫不是个聋子吧?!”奔波儿霸花木兰马上要发火了。
这时,李乘风一夹马腹缓缓走了过来。
他打量了一下叫花子的穿着。
浑身上下衣衫破烂,但是手臂和腹部偶尔露出的皮肉却是异常白皙干净。
脖颈处一只蚂蚁形状的纹身若隐若现。
李乘风冷笑:“哼,你是刘三儿的手下?老子这段时间以来不在京城,看来刘三儿把我们五城兵马司给忘了?!得空儿了,我李乘风还得去拜会拜会三爷啊!”
叫花子听到李乘风点破他的身份,连忙抬头仔细观瞧他的穿着。
五城兵马司火红的衣袍,上面张牙舞爪的金色老虎云纹,甚是威武。
“哎呀哎呀,小的该死,有眼不识泰山。三爷经常告诫我们见到五城兵马司的大老爷们,一定要磕头问好。小的眼瞎了,这就和您磕头认错……”
叫花子一边油嘴滑舌的说着,一边装模作样的磕起头来。
“行了行了,”李乘风没有心思为难一个小虾米。
“这个院子,主家是不是一个叫王若虚的书生?”手里的马鞭一指,李乘风问道。
叫花子忙不迭回答道:“是的,是的。原来这里是那王若虚王公子的院子。”
“原来?”李月娘一旁插嘴问道。
“可不是咋滴!后来王若虚被人举报写了反诗,被长平县衙判了个流放蜀州。这个院子就被一个叫许书言的书生接手了。”
叫花子一口气说出了原委。
李月娘有些着急:“你磨磨唧唧说了半天,到底有没有见过王若虚?”
“有,有,有!”叫花子赶紧找补:“几个时辰前,被长平县的衙役和一个白面书生,给带走了!”
我草!李乘风忍不住心中暗骂,把这茬给忘了!
王若虚这小子到现在还背着写反诗的罪名呢!
这长平县以前说白了就是京城的卫星城。后来随着京城面积的不断扩大,就连长平县县衙都被囊括进京城里了。
此时,阴暗的长平县衙牢房。
王若虚帅气的脸庞已经被揍的像个猪头了,两个乌青的熊猫眼遮盖了小半张脸。
血水顺着嘴角不住的滴答滴答流出,但他的意识还很清醒。
“妈的,万恶的封建社会没人权啊!”王若虚低头看着自己的一身书生长袍,早已经烂成了前卫的洞洞装。
“师父,您老人家咋还不来救我了?您该不会忘了还有一个天生丽质的徒弟吧!”
正在心里吐糟时,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一旁响起:“若虚贤弟,怎么样?你就说出来吧,让你受这样的皮肉之苦,为兄实在是于心不忍啊!”
王若虚用模糊不清的眼睛努力看向声音的方向。
“呸”的一口血水吐出,“许书言,我日你先人!亏我和你相交数年,竟然没发现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真面目……我草……啊!”
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感打断了王若虚的喝骂声。
许书言脸色铁青,把手里的烙铁从王若虚烧焦的胸前移开。
“王若虚,你以为你现在是在万花楼喝花酒吗?你现在写反诗的谋逆重犯!我就是在这里把你活活整死,也不会有人在意。”
把烙铁扔进炭盆,许书言拍了拍手:“所以,只要你乖乖说出那万两黄金在哪里,我保证让你死的痛快些。”
王若虚扯了扯嘴角:“嘿嘿,许书言,你会后悔的。我师父是五城兵马司……”
“啪”的一声脆响,
许书言收回手掌冷笑:“五城兵马司?整日里和那些贱民打交道的破衙门,指望能有什么大人物出面救你!
呵呵,我义父可是当今都察院左都御史,连内阁大臣都得礼让他老人家三分。别抱什么期望了!再说你可是朝廷重犯,谁敢救你?”
在牢房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钱益得有些不耐烦的说:“许贤侄行了,这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厮还是不肯吐口。依我看那多半是他酒后胡言!赶快处理掉他行了!”
“钱世叔,您再给我一炷香的时间。到那时再结果他也不迟。”
钱益得见许书言还是不肯放弃,无奈摇了摇头。
看着蜷缩在牢房角落里的阿就,钱县令指了指对着许书言说:“还有这个傻子结巴,也一并处理干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