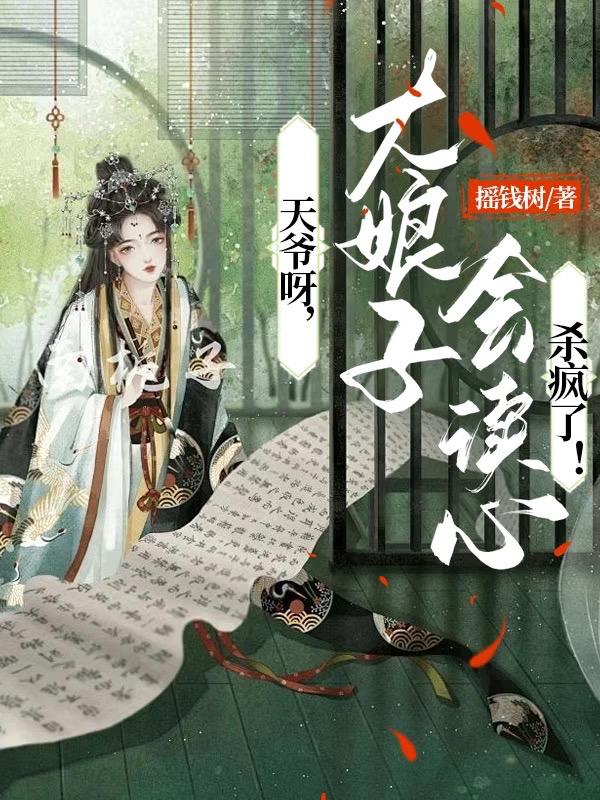顾怀宴高大身躯逆着车灯缓缓靠近,明明只有十几秒的时间,时愿却觉得无比漫长,然后那张英俊的面孔如恶魔般出现在副驾车窗旁。
他慢条斯理地拉了拉车门,不出所料,是锁着的。
然后时愿就看见他勾唇轻轻笑了笑,手指弯曲,叩了两下车玻璃。
时愿身子也随着那两声声响而颤抖。
时愿咬了咬牙,正准备拉开车门,裴妄却突然攥住了她的手腕,沉声道:“别开,我的人马上到,我保证他不会把你带走!”
时愿苦涩地扯了下嘴角,还未来的及说什么,车窗外顾怀宴突然把手伸向了后腰。
时愿无意瞥见后迅速甩开了裴妄的手,可她动作还是太慢了……
“砰——!!”
消音手枪发出的声音并不大,但子弹穿透玻璃又擦着时愿的脸飞向裴妄,最终击碎另一侧玻璃的动静却极大,以及裴妄口中忍不住溢出的闷哼。
时愿骤然回头,裴妄胳膊上的擦伤流血不止,脸色也变得苍白。
“阿愿。”顾怀宴的声音透过碎掉的车窗传了进来,“你是要我绑你下来吗。”
很平淡的声音,平淡到甚至辨不清他的情绪。
可只有时愿知道,此时的顾怀宴有多生气。
时愿眼睑颤了颤,轻声说:“裴妄,谢谢你,但我走不掉了……”
“时愿!”裴妄忍着伤口的痛,再一次抓住时愿的胳膊,“你再相信我一次,我的人真的马上就到了!我会带你走的,一定会的!”
“阿愿。”顾怀宴又叫了声,这次的声音明显没了耐心。
时愿咬了咬唇,一点点掰开裴妄的手,冷淡道:“裴老板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待手腕解脱,时愿立即拉开车门,走到了顾怀宴面前。
顾怀宴看她一眼,又冷冷睨了车里的裴妄一眼,未发一言,转身往直升机前走去。
时愿顿了顿,抬脚跟上。
直升机升到半空时,时愿往下看见了十几辆越野车齐齐赶来,无数黑衣人从车上跑下来,而裴妄站在他们中间抬头往上看。
“舍不得?”顾怀宴冷嗤道。
时愿收回目光,垂下脑袋没说话。
顾怀宴刀刃一般的眼神落在时愿脸上,这种目光太过难捱,时愿索性闭上了眼,靠在椅背上。
她看起来很平静,像是毫不在意他的怒火,也像是接受了现实,接受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事情。
可她这副平静的样子却彻底激怒顾怀宴,大手直直扼住时愿的脖子,甚至都能听到骨骼在手下发出脆弱的声响。
时愿说不出话,窒息的感觉让她头脑发昏,她勉强睁开眼,看见顾怀宴那张毫无瑕疵的脸慢慢朝她耳边靠近。
灼热的呼吸洒在耳朵,顾怀宴的声音沉的吓人:“阿愿,你有胆。”
缺氧的感觉已经到了尽头,时愿感觉自己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她全身感官正在一点点消失,挣扎的手也慢慢没了力气……
顾怀宴冷眼看着,手上仍没松劲儿。
双手无力的垂下,时愿在意识消失前的最后一刻,好像隐约听见了顾怀宴开口说了一句话——
“想离开我,那你就去死。”
接着时愿便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时愿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她还很小,孤儿院的小朋友都有小伙伴一起玩,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蹲在操场角落。
然后她又梦见了时父时父,看见他们从一辆豪车上下来,笑着走到她面前伸出了手,问愿不愿意跟他们回家。
小时愿点了点头,怯生生的说愿意。
从此她就从孤儿院里的小七,变成了时愿。
她还梦见了在舞蹈室里受的伤,梦见了妹妹跟在后面叫姐姐,梦见了校园里的朋友,家里的饭菜,以及大学后登上的第一个大舞台。
然后她梦见了顾星越,他温柔的眉眼,深情地对她说:愿愿嫁给我,我会对你很好……
梦见了顾怀宴,那个离经叛道疯子一般的男人,他有着让女人疯狂的脸,可那张好看的脸却对她说遍恶语,对她做尽强迫的事。
画面一闪,是她睁开眼后顾家所有人脸上嫌恶的表情,她们口中骂着不知廉耻,捉奸,丢人,娼妇……
然后一个宽大温暖的怀抱,抱着她离开了那些如同万箭穿心一般的话。
最后她住进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那里种着万万朵玫瑰,阳光折射在玻璃房,耀眼的好看。
可是她却很不快乐。
她阴暗,她颓废,她一心只想离开……
可为什么她的妈妈却在哭,她拉着自己的手一直在哭,在卑微的乞求着什么。
从哭声中她知道了,她还不能死,她还要再活三年。
可三年到了,她还是不能离开。
她真的好想离开,如果离开不了,那她还是想死……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男人,他说他可以带自己离开,他保证的很诚恳,她信了。
可直升机却来了,顾怀宴太强大了,她好害怕。
意识越来越不清楚,时愿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不停下坠。她拼命挣扎,可却抓不到任何东西。
恍惚间,她好像看见了两个人。
那两个人背对着她,她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见穿着白裙子的女人把一把尖刀插进了男人身体里。
好多好多血……
女人哭着踉跄在地,可男人却伏下身,替她拭去了脸上的泪。
男人倒地了,女人也睡着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没有第三个人,她却听到了有人在哭。
那哭声听的人好难过,好难过……
…………
再醒来时,时愿第一反应便是疼,全身上下铺天盖地的疼。
她试着动了动,却发现四肢都被绑住了,一瞬间时愿冷汗直冒,脑袋顿时清醒,睁开了眼。
纯白色的屋子,没有窗户没有装饰,只有一张孤零零的床。
看清一切后时愿呼吸猛地一滞,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咳嗽。
她嗓子疼的厉害,想必是直升机上留下的伤。
待咳嗽缓解后时愿平复着呼吸,慢慢打量着整间屋子。
刚才不是眼花,她确实是在一间纯白色的屋子里,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屋内安静的出奇。
时愿四肢都被绑在床上,她艰难低头看了看,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都被换过了,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