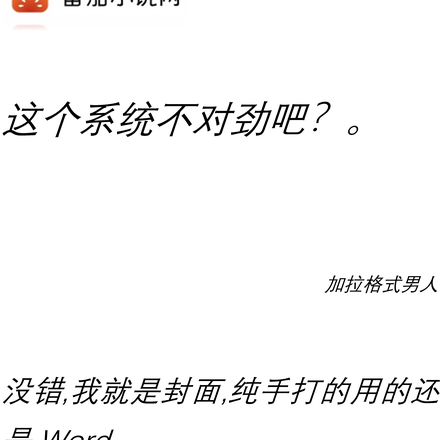吃过饭,几人再次上路,到了常州边境,东宫盛提议住客栈,许长生很是不解:“叔叔,您不是有事要办吗?住客栈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这里的蛇都精着呢,打不打草有什么关系?”
许长生似懂非懂点点头,东宫胜选了客栈住下,叶飞领着几人入客栈,刚刚啃完黄瓜的王孙玉莲叫住了东宫胜。
他回头,她偏着头不看,抬手举起水囊,故作扭捏地递给已然口渴的老狐狸精。
许长生几人回头,远远看着公主殿下孝敬师父,顿时满眼欣慰,只觉是师父将那小小孩感化到知错而改心存愧疚,于是转头往客栈内继续走。
“喝水。”
明眸皓齿的公主殿下满脸期待,东宫胜拔开木塞猛灌两口,神色一变,她立马得意洋洋地往客栈里跑,隐约听见身后有呕吐的声音,只觉大仇得报,心想那老狐狸精不过如此,真真是蠢笨如猪。
知计而饮的东宫将军胃里翻江倒海,将口中水全都吐了出来,随后赶忙走到马车后,扶着马车继续呕吐不止,却什么都吐不出。
想着那小家伙这会儿应当消气了,便将木塞塞上,只是那翻江倒海的感觉仍是一阵阵袭来,他只得继续扶车而吐。
“叔叔……吃饭了。”
入了厅一起吃饭,那小小孩低着头自顾自吃饭,只是嘴角忍不住上扬,许长生几人问她为何发笑,她只沉默不语,唯有东宫将军故作无事发生。
入了常州,随处可见的是横七八倒的尸体,或奄奄一息的百姓躺在官府门口,满脑子都是那清不过水的粥。
王孙玉莲坐在马车里,静静看着外面,横尸遍野四字忽而在心头浮起。那凉凉秋风,似是苍天奏起的悲歌。
她无心关怀此事,却不知为何胸闷气短:“官府没有……赈灾吗?”
“户部已拨了赈灾银两,各地的粮仓也尽可能的载运粮食。”东宫胜轻声回答。
“都是贪官!”
“您,着实是冤枉这儿的郡守了。”他摇摇头:“各处粮食运来,路途遥远,运者途中食其七八,唯剩二三。我们赶路就赶了十几日,各地粮仓紧赶慢赶,加之附近州郡的粮食和医药采购,即使无贪吞银两,可断了这十几日的粮,便是大罗神仙也难熬。”
“此患如何治?”
她看着他,满眼期待,从未有过的诚恳。
许长生几人如她一般,静静凝望着如师如父的他,只听他淡淡话语显得苍凉:“天灾无解,人祸难免。”
几人似懂非懂,他说:“这一路上,您见过了饿死街头的乞丐,任人欺辱的残者,或是天降横祸,或是人为所致,这就是大永的子民,这就是大永江山。”
王孙玉连几人没有搭话,东宫胜示意车夫往别处赶去。
秋风贯耳,她听见那老狐狸精轻轻的又说了一句话:“咱们,在四处逛逛。”
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的荒凉处人满为患,有驴牛车马,粮食满车,旁边有许多抱着孩儿人,还有不少形单影只的妇人大排长龙。
孩子被放入麻袋,成人则自行钻入麻袋被称上一称,钻出麻袋在纸上按上手印,便可得几张大饼,回头赠与家人,泣咽叮嘱一二,含泪而去。
“他们卖了自已的孩子?”马车里的王孙玉莲看着远处情形,心中些许沉闷,却又有些好奇:“他们会到何处?如此明目张胆,朝廷不管吗?”
历朝历代,贩卖人口都是重罪,大永朝也不例外。
东宫胜无奈道:“官府唯一能下场拦的法子,是给他们食物,要不然哪怕是利刃架颈也不能如何,天灾之下人祸随行,能活一日是一日,于他们而言,这兴许是唯一的活路,亦是此生的绝路。\"
“要是我,宁愿饿死,也不去做他人的奴仆!”
柔柔弱弱的少女从骨子里透出的坚定,让东宫盛深信不疑的知道她能言出必行,点点头,语重心长道:“有些人活着,有很多路可以选,有些人活着,只是为了活着。”
她怜悯地问:“所以他们都会被卖去当杂役吗?”
徐良和许长生陆续搭话:
“嗯嗯,当下人。”
“有的去当苦工,做那些很重很重的活。”
东宫胜道:“若能到大户人家里当个寻常杂役,便是极好,只可惜这样的好,是多少人都遇不上的。”
“碰上天灾战乱,若出些苦力便能得食无忧,是幸事,然而多则活不过今朝,见不到明日。”他指着人满为患处,语重心长道:“那些人,几张饼就可以跟人走,他们可以是大户人家的杂役,可以是街边乞讨的布衣,可以是被买去等着长大的童媳,童夫……”
“他们可以是拍花子们采生折割的对象,他们可以成为稀奇古怪的神熊,神蛇,神驴,神羊,他们是旁人一念之间就能做成法器的躯壳,是可以被掏去五脏六腑的牲口,也可以是哪家店里私下多花些钱便能吃上的两脚羊,却唯独,不能是人,做不得人。”
“两脚羊?”
少有言语的叶飞皱了皱眉,沉重地说:“就是人肉。”
“呕……”
许长生几人趴在马车窗边呕吐不止,胃里翻江倒海的王孙玉连沉默一会儿,顺手拿过旁边的水囊,打开木塞喝了起来,转头狠狠盯着老僧入定的东宫胜,斥责道:“你年纪大,我本不与你计较,我敬你是师长,可你为老不尊,张口闭口都是这些恶心东西,雷打不动日日说,你说这些东西来恶心我,你不觉得恶心吗?”
“啊?……你干什么?”
王孙玉莲还未反应过来,那人起身,将她拽出了马车,一把扛在肩头,声音淡淡似幽冷枯井:“还有更恶心的。”
“放开放开!”
惊慌失措的柔弱少女,死命拍打着魁梧身躯的胸膛和手臂却终无济于事,最后只得像霜打的茄子一般,任由他扛着自已,走了许久许久又许久。
她原本如烂鱼一样不再挣扎,可越到后面越觉得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越来越近,那直冲脑门的难闻气味,伴随着有婴儿或强或弱的啼哭之声。
腥臭的气味和杂乱的声音,让她想起了那日的地窖,着实无法忍受,于是她又开始挣扎起来:“东宫胜你放开!”
东宫胜在一处破落门前停下,将她高高举起,轻轻放进门内,惶惶不安的她扒着门,哽咽出声:“你干什么?”
她不断拍打着,拽着破旧的木门,破破烂烂的门却像是焊死一样,怎都打不开来。
这里并不昏暗,光线从半人高的门外透进来,外面已没了动静,老狐狸精好似走的无踪无影,无人应答她的无助,唯剩婴儿啼哭,只叫她更加不安,一阵阵的后背发凉。
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室内是数不清的婴儿堆积一处,微弱的叫声像猫儿一样,有些已开始腐烂,叫不出声。
“啊!”
她吓得眼泪横流,转头再不敢看,继续拍打着身前的门:“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拍了几下,眼见这破门还打不开,她“哇哇”大哭:“开门!我要出去,我要回家,父皇,父皇,父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