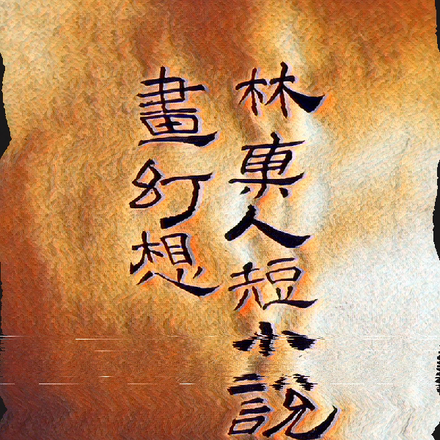第100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
面对陈光蕊的提问,袁守诚像条滑溜的泥鳅,打了个哈哈就想糊弄过去,
“嘿嘿,陈状元,您这话问的…天机难测,天机不可泄露。有些事儿不是不想说,实在是沾了因果太麻烦,稍有不慎……”
他夸张地缩了缩脖子,挤眉弄眼,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
“那是要掉脑袋的!小子,你总不能存心害老道我吧?”
陈光蕊没说话,只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正在不远处闷头拆地基的两个童子,金炉板着小脸,动作却异常坚定,一掌下去,土石飞溅,刚有点雏形的屋基瞬间塌了大半。
银炉抱着瓶子,虽然嘟着嘴一脸不情愿,但脚下也不闲着,把那点残留的木料砖石踢得到处都是,坚决执行着“毁掉庄子”的命令。
等到毁的差不多了,两个孩子在附近找了很多短工,开始热火朝天的拆庄子。
银炉虽然恋恋不舍,但还是指挥着人干活。
袁守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小眼睛滴溜溜转,凑近了些,指着两个童子的方向,带着点忧虑低声提醒,
“陈状元,你瞧他俩那拆房子的劲儿头,怕是没留半点后路哇。你这法子……真行吗?要是过两天高老庄里头那点腌臜事没闹起来,猪刚鬣还舒舒服服待着,高老头也没动静,这俩小祖宗岂不是要跟你翻脸?我看那小银童子,脸都绷成铁疙瘩了!”
陈光蕊终于开口,语气平淡无波,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笃定,“你不是能掐会算么,算算看,高太公会不会跟猪刚鬣翻脸?”
袁守诚压根就没算,而是咂咂嘴道,“翻是肯定会翻……可是这事未必就是现在啊。这种事,一日是它,一年是它,十年八年也是它,等那猪刚鬣的真面目一点一点露出来,高老头彻底压不住火才能见真章!你现在就撒手让他俩拆了家底,回头高老庄没动静,你怎么跟这两位交代?”
“这不就需要你袁道长来帮个小忙,让这一段时日稍微缩短些么?”
陈光蕊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看着袁守诚。
袁守诚胖脸上的肉抖了一下,没吭声,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呢。
高老庄内。几日前那点小骚动带来的不安早已消散。高太公穿着簇新的员外袍,背着手,在修葺一新的庭院里踱步。池塘锦鲤摆尾,屋檐下燕语呢喃,田庄上报来的秋粮长势喜人,仆从们忙中有序,一派蒸蒸日上的富庶景象。
前几天那突然冒出来捣乱的猫妖虽然闹心,但自家的“贤婿”猪刚鬣一耙子就撵得它抱头鼠窜,事后还博了庄里一片赞誉。
这桩事落在高太公眼里,非但没让他觉得是隐患,反而愈发觉得这个有本事护住庄子的“女婿”选得值当,省了多少护院的银子!他的心情,自然也就如同这秋日里的天气般爽朗熨帖。
这时,突然听到了外面人声嘈杂,高太公离远一看,竟然发现不远处那个要新盖的庄子,竟然有好多人,看那样子,好像是要拆了这庄子?
高太公刚想叫人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下人小跑过来,急声道,
“太公,隔壁……隔壁那块新庄子的地基,不知怎的,今早被人给砸了!好多短工在那拆呢!”
高太公脸上的笑容一顿,蹙眉,“砸了,谁砸的,怎么回事?”
“好像是……听说来了个游方的老道士,仙风道骨的,在那地基跟前算了一卦!”
下人喘了口气,接着道,“那老道说什么…此地风水本是极好的聚宝盆,却犯着两个妖邪冲煞,必主祸患一方,其中一个跑了,另一个还蛰伏此地,如不早除,必成心腹大患,连累乡里,所以劝那庄主赶紧停了工程,拆了地基以泄煞气…”
高太公起初还没反应过来,捋着胡须还琢磨,“两个妖邪?猫妖跑了一个,还有什么妖……”
话说到一半,他那松弛的眼皮猛地一跳,另一个,莫非……
下人小心翼翼地补充道,“太公,您说那道士会不会说的是……姑爷他?”
高太公脸上的轻松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心里那点得意被“妖邪”、“祸患一方”几个字刺得激灵一下。
“胡说,你也信这人乱说?”
他虽然呵斥,但是脑中却在嘀咕:
猪刚鬣,那道士说的是不是猪刚鬣啊?
可猪刚鬣明明……他脑子里下意识想反驳,猪刚鬣刚刚才护了庄子啊!但随之冒出来的念头却是,那饭量着实惊人……一顿抵得上十来个壮劳力,那日护庄打猫妖之后,伙房忙的加了人手都供不过来。
正心烦意乱间,庄外传来一阵清脆悠长的铃声,“叮铃铃……叮铃铃……”
高太公一个激灵,忙问,“外面铃响,可是刚才说的那个算卦道士?”
“听着像,太公可要去看看?”
高太公略一犹豫,强压下心头翻涌的疑忌,对下人道:“去,请那道士过府,就说……老夫请他吃杯茶!”
不多时,一个身着浆洗得泛白、但异常干净整洁道袍的老者被引进花厅,正是袁守诚。
此刻他脸上哪还有和陈光蕊扯皮时的市侩与滑溜,须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色端凝,双目半开半阖,俨然一副洞察天机、不染尘埃的得道高人模样。
高太公起身相迎,笑容堆了满脸,透着一股刻意的热络,“仙师驾临敝庄,蓬荜生辉啊,快请上座。”
袁守诚却眼皮都没抬,仿佛没听到他的客套话,只凝神静气地掐算了几下,然后突然脸色微变,“哎呀”一声,转身作势就要往外走,语气也带上了几分急迫,“不好!贫道老母亲要生了,我得赶回去,告辞告辞!”
他这一走,高太公的心更是提溜到了嗓子眼,本就揣着满腹狐疑,见这道士如此作态,更觉得他是看出了自家要命的勾当,哪里肯放人?
“仙师留步!仙师留步!”高太公慌忙上前拦住,也不顾什么体面了,紧紧攥住袁守诚的袖子,脸上挤出十二分的恳求,
“仙师何故走得如此匆忙,在下庄上略有薄茶点心,还请仙师略坐片刻,指点迷津啊。”
说着话,高太公一咬牙,给身旁管家使了个眼色,那管家先是一愣,但是看到高太公确信的眼神,走了一会,然后取出了一些银钱。
袁守诚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忌讳,连连摆手,作势要挣脱,
“非是贫道不给员外脸面,实是贵庄……唉!前几日那妖邪之事未了,又有更凶戾之物暗中盘桓纠缠,侵宅压运,此乃大凶之兆,贫道这点道行浅薄,不敢妄自插手,恐引火烧身啊,员外,你还是……松手吧!”
他越是推拒,越是点破“妖邪”、“暗中盘桓纠缠”这些字眼,高太公就越发笃定这老道是真看出了什么,松手,那肯定是不能松手的。
“大凶之兆”四个字,更是像冷水浇头,将他之前因为猪刚鬣护庄而生的那点得意冲得一干二净。
“仙师既然一眼就看出症结,还请大发慈悲!”高太公几乎是在哀求,给旁边的管家使了个眼色。管家心领神会,立刻端上一个精致的木盘,上面又放着两锭沉甸甸的银元宝。
袁守诚看到银子,眼神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动作也放缓了,但脸上依旧一副正气凛然、不屑阿堵物的高洁模样,沉声道,
“员外这是作甚?此等煞气,岂是区区白白之物能化解的?”
嗯?白的还不行?
“仙师明鉴!些许茶水钱,不成敬意,万望仙师救命啊!”
高太公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咬牙又加了点银子和一枚小巧的金锞子,亲自塞到袁守诚手里,沉甸甸的压手。
袁守诚掂量着手里冰凉的份量,面上挣扎了半晌,仿佛经受着巨大的内心煎熬。
最终,他重重叹了口气,勉为其难地收了银子,声音也软了下来,
“唉……罢了罢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既然员外心诚至此,贫道便破例再卜一卦,为贵庄……哎,为你个人,指条生路。”
他重新在花厅坐下,从怀中掏出一个油光水滑的龟壳和三枚磨得锃亮的铜钱。只见他闭目凝神,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含混不清,仿佛来自远古的咒文,充满了神秘感。
他将铜钱投入龟壳,郑重其事地摇动起来,发出哗啦啦的脆响,脸上表情随着摇动而变化,时而蹙眉,时而叹息,嘴里还煞有介事地念着,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如此连续打了三次“响卦”,看得高太公和旁边的管家屏息凝神,大气不敢出。
最后,袁守诚猛地将龟壳倒扣在桌面上,将三枚铜钱“啪”地一声摔在桌上,然后凝神细看铜钱的排布。
他看了好半晌,眉头越锁越紧,又掐指算了好久,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看着高太公,眼神锐利得似乎能看透人心,
“员外,贵庄这运势……啧啧,贫道直说了吧。”
他拿起一枚铜钱,在桌上点了点,
“你起初运道极佳,如同春风起势,广收财帛粮草……”
他又拿起一枚铜钱在另一处敲了敲,“恰如那水泊起浪,助你行船!这本是上上大吉之局!”
高太公听到这里,脸上不由露出被说中心事的得意之色,确实,有了猪刚鬣这“好女婿”后,庄子上是顺遂多了。
然而袁守诚话锋陡然一转,拿起第三枚铜钱重重一按,
“坏就坏在这里!助你水涨船高之时,却也引来了那水下蛰伏的妖孽,”
袁守诚指指天上,又指指脚下,“此物初时或许只是贪图些槽中细软,日久便会渐渐显露凶相,胃口大增,如饕餮再世。此孽障一日不除,非但员外你的万贯家财终将被其耗空,更因其性属‘妖’,迟早引来天怒人怨,到时…恐有灭门之祸啊。”
这番话句句诛心,尤其是“槽中细软”、“饕餮再世”、“耗空家财”、“灭门之祸”这些字眼,如同重锤狠狠砸在高太公的心坎上。
他脸上的得意早已消失不见,冷汗顺着鬓角就下来了。
猪刚鬣那张大嘴,那骇人的饭量,还有他妖怪的身份……这些担忧和恐惧被袁守诚毫不留情地撕开,赤裸裸地摆在了眼前。
高老庄是富了,可被一个妖怪坐吃山空,万一哪天猪性大发……他不敢想下去!
但高太公毕竟是老狐狸,惊惧之下,还存着最后一丝侥幸和试探,他强笑道,
“仙师说得虽然有理……可我家女婿……呃……颇有本事,能挡妖邪……”
袁守诚冷笑一声,毫不客气地打断,
“本事?呵呵,员外糊涂啊,他那本事是凡俗武艺还是妖邪妖法?它若真是良配,何须隐瞒来历,做那缩头藏尾之事?它若真是祥瑞,怎会招致那猫妖寻衅?如今连贫道这等外人都能窥破天机,可见此物凶兆已显,气数已尽,若不尽早处置,待其妖性大发,反噬主人时,悔之晚矣!”
他拂袖起身,再次作势欲走。
高太公被他一番话骇得面如土色,心中那点侥幸彻底破碎,一想到“妖性大发”、“反噬主人”,再看看对方决然离去的样子,更是六神无主。
他哪里还顾得上猪刚鬣此刻可能就在庄内某处?急急再次拉住袁守诚,声音都带着颤音,“仙师,仙师!万请指点迷津啊,那……那该如何是好,如何才能送走这……这孽障?”
袁守诚被拉住,停下脚步,回头看了高太公一眼,那眼神复杂,带着点悲悯,又带着点“天机不可尽泄”的意味,只留下七个字,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解铃还须系铃人!”
说完,他再不理会高太公的挽留,拂尘一摆,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留下心神大乱、满脑子都是“系铃人……系铃人……”的高太公独自在花厅中,脸色惨白,陷入深深的恐惧与挣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