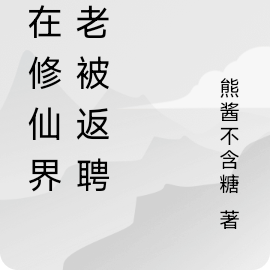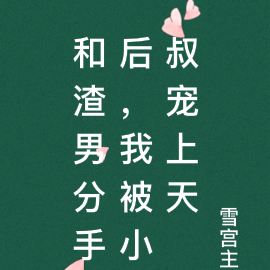陆仁彬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壮起胆子,语气依然奴性十足,“王爷,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在深埋空间里,那么好的回收神魂的机会,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浪费了?”李贺冷哼一声,“听说你在神脉空间里,出尽了风头,甚至一度违背本王的意愿,会不会有些着急了?”
陆仁彬闻言浑身毛骨悚然。
尤不罢休,“王爷,小的只是不理解,还请您解惑。”
“总之,近期内不准你对何家余子出手。”李贺冷言道。
“可不回收神魂,卑职的娘子始终残缺……难道王爷就一点都不急吗?”
李贺沉默,没有回答陆仁彬抛出的问题。
“王爷!”陆仁彬急眼了。
無錯書吧“不要让我说重复的话。”李贺的语气里多了些不耐烦。
“难道王爷是忌惮他身边的雷城之女?”陆仁彬直言不讳,这是他第一次壮胆刨根问底。
“这一次先饶了你,下次再敢随意揣摩,后果你自已清楚。”
陆仁彬冷汗直冒,但仍然不肯就此罢休,如果一直听从这位王爷的话,那么鬼妻要想真正意义上的成神,简直遥遥无期。
“你总得告知在下是为什么!到底在等什么!”
“你?在下?”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空荡的地牢夹道之中,安静极了,唯有李贺的冷笑。
他看着李贺的背影,心跳如雷,身上的每一处都在微微发抖。
紧接着,地牢一阵哀鸣,鬼妻从地下爬出,蓝色妖力覆盖,身体扭曲化作阿尔忒弥斯真身。
这不是他冲动所为,相反,得到神魂力量之后,他早就跃跃欲试。
李贺依旧没有回过身来,只是意念微动。
地牢的烛光忽的熄灭,陷入黑暗,随之替代的,是庞大的金色光芒,一瞬间亮如外界白昼。
半空,冲天而起的妖息凝聚成标志着地位权力的五爪金龙。
金龙仰天怒吼,金色强压降下,阿尔忒弥斯真身逐渐瓦解,鬼妻恸哭怪叫。
李贺转身面向陆仁彬,每迈出一步,陆仁彬如遭强击,身体寸裂,鲜血溅洒。
逼得陆仁彬不得不双膝跪地。
鬼妻更是被金龙摧残得难得成型,化作一摊脓水,剧烈沸腾。
“小的知错,请王爷高抬贵手,莫要跟小的计较。”
陆仁彬彻底老实了,顶着无形威压,艰难行礼。
“你不过一颗棋子,也敢在本王面前大言不惭!”李贺狞笑,“还是说,你在试探本王?”
“不敢不敢,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只是想不通。”
“想不通就不要想!”李贺怒喝。
他语气一转,没了先前的怒意,“你也太小瞧本王了,想要取本王性命,至少也要等到神魂齐全才行。”
“小的不敢。”
“哦?”李贺神情戏谑。
“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本王现在告诉你。”
他依然没有解开施加在陆仁彬身上的威压,双手负后,走到身后,踩着那一滩沸腾滚烫的脓水。
“要知道,雷城城主尚且立场不明,要想完成大业,不能与其交恶。再者,黄叶村近期还会来一名新上任的县令书记。目前不知何人,亦不知所属派系。”
“此事若是再闹下去,不免会被抓住尾巴。”
说着,李贺转身的同时收起威压,陆仁彬得以喘息。
“如今朝廷有两大派系,一是太子为首的革新派,二是宦官为主的求和投降派,再者就是何老这等愚昧顽固的忠臣。”
“你猜,那位将上任的书记,会是哪一派的?”李贺问道。
陆仁彬汗毛战栗,不敢再随意揣测,“小的不知。”
“哼,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狗东西,现在不敢了?”李贺故作悻悻然,踹了陆仁彬一脚。
“小的知罪,小的再也不敢了。”陆仁彬头紧紧贴在地面,再不敢抬起。
李贺对面前卑躬屈膝的陆仁彬失望极了。
他自顾自的朝地牢的出口阶梯走去。
“何家余子,近期会去雨城,现如今通向雨城的一切交通路线全部封锁,他走不了多远。等你神魂齐全,本王洗干净脖子等你。”
留下这一句话后,李贺踩着台阶,不紧不慢的离开地牢。
李贺失声而笑,地牢发生的这一切,同样是他对陆仁彬的试探。
早在与李青隼一战之后,他就注意到了陆仁彬散发出来的微妙杀意。
出于大局着想,他没有立刻问罪,反而加以重用。
比起苟立那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忠狗,陆仁彬这种反骨反而有趣得多。
帝王大道上,这等人何其多,若是屠戮殆尽,不能征服震慑而加以利用,哪怕成就帝王,亦是无能之辈。
只是这一次,他没想到陆仁彬仍旧会对他露出如此明晃晃的獠牙。
陆仁彬这样的棋子肯定是不能留了,只是可惜了浪费在他身上的精力。
他不是喜欢揣摩吗?那就让他尽情揣摩好了。
不知为何,李贺突然有些想念苟立了。
空荡荡的地牢内,陆仁彬匍匐在地,内心大喜。
李贺一离开,他便再也忍不住的大口咳气,稳住妖力河的同时满脸不服的啐了一口血水。
他不长记性的又一次揣摩起李贺的心思。
既然能让他知道如此多的情报,足以印证他在李贺心中的地位。
甚至最后离去前,还特意告知何晨阳的去向。
这其中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想到这,陆仁彬面容逐渐扬起笑意,狰狞可怖。
——
风城通往雨城的陆运总车站,大门紧闭,里面更是空无一人。
外边,站着愁眉苦脸的许赫等人,陈年年更是夸张的背着一个快比她人还大的包袱。
“都说停运了,偏不信邪,好了吧,白白浪费半天。”
凌纤雨双手叉腰,虎着脸看向许赫时,又不好意思起来,羞赧不敢直视。
许赫满脸尴尬,“这不是想来确认一下嘛,谁知道真停运了呢。”
“那现在怎么办?”许赫问道。
苟立冷眼相待,喃喃,“到底谁是被委托人?这么不靠谱。”
许赫尴尬的笑了笑,看着陈年年那大包袱,随便找了个理由宣泄情绪,缓解尴尬。
“都叫你别带这么多,懂不懂什么叫轻装上阵啊?”
陈年年一脸迷茫,“啊?”
“只能徒步,或者买条小船走水路了。”凌纤雨叹气道。
“水路,水路!”陈年年和许赫异口同声。
陈年年是想感受坐船的新奇,许赫单纯是因为懒,不想动。
“你们还真是不客气啊。”苟立说着风凉话,“买船钱算谁的?”
陈年年和许赫囊中羞涩,不自觉的脸红起来。
凌纤雨无奈,“算了,我出吧。”
苟立闻言直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