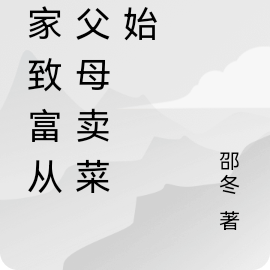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要问魂归何处,魂自归故里。
“师父,那位施主还会来吗?”
“不知。”
绵绵细雨,屋檐之下,身穿僧袍的两位僧人似乎正等待何人。
远处的阶梯传来踩水声,那人脚步不急不躁,想来应是常客。
这便是他们要等的人了。
那人撑着雨伞朝他们走来,尽管在微寒的初春清晨,他依旧穿得很少。
寺庙的人很少,大多都会挑个良辰吉日来祈福,或是求平安喜乐,或是家财万贯,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贪嗔痴,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
佛曰,人有八苦,而眼前之人皆不为此求。
“最近可安好?”
“一般。”那人身穿墨绿衬衫,一头乌黑的长发及腰。
“又是三年啊……幻真。”
被叫作幻真的高僧双手合十,他拨动手里的佛珠,看向那人手腕上已经磨损到发旧发黄的红绳。
“祁施主,该放下了。”
发丝被风吹散开,遮蔽了他的眼睛,像是没听见这句话。
祁肆依旧每月来此地上香,与幻真算得上是老相识。
“我大概是还在梦里。”他喃喃自语着。
三年前,祁肆从那棵树下醒来,所有人都告诉他,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多年,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类疾病。
祁肆不相信一切都是他的臆想。
他收起雨伞,将手腕的红绳摘下,双手交给幻真。
“幻真,请你帮我换根红绳吧。”
幻真接过红绳,对他来说,这是一根再普通不过的绳子。
于祁肆而言,却是一生执念。
幻真永远记得,那天也是清明,祁肆千里迢迢赶来寺庙,在门口等了整整一晚,只为见他一面。
祁肆捧着那根红绳双膝跪地,双目充满红血丝,眼神执拗。
“求您,让我看她最后一眼。”
这根红绳幻真在几年前就给了祁肆,只因这人每年都会来为他的妻子祈福,他会主动与幻真聊起他的妻子。
幻真从他口中得知,他与他的妻子在校园相识相知,然后在一起了。
但他的妻子身体不大好,所以不常出来走动,幻真给他算了算,却总也算不出他的妻子到底是何病症。
所以,幻真问过他妻子的生辰八字,再特意送了他一根红绳。
之后,祁肆就没再来过。
直到再见祁肆那一刻,幻真才明白他为何算不出来,原是亡故之人。
幻真那时也无他法。
“当执念散去,即死而无憾,魂魄便会消散于天地间。”
“你那时能见到她,只因她执念过重,不愿就此消散。”
祁肆转过身,他的背影如此单薄。
“那我的执念呢?”
他每日上班都如同行尸走肉,那个叫作段念的女人,再也没出现在医院过。
段念,断念……
这也是他的臆想么?
祁肆曾找过那位小护士,只是她满脸都是惊悚与害怕的感觉。
“祁医生,您妻子死的那天,是我在医院门口将她抬上担架的啊。”
“我以为三年前您早已释怀了,没想到您还是……”
至此,他也没再找过小护士。
所有人都认为祁肆精神失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是这样。
幻真见他困扰又痛苦的神情,轻声细语道:“总会知晓的……”
恰好,雨停了。
幻真从禅房替他换上一根新红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祁肆只当留个念想罢了。
他将及腰长发半束,面色过于苍白,平添了几分病态的美感。
“幻真,这些年来,多谢你了。”
幻真摇摇头,“我也只是这大千世界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既不甘如此,那便把握机会。”
祁肆没理解他的意思,只是笑笑。
“我走了,再见。”
幻真注视着他孤寂的背影,闭起双眼嘴里念着什么,继续等待。
“……再见。”
……
……
……
祁肆踩着阶梯往下走,途中遇见不少上山祈福的游客,他没有留意。
忽然,一位少女与他擦肩而过,那少女脚底打滑险些跌倒。
祁肆扶了她一把,这才站稳。
不是好心,而是他见过这位少女。
“谢谢你啊……”
“不用。”
虽然记不得她的名字,但她的长相还是稍微有点印象。
少女见他上下打量自己,往左右两边瞟了几眼,暗自松口气。
“请问,还有事吗?”
“你在躲人?”祁肆随口一问。
“呃……没有啊……”
少女撒谎的模样显而易见,祁肆忽然又想起了她。
“啊!我想起来了!”
“游乐场我见过你们。”
“我是那个池鱼,之前和你们一起玩鬼屋的。”
祁肆不在意这些,只觉得这个池鱼身上的气质很奇怪。
“怎么没看见你的女朋友啊?”
“她去世了。”祁肆说得轻描淡写。
池鱼话哽在嘴边,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
“不好意思啊,提起了你的伤心事。”
池鱼被祁肆一直盯着发毛,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的眼神太过尖锐,仿佛要把她看透。
“我有事,我先走了……”
“等等。”
池鱼顿住脚步,却没有转身看他。
“过了二十年,你的样子倒没什么变化。”
“我早面目全非,你却还能一眼认出我是谁。”
“你的记性真好。”他语气凉薄。
池鱼看不出什么破绽,“那当然,我记性是不错。”
“是吗?”祁肆死死盯住她的背影。
忽然,池鱼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她弯腰抱住脑袋,难受得蹲下去。
祁肆见状况不妙,正想查看情况。
哪知她忽然又重新站起来,还装作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需要我叫救护车吗?”
“不用不用。”
池鱼偏头看起来没事,她朝祁肆挥挥手道别,快速溜走了。
祁肆反复回忆,无形之中有一道枷锁在禁锢住他们,看不透摸不着。
他猜,池鱼就是关键钥匙。
或许是他的臆想症又犯了。
祁肆的手指反复揉搓着他的发尾,或许他就是一个疯子罢了。
任何想法,他都不会放过。
回去后,他依旧每日正常工作,尽管医院总有个别小人检举他。
院长多次找祁肆谈过话,得到的永远都是一模一样的答案。
他各项检查都正常,包括不同地方的心理测试,也表明他是正常人。
所以,院长也奈何不了。
况且,他比别人都更优秀,按理来说医院确实没资格随意处置他。
医院虽然有些风言风语,但没过多久该散的也散了。
祁肆更是不放心上。
科室里的人都在唠嗑,祁肆没一点兴趣了解,直到听见池鱼的名字。
“啧啧啧,这女孩年纪轻轻地,怎么就癌症晚期了。”
“听主任说,没几天时间了……”
祁肆震惊于这个消息,他从同事那里要来了池鱼的病历资料。
资料看着没问题,但她怎么……
祁肆找机会去病房看望了池鱼,她的变化极其可怕,简直不能相信。
明明几个月前还很好,现在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少女,毫无生机。
池鱼嘴唇发白,头上戴着毛帽,大概是做化疗的缘故,头发全部都剃光了,看起来她的心态似乎还好。
“你是医生?”
“是。”
池鱼看到他时很惊讶,就如同祁肆看到她时也没想到。
“你以前没检查过身体吗。”
“没有。”
癌症晚期,没有任何预兆。
池鱼捂嘴咳嗽几声,她抬眼见祁肆还在用那种眼神观察她。
“祁医生,我没得罪你吧……”
“为什么这么说?”祁肆反问。
池鱼有些无语,她也不好直说。
“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她没再纠结这个问题,反正她一个快死的人,何必在意这些。
“不是错觉。”祁肆坦白道。
“我只是想从你身上,找个答案。”
“答案?”池鱼发出疑问。
“对,我想要的答案。”
祁肆而今束起高马尾,眼神却游离世界之外,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池鱼的头又开始犯痛,她这次抱头的时间很长,祁肆并没有上前帮忙。
过了一会儿,她的头就不痛了。
祁肆很好奇她这种突发反应。
“你好像并不悲伤。”
“毕竟,你快死了。”
祁肆故意说得这么难听,哪知池鱼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死亡。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她说得这么深奥,眼神不见痛苦。
祁肆似乎明白了什么,笑了笑不再继续试探,只留下一句话。
“死亡,也就意味着新生。”
池鱼目送走祁肆的人影,她颤巍巍地抬起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或许吧……”
祁肆回到家打开门,屋里摆满了一盆盆的风信子,他心中发涩。
虽然是温暖的春天,但这些风信子开得不太好,看样子也活不久。
他的精心照料,终抵不过岁月漫长。
花败了又败,就算四季更迭,回不来的终是再也回不来了。
祁肆指尖触碰花瓣,怜惜地抚摸着,花瓣顺势凋落下去。
“你也,坚持不住了吗……”
他声音喑哑,艰难地开着口。
翌日,祁肆散着长发踏进医院,他直奔向池鱼的病房走去。
打开门,却发现她人不在。
按照平常的时间,她这个时间点应该在吃午饭,等了很久还没回来。
祁肆预感到不好的事情。
他在医院四处找了半天,依旧没看见池鱼的身影,像是一个预兆。
祁肆回想起,照顾池鱼的护士曾吐槽过她总想不开,总想……
最后,他找到了池鱼。
池鱼站在天台外围,张开双手,就像张开鸟儿的翅膀一样。
她毫不犹豫地往后倒下去,嘴角还挂着轻松地笑,解脱又释怀。
祁肆站在那里没动。
世界仿佛停止运行,他的意识逐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此世界已崩塌,重启失效,请宿主尽快脱离角色……”
冷漠的机械电子音响起,他忽然便明白过来,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原来那天,幻真是这个意思。
亦幻亦真,亦真亦假。
所以,我们都只是茫茫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罢了。
现已,尘埃落定。
……
……
……
虚无之空,混沌意识。
“若给你一次机会,你能否把握?”
“朱砂难消,欲望难除。”
“本世界已无法再启,便让你堕入轮回之眼,去寻找灵魂碎片……”
“多谢主上。”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