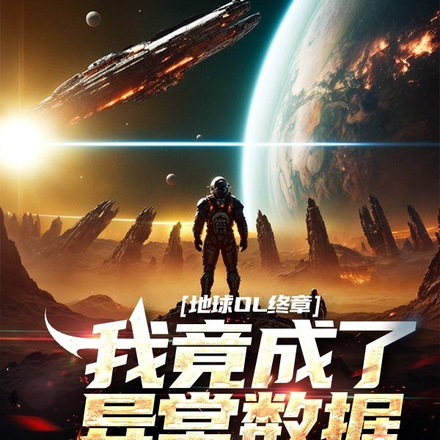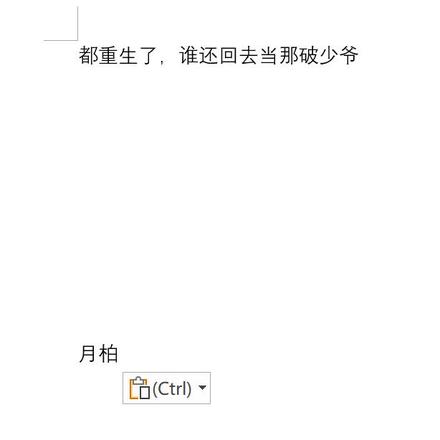慕凌以为人算齐了,江崖告诉她:“还有两个人没来。”
“还有人吗?”
江崖解释:“嗯,不过也不确定会不会来,要是她来的话,希望你不介意。”
“我想我不会介意的。”
都是被邀请而来的人,谁又能介意谁呢?
篝火堆上架着烤肉,每个人面前摆着散发香甜气味的果子,以及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果酿。
火光在每个人脸上跳跃,一派喜气洋洋。
有狼兽领头,带着众人站起来手拉着手围着火堆跳舞。
牛皮鼓的响声也在此时响起,另有狼兽拍鼓奏响节拍,以便跳舞的兽人踩着节拍起舞。
气氛很是热闹。
可这样一来,慕凌不得不和同一个篝火堆里的人牵着手,也投入到这个环节中。
她的左手牵着亚利,右手空着;
蓝衍和江崖都想上前一步去牵,还未触及,有人先一步牵过她的手。
欧泊很自然地牵过了慕凌的手,和颜悦色地看着她。
没想到被人捷足先登,蓝衍和江崖相视一笑,悻悻地握住了彼此的手,心中都叹了口气。
亚利努努嘴,有几分不高兴,可也没多说,免得破坏气氛。
慕凌第一次参加结侣仪式,心中欢喜雀跃,这里的风土人情,别有一番滋味。
众人跳累了,烤肉也熟了,接下来便是兽人们最期待的大吃大喝的环节。
沙丽瓦和白汀牵着手同时出现,往慕凌所在的篝火堆走来。
两人已换回正常的兽皮衣服,一出场就引得狼兽们起哄。
“这是你说的两人吗?”慕凌问江崖。
江崖笑着探出头来,他和慕凌中间还隔着欧泊,“不是呢,也许今晚她不会来。”
沙丽瓦一走近慕凌,就从身后拿了个兽皮袋出来,“小凌,给你的。”
一脸神秘兮兮的。
兽皮袋有些沉,慕凌拿在手中,感觉里面的东西硬邦邦的。
“什么来的?”
“你打开看看。”沙丽瓦眨眨眼。
一双琥珀色的眸子陡然亮了亮,欧泊突然转头看向慕凌,嘴角扬起好看的弧度。
他看向慕凌时的视线简直溺死熊,亚利心里咕哝了句,有什么好乐的?
慕凌将袋子打开,一件雕刻得惟妙惟肖的木雕人像呈现在几人眼前。
在场的狼兽还有谁没看明白?
江崖、小津、斑孟,三个从小和欧泊玩到大的雄性,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欧泊的杰作。
慕凌拿在手中仔细看了看,雕的竟是自已和沙丽瓦相依相偎的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前两天的欧泊送的木雕,心中有了疑惑。
“送这个给我做什么?”
沙丽瓦大喇喇地说:“这是我们作为同伴的见证,我一件、你一件。”
“这么客气。”慕凌调侃她,“你请人雕的?”
沙丽瓦挤到慕凌和亚利的中间,一屁股坐下。
亚利不情愿地挪了挪地,结果白汀见缝插针也坐了进来,这下他和慕凌中间隔了两个人。
亚利心里憋屈,闷声闷气地和白汀说了什么,白汀摇了摇头。
沙丽瓦凑在慕凌耳边,低声说:
“不是,欧泊阿兄那天撞到了我,这是他给的赔偿,他还真的按我说的雕了两件,我这不就给你带过来了吗?”
话说完她冲欧泊眨了眨眼,像是打着暗语。
原是这么来的。
同伴送的礼物没有理由不收下,慕凌笑说:“那真谢谢你了。”
慕凌能收下,沙丽瓦很高兴,但有人却比她更高兴。
沙丽瓦哈哈大笑了一阵,突然停了下来,扭头冲着亚利说:“干嘛这样看着我?”
亚利忽然被她一说,老大不高兴地转过头去,“谁看你了?”
“那是在看小凌?”沙丽瓦反应迅速。
亚利没承认。
他不是个擅长说谎的雄性,干脆闷声不回答。
沙丽瓦了解他的性格,“哦”了一声,恍然说道:
“呵,就说是在看我嘛,还不承认?干嘛,我结侣你不高兴啊?”
亚利被她话激怒,反驳:“哼,俺哪里不高兴啊,你结侣是好事!”
“不见得,你怒视不就是不乐意我结侣吗?”沙丽瓦起了戏弄心,“让你和我结侣你不听,好了,后悔了吧?”
“谁后悔?俺才不会后悔。”亚利气急败坏。
沙丽瓦继续说着自已想说的,“如果你现在愿意和我结侣的话,我保准收下你。”
亚利又反驳了几句,两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
夹在两人中间的白汀心里不好受,这和打情骂俏有什么区别?
慕凌也不是第一次见两人这样相处了。
没出什么事,她索性不管,默默品尝起果酿来。
坐在慕凌对面的蓝衍端起牛角杯,对着她高举了下,便一饮而尽。
兽世难道也有敬酒文化?
慕凌觉得不太可能,巫师那是不经意的动作吧。
果酿带着芳香,甘甜微辛,比慕凌以往喝过的酒还要好喝。
慕凌是喝了一杯又一杯。
欧泊见她爱喝,端着陶罐给她慢慢地倒着果酿。
慕凌道了谢,两人并未多言,气氛却好得出奇。
看得身旁的人都安静下来,亚利和沙丽瓦也不吵了。
“他们还真是般配啊。”小津嘀咕了一句,他身旁的雄性们也都听到了。
有这样想法可不止小津一人。
连亚利也不得不承认,两人是真的配,欧泊的颜值不差,实力也强;
一想到这,亚利的眸光黯淡了几分,他是二纹兽,比欧泊还差了一纹,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达到三纹,这不禁让亚利心生几分自卑。
慕凌的身旁总有不同的追求者献殷勤,喜欢她的雄性心里就不好受了。
不知是不是看得心里难受,蓝衍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开。
蓝衍走后,没多时,原本闹哄哄的气氛一下安静下来。
慕凌抬起微醺的眼眸,问沙丽瓦:“怎么这么安静啦?”
沙丽瓦目光落在了前方的一处。
慕凌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
一名跛脚狼兽推着轮椅上的雌性,缓缓向她们走来。
那雌性戴着张古怪的白色面具,像是用骨头制成的,让人看不清她的容貌;
她安安静静的坐在木轮椅上,任由身后的雄性推着她往前走。
所有在场的兽人都噤了声,心中只道:她怎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