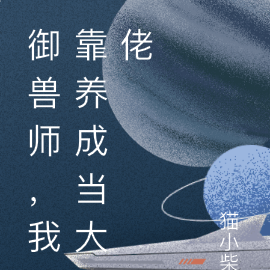第25章 迟袂利群
我拉着迟袂利群来到一旁人少的地方,对迟袂利群展示着被绑带层层缠绕的右手臂:“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手撞到护栏了。”
迟袂利群闻说,定定地看向我的手,目光停了好一会,才显得有些迟钝问道:“噢,手、手受伤了。手,没事吧?”
我点点头,笑了一下:“没什么事,医生说只是软组织挫伤。”
然后我看着迟袂利群的脸色,斟酌着道:“利群姐,我听说你的事情了,你还好吗?”
迟袂利群勉强笑了笑,笑容显得很惨淡,也带着一些嘲讽:“怎么,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了我家出了什么事吗?”
我赶紧摇头:“不是的、不是的。”
“副社长今天来告诉我周五的聚餐取消了。”我手忙脚乱地解释着,“我见你两天都没来上学,而且周六的那通电话又是那么急匆匆的,我很担心,所以多问了几句。”
迟袂利群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有些麻木,她听我一阵慌乱的解释后,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漠然地点了点头。
我看向她手里的发票:“这是给妹妹刚交完费吗?”
她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然后将这些单子折起来,小心的放进了随身带的包里。
见她谈话兴趣缺缺,我决定在话中加码:“肇事者是不是姓樊?”
迟袂利群的眼睛闪过一丝惊讶,她追问道:“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又问道:“为什么是你来缴费,这种费用不应该是肇事者承担吗?”
迟袂利群低着头,显得有些失落和无奈:“说是他们家的资产被冻结了,说拿不出现金,明天妹妹就要火化了,医院这边又一直催......”
说着,泪水从她脸侧流下,滴在了大厅的白色瓷砖上。
我有些于心不忍,向前走了几步,用一只手抱住了她略微颤抖的肩膀,默默无语。
迟袂利群的身体一僵,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但很快,那紧绷感渐渐消散。
她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头轻轻搁在了我的左肩上,泪水不断地往下淌。
一边低声啜泣,她一边呢喃着:
“我就不该让她自已出门,我应该陪着她的。”
“都怪我......这都怪我......”
我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没有说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已经下班了,此时正坐在我原来的位位置上,和爸爸说着话。
他们的目光不时地看向我这边,明显是在等待着我。
我轻声对迟袂利群道:“这里不是方便说话的地方,你要不要去我家,我好好听你讲。”
迟袂利群这时才如梦初醒般抬起头。
她轻轻推开我,站直了身体。
她的眼眶周围因为哭泣而留下了明显的泪痕,脸颊也因为缺氧而微微泛红。
听说要去我家,迟袂利群摇了摇头:“我一会还要去警察局。”
我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纸巾,递给了她,惊讶道:“怎么这么晚还要去警察局?”
迟袂利群接过纸巾,摘下眼镜,然后擦了擦脸,恢复了刚刚的样子,但话语中多了一些温度:“很多事情还没定下来。”
她看向我的家人,然后转头看向我,眼里带着些羡慕:“快回家吧,他们在等你。”
我突然想起学哥说的话。
他说迟袂利群家里只有姥姥、她和妹妹,而现在妹妹却死了——她的亲人只剩下姥姥了,她只能与姥姥相依为命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道:“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或者你想找人倾诉,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迟袂利群听到这话,突然自嘲般的发出了一声尖利的笑,周围的病人、护士被这一声吓到,纷纷侧过头看向她。
她脸上挂着讥讽:“你和樊青不是朋友吗?你怎么不去找她,反而来找我?”
我一时语塞。
她见我沉默,以为自已说对了,嘲弄地勾了勾嘴角。
迟袂利群后退一步,将我俩之间的距离拉开,然后将沾满泪水的眼镜取下,慢条斯理地将上面已干涸的泪痕擦净。
再次戴上眼镜时,眼睛里已满是疏离。
她转身向医院门口走去,没有再看我一眼。
汪韫沁这时来到我的身边:“姐姐,那个人是你同学吗?”
我看着她的背影渐渐隐入黑暗之中,轻轻点了点头。
妈妈这时也来到我的身旁,她知道迟袂利群家里的情况,只是也看着迟袂利群逐渐消失的背影,微微叹息了一声。
妈妈轻轻拍了拍我左肩,道:“走吧,回家吧。”
回家吃完消炎药,又简单的梳洗了一下,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直是今晚迟袂利群那略带讥讽却脆弱无比的笑容。
事情果然就像我推测的那样,迟袂利群的妹妹去世了,而肇事者就是樊青的母父。
我关心她,她却误以为我是为了樊青而接近她。
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
但我是为了让樊青不要被骗入诈骗集团,而不是想左右这次的车祸任何判定或者赔偿。
迟袂利群的妹妹去世了,令人心痛,但樊青母父做的事,不应该牵扯上樊青。
而还在上高二的迟袂利群,因为这件事失去了自已的亲人。
除了处理丧事之外,还要和樊青母父那种有许多年社会经历的成年人谈判和周旋。
想想就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对着天花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起床,妈妈来到我的卧室,给我的手臂换药。
拆开纱布后,明显看到手臂的部分地方已经恢复了原本的颜色,只是还有些肿胀,还需要用药。
妈妈也伸手摸了摸我的骨骼和关节:“没大事,消肿了就好了。”
我点了点头,乖乖的坐着,让妈妈替我换药包扎。
妈妈手里麻利的做着,一两分钟便包扎好了。
妈妈将药和纱布收拾好,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我在卧室里高声叫道:“汪韫沁!”
汪韫沁打着哈欠,满眼惺忪地走过来,靠在卧室门口,带着些起床气,她语气不善道:“干嘛。”
我笑了笑:“帮我换衣服。”
汪韫沁走了进来,径直走向衣柜,转头问我:“你要穿哪件,这件?还是这件?”
我在床边坐下:“都行,你帮我选。”
十分钟后,我穿着酒红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深绿色的呢子大衣,背着书包,走出了家门。
出门买完菜回家的邻居叔叔们看见我,都跟我打着招呼:
“小丫头,今天穿这么精神。”
“早啊,姑娘,今天过节啊。”
我笑着一一应着。
待邻居走远了,我狠狠剐了一眼正在偷笑的汪韫沁。
汪韫沁抗议道:“是你让我随便选的!”
是啊,不穿你选的你就撂挑子。
我咬碎后槽牙,低声道:“等我手好了再收拾你。”
汪韫沁装作没听到的样子,蹦蹦跳跳走在我前面:“啊,你说什么?哎呀哎呀,公交车来了,赶快上车。”
手臂受伤,骑不了车,因此我们今天坐公交上学。
公交车上除了上学的孩子,还有许多通勤的大人,人满为患,一个小小的公交车上站满了人。
我左手抓住公交车的护把,微微弓着背,把右手护在胸前,随着公交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摇摇晃晃的。
我站在紧紧挨挨挤挤的人群中,突然觉得自已就像在罐头里一条条整齐排列的沙丁鱼,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身边的路人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赶紧收住脸上的笑意,作正经状。
半小时后,我到了学校,刚坐到位置上,于怡佳和饶一诺便围了过来。
她俩看着我的手,饶一诺伸出一根手指头,戳了戳被纱布包裹起来的右手臂,疑惑问道:“你怎么了?”
饶一诺怎么跟妹妹似的,看见我手臂受伤,就伸手指头戳我。
我眼里带着笑意道:“昨天和你们分开后,骑车摔了一跤,手臂摔肿了,今天已经好多了。”
于怡佳点了点头,道:“那就放心了。”
然后她抬头看向我,问出了我没想到的一个问题:“右手受伤了,你今天怎么记笔记、写作业?”
还真是!
我挠了挠头,伸出左手抓起了笔,在空白纸上尝试写下自已的名字。
歪歪扭扭的字迹在出现在笔下,但出乎预料的是,“汪韫玉”三个字还是顺利的写完了。
我盯着那三个字,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拿起来递给两人看:“好像,还不错?”
饶一诺惊讶道:“比我想象中好啊!”
于怡佳也表示同意:“看来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了。”
上课铃响了,她们将那张纸放下,回到了自已的座位上。
我看着纸上那略显扭曲,但依然流畅的字迹,心里略感到惊奇。
我的右手在此之前没有受过伤,因此也从没尝试过左手写字,今天一试,竟然出乎意料的流畅。
难道我是个隐藏的左撇子,活了两辈子了,到今天才意外发现自已的天赋?
我心里“哈哈”一笑,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课堂上。
日子很快过去,我的手臂也逐渐好转起来。
半个月后,迟袂利群才回到了校园。
她看上去比在医院时显得更加憔悴和瘦弱了。
原本圆润的脸庞,现在瘦削得几乎能看见颧骨的轮廓,曾经合身的校服,如今松垮垮空荡荡的挂在她的骨架上,秋风吹过,冷风便会毫无阻碍地灌入那些宽松地衣缝,像是鼓起的一个无力的气囊。
原定的阅读社聚餐延期了,而迟袂利群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似乎,妹妹的的意外死亡让她对聚会聚餐这种事情失去了兴趣。
阅读社的活动也全权交给了副社长,她几乎不过问了。
大家都知道她家里发生了什么,都很理解,默默地不去打扰和催促她。
再后来,我听学哥说,樊青在迟袂利群请假的那一周,主动申请退出了阅读社。
樊青,也依然躲避着我们,在校园里面匆匆看见了,也只是低着头快速经过。
偶尔,我、于怡佳和饶一诺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会看见樊青一个人默默的站在深秋的暖阳下,闭着眼睛,仰面朝着太阳。
周围的同学大多都是两三人一伙,樊青独自一人站在操场中间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
她上下学也不再打车了,而是蹬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一看就是在二手市场里购买的。